
《黄河长调》是一部厚重的行吟之书,它既是地理的史诗,又是心灵的独白,既是历史的回响,又是现实的切片。它也让我意识到,通过长卷去展示诗性空间的同时也能折现自我的内心世界,两者既并行不悖,又相互缠绕。
行吟诗自然跳不开行路中的一站又一站,涉及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历史钩沉与传说。诗人在出发前,必须作相当的文案功课,从中确立行走路线以及沿途的停留方式和关注重心,这功课绝非简单的行程规划,而是一次精神的预演与知识的奠基。它要求诗人提前潜入历史的尘埃,触摸地域的脉动,在纸上勾勒出一条不仅是地理的更是精神的、情感的、诗学的“预行路线”。而更为关键的是,诗人行走的使命不是探险或观光,而是怀揣秘密的心事:行万里路,写万行诗。这是生命力的投入,更是心智的产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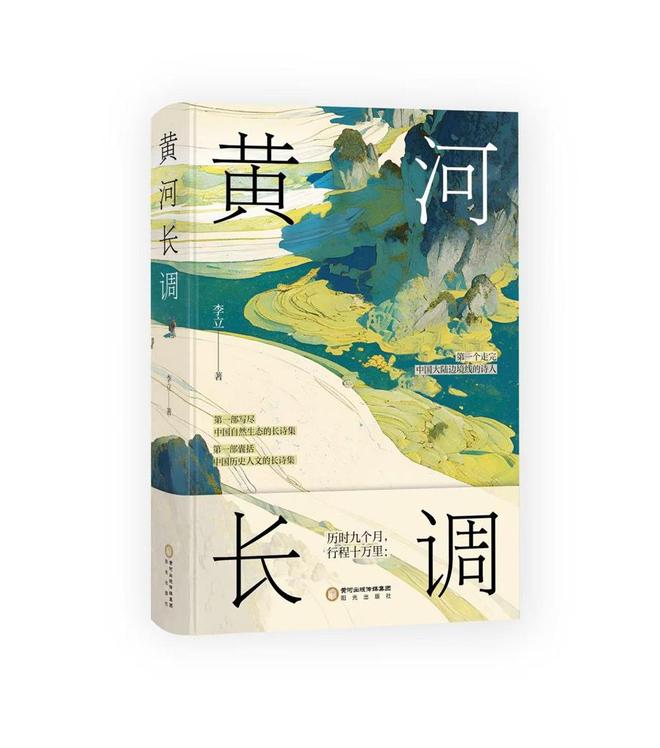
诗人一路走一路被自然和异域风情所“融化”,这“融化”是灵魂的敞开与重塑,是诗人卸下都市的盔甲,让高原的风、戈壁的沙、草原的雨浸润肺腑,直至与万物同频共振;诗章或许边走边写,但归来复盘时,全书才能一气呵成。李立九个月的行程,内心既有恒定的温度也有惊悚与落魄,这构成贯穿全书的气息,他的内心有另一条“黄河”,它同样源远流长,同样泥沙俱下,同样有九曲回肠的迂回,它是诗人个体生命体验与民族意识交融的河床,承载着个人的孤独、时代的困惑、历史的回声以及对生命本源的追问。
从全诗来看,不同的地域记述采用了同一种叙述风格,并没有采取不断“变调”或相异诗体的手法,保持了强劲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关键是,作为读者一节节读下去,自然随着诗人的“吟唱”行走,尽管大部分地方我们或许没去过,却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也是一首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诗,你可以从任一章节出发,也可以在任一处结束。必须指出,李立诗中对一座孤峰或清流描述时,他着重的不是“拍照”而是“摄影”,这是内心情感、认知、生命和现实的投射,在一派纯简与质朴中给予人生的许多答案。
《黄河长调》的信息量是惊人的,也是节制的。当然,李立的诗没有对一路风光作过多“象征性”的诗化处理,而是坚定“写实”,作为一部“万行诗”,他的选择是明智的,近二十处不同风光的意象式描述反而会让与自然的对话变得不那么可靠。李立诗歌倾向于明快与直截了当,这是他的个性也是他遣文造句的力道。他同时是激情的、有胸怀的,不然如此宏大场景的铺排注定会无法安放。他在每一章的某几个“转合处”,往往会在平静叙述中果断加速,如一个情感“爆发点”,读者也会跟着热血沸腾。他的每一章节都会有一个主线索,实际上就是诗人“走进”每一处时双眼和心灵初始接触的点。如《极边第一城》,诗人是从“翻越高黎贡山的石头古道”进入的,于是从这条古道说起,从“生存之道”展开至命运的探讨,转至对“石头”特别论述,又因为当地人生活与石头的特殊关系展开对山石的哲思,将“诗与思”推至极限。可以说,这一章是一首完整的有关石头“宇宙”的诗,相互铺垫,转合自如,前后关照,突显了诗人笔力的苍凉沉雄。

作者充分利用长诗创作中自由度广的优势,笔峰和意象的游走不拘一格,但不代表诗人对文字的简约性没有关注。《黄河长调》虽长至万行,二十多个题材,却始终显示了通盘把控力,李立在写作中或许曾做过多次修改,把多余的枝蔓删除了。值得注意的是,李立是激情四溢的,但当他静心打理长篇巨制时又显示了沉静与耐心,形成了细微处冷静、全诗抒情的风格,甚至他穷尽了当代诗歌中多种抒情元素的可行性,情感成熟、丰盈但不外溢。他坚执地照着现实写而非吟咏,见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用语言跳跃和翻转说出他想说的,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所以他的抒情是宽阔而又细腻的,尽管情绪指向是多解也无确切内涵的,但他内心既孤独又壮烈的“空疏感”让读者强烈感受到了。
如果我们将他的诗句置于恢宏又幻变的时代背景下,会发现他无意中确立的情感坐标以及清晰呈现的历史想象力,所以从他的万里行程可以断定,这是他的思索之旅或曰人生修行之旅。在这部长诗的创作过程中,诗人的人生也发生了多个事件,将人生旅程与万里河山行比照起来,我们就更能理解作者创作这部长篇的初衷,感受他的勇气、“野心”、修为、哲思与巨大的“吞吐力”。
(作者系诗人、诗歌研究者)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