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名士”,事事皆“快乐”

对学者董铁柱而言,《世说新语》不仅是一个研究课题,更是一部“生活之书”。若要谈论生活,免不了要对思想祛魅,在2021年出版的《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一书中,董铁柱一反传统观念中认为魏晋名士皆“自由”“真性情”“浊世清流”的成见,指出《世说新语》中的一个个故事更接近于“公共空间里的表演”,“魏晋名士人人都渴望通过‘表演’获得赏识……魏晋玄学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当时的生活产生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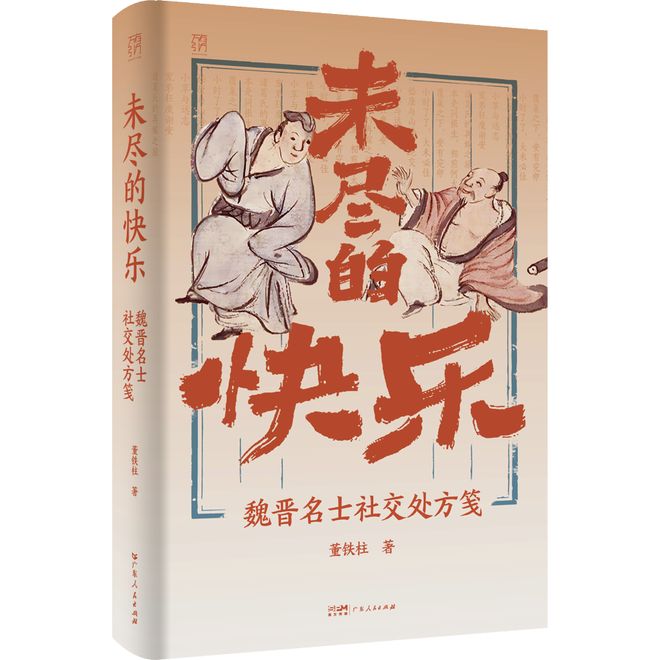
《未尽的快乐:魏晋名士社交处方笺》,董铁柱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然而到这部新作《未尽的快乐:魏晋名士社交处方笺》,当董铁柱以“快乐”为主题再次进入《世说新语》的世界,魏晋名士身上“真实”的标签,似乎又被他重新贴了回来。“《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大约正是由于他们的‘真实’。”但细读文本,其实不难发觉,这样两种解读并不矛盾。《演而优则士》中“表演”,是公共空间中的安身之法,而《未尽的快乐》中“真实”,则是植根于个人性情的安心之道。由此《世说新语》之于生活的意涵得以进一步丰富:当我们意识到魏晋名士既需要在公共生活中演绎一种“自我”,又努力在内心保持“本我”,我们便可以将他们充分想象成如我们一般的存在,而这正是本书的立足点之一,“不是让我们成为名士,而是把名士变成我们”。
内心真实,进而获得满足,这便是董铁柱对于魏晋名士个人层面“快乐之道”的高度概括。但纵然魏晋思想以“独化”为主流,“独化”本身也仍然包含对和谐关系的追求。因而在《未尽的快乐》中,董铁柱真正讨论的是个人何以在“关系”中取得快乐——全书七章以“君臣”“父子”等七种关系入题,即彰显了这一点。而在种种关系的背景下,最能体现所谓“魏晋风骨”的,其实是“习俗”。在这里董铁柱借用英国史学家E. P. 汤普森的经典观点,将习俗视为“共有的习惯”——正如18世纪的英国工人经由此类在贵族阶层看来耸人听闻的习惯确认自身、联系彼此,魏晋名士对礼教的所谓“反抗”,实则体现的是一种默契, “习俗尽管偏离了礼教的规定,但也依然不离礼教的精髓——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从而让人获得快乐”。
到这里我们不难发觉,“中西互鉴”乃此书的一大特色。作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哲学博士、汉学家魏斐德的高足,董铁柱西学功底扎实,同时又对中国古典思想与文学理解颇深。故而读者在本书中既可以经由文本细读,收获关于《世说新语》种种故事的通俗性和现代性理解,又可以看到它们如何与齐泽克、休谟等西方哲人的思想相呼应。如写到“将无同”(《世说新语》中最著名的“梗”之一),作者援引休谟认为道德讨论应“建立在事实和观察基础之上”的主张,强调了“将无同”绝不意味着道德虚无主义,而是对非黑即白的二分准则的废弃,进而使得多元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
“将无同”一则,被作者安排在“君臣”一章加以讨论。相比本书其他的六种关系,君臣关系似乎早已被当代社会废弃,却往往又被认为最“不可动摇”。有趣的是,当我们在《叫魂》中看到一个“受困扰社会”如何因为不可避免的“损失分摊”走向零和博弈,以致分崩离析,魏晋名士恰恰通过自己的“习俗”,即对于传统礼教的适度偏离,令社会裂隙有所弥合——至少是在贵族阶层。如常常被诟病以僭主之姿登上皇位的司马一族,其争议性往往能够通过对名士不羁言行的容忍得到消解。《轻诋》第十八则写的是东晋名士许询在简文帝司马昱面前直言“举君亲以为难”,即在君王与父母之间二选一并不容易,而简文帝却并未直接斥责许询,只是在许询离开后表示“玄度故可不至于此”——许询(字玄度)本可不必说这种话。世人往往由此看到皇权没落、君王卑微,但这种卑微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在门阀崛起的背景下)君王需要考虑的是在做一个真实自己的基础上如何与臣子之间展开双赢的合作,而不需要担负起教化臣子的责任,也不必须成为臣子的表率”。
灭亡与担忧灭亡的焦虑注定令人不快——在社会动荡、关系松动的背景下,如何求得安稳,成为魏晋名士生活的重要课题。书中最具启发的部分,也许是《春秋》中“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与《世说新语》中最典型的快乐“父子之乐”的对比。“作为人伦关系的基础,父子关系也是一个人快乐的最基本保障。在一个纷乱的社会中,当君臣等其他关系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之时,父子关系成了一个人最可以依赖的纽带”。若是再进一步,我们其实可以得出孔子与刘义庆在书写诉求上的差异:春秋时期也并非父子皆仇敌,但孔子写父子相残,是为了强调纲常可以提供超越人性的约束;相应地,魏晋时期自然也不乏父子抵牾之事,但刘义庆却希望提供纲常崩坏之后的备选方案。其极致也许是“何氏之庐”:当曹操欲将时年七岁但“明惠若神”的何晏纳为自己的儿子,何晏却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称之为“何氏之庐”。在董铁柱看来,“即使我们不知道何晏的父亲是谁,也可以感受到何晏对自己父亲和家族尊严的捍卫。可以想见,父亲是令何晏自豪的”。关于何晏是否果真对一个已然缺位的父亲感到自豪,其实有待商榷,但无论是“公共空间的表演”,还是捍卫自己内心的真实,“何氏之庐”都意味着一种自保策略——在秩序趋于混乱的节点,与其趋炎附势,不如退回自己的一方天地,坚守最基本的“角色”。

图源:视觉中国
退守根本,进而根据现实变化调适自己与周遭世界的关系,成为在转型时期安顿自身进而寻得快乐的关键。《未尽的快乐》重构的正是这样一段“快乐史”:一些聪明的“名士”,如何将负累重重的实际生活转化为种种“快乐”。由此董铁柱对《世说新语》的探索得以进一步完善:纵然魏晋清谈的确无助于改变现实,但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还是为后世提供了有关生活方式——如何构建、调适“自我”——的有益参照。而个中益处首先为书写者所享。在后记中董铁柱坦言“写这本快乐之书的过程中,正是我感到抑郁之时”——写作本书是为了找回快乐。如此真实、现实的诉求,正是成就一部佳作的起点。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