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邓鼐的长篇儿童小说《蒲公英花园》(武汉出版社2025年4月版)以盲童学校为背景和舞台,聚焦作品主人公音乐教师章华与视障儿童之间细腻而深刻的情感互动,抒写充满诗意与力量的寓言故事,将声音与光明、自我救赎与教育本质等紧密融合,奏响了一曲动人心魄的生命赞歌;同时,在儿童文学的领域,将笔触探向人性深处那些未被照亮的幽微角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残障叙事的局限。作品中,音乐化身为穿透黑暗的光芒,而教育的本质也在灵动的音符中被重新诠释——它绝非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生命觉醒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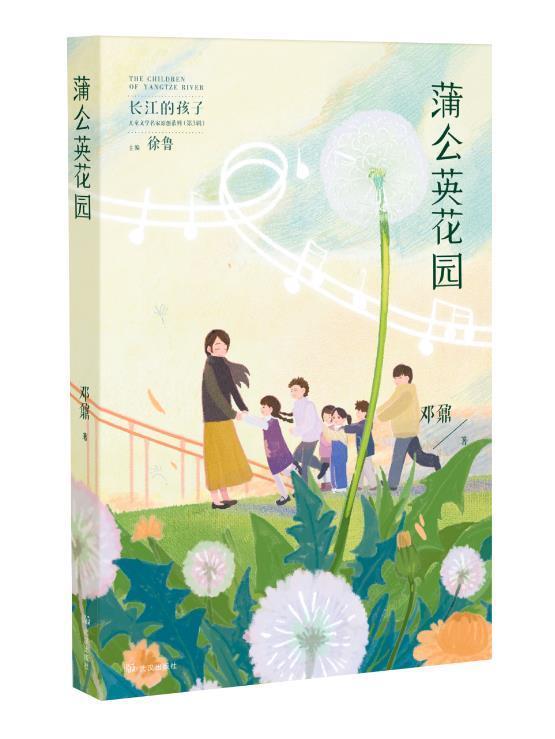
给声音赋能:从补偿到多元认知
《蒲公英花园》最动人的特质,莫过于对“声音”的重新赋能。在视障儿童的感知体系中,听觉非但不是残缺的补偿,反而成为一扇通向丰盈世界的门。邓鼐以人类学的视角,捕捉到这一群体的独特感知方式:琴弦的震颤是形状,音色的冷暖是色彩,合唱的共振是海浪拍岸的壮阔。当章华带领孩子们触摸蒲公英的绒毛时,盲童蕊蕊说那触感“像妈妈的手”;当小鱼从次声波中捕捉到他人未察的震颤时,声音便成为他独享的星空。孩子们甚至能从金属手环的细微嗡鸣中察觉常人听不到的烦躁信号,这种对声纹的极致敏感,让他们在音乐课上仅凭章华拍手的力度变化,就能判断指令的轻重缓急。这些细节,既是对视障群体尊严的敬重,亦是对认知多元性的礼赞——正如普鲁斯特所言:“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大陆,而在于以新的目光看世界。”
当章华握着孩子们的手,轻轻放在震颤的钢琴琴弦上时,那些看不见光明的指尖,却在声波的涟漪里触到了形状。孩子们学着分辨木质的温暖、金属的清凉,就像辨认春草与秋霜的不同呼吸一样。作者没有用悲情的笔调描绘他们的世界,而是让声音变成一串会发光的钥匙——琴键落下时是蒲公英绒毛落在掌心,和弦荡漾时是潮水漫过沙滩的脚印。在这个用耳朵作画的花园里,孩子们把声音揉成柔软的黏土。他们听见月光在低音区流淌成银色的小溪,捕捉到高音里闪烁的星子,甚至能从合唱的共振中触摸海浪的弧度。这些被常人忽略的声纹,在他们心中生长出青苔、云雾和风的轨迹。当小鱼把脸贴在音箱上感受次声波的震颤时,那不是物理课上的频率图表,而是独属于他的、会跳舞的星空。
故事最温柔之处,在于它悄悄擦掉了“残缺”的标签。就像章华常说的,当我们不再执着于“看见”时,才会真正懂得如何“凝视”。孩子们用声音编织的世界,让存在有了另一种注解——或许每个人心里都该留一块这样的花园,在那里,所有的“不够”都能长成新的感官,带我们走向更辽阔的清晨。
声音在此化身为诗意的符号系统,构建起一座隐喻的城堡。章华提出的“推开窗看大海”,表面是发声技巧的譬喻,实则暗含对生命境界的升华。当孩子们以气息共振完成声部协作时,个体的声音并未湮没于集体的洪流,反在彼此的呼应中获得了更辽阔的表达。这种“声音如画”的叙事策略,恰似中国古典诗学中的“通感”传统——苏轼听琴“如见万壑松”,李贺闻砧“寒声带雨山棚湿”——邓鼐则以现代笔法,让声音承载起触觉的温度与视觉的斑斓。
教学双向启蒙:师生共同成长
在传统教育叙事的套路中,教师往往被塑造为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学生则是等待被塑造、被填充知识的客体。然而,《蒲公英花园》果断地颠覆了这一陈旧模式,将教育重塑为一场双向的启蒙之旅。
章华初入盲校时所经历的挫败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她曾引以为傲的音乐教学法,在视障儿童面前却彻底失效,甚至因无法理解孩子们那超乎常人的听觉敏感度而屡屡碰壁。当她发现孩子们能从《春天的芭蕾》的花腔中“看见”天鹅展翅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需要以听觉为钥匙,重新解锁教育的密码。这种挫败并非对能力的简单否定,而是两种认知体系的激烈碰撞——当明眼人依赖视觉构建的教学逻辑邂逅听觉主导的感知模式时,教育的单向性瞬间被瓦解,暴露出其固有的局限与狭隘。
通过多重视角的巧妙交织,作者深度挖掘了这种碰撞背后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从章华的视角,我们目睹了一个教师如何艰难地放下“拯救者”的傲慢与偏见,转而以谦逊的姿态成为学习者;从孩子们的视角,盲态背后那些隐秘的心理阴影逐渐浮出水面——大磊因所谓的“木耳朵”而深陷自卑,小鱼对黑暗的恐惧,实则是对社会偏见那无形枷锁的无声反抗。最具张力的一幕,当属合唱团参赛时,孩子们毅然决然地摘下象征特殊照顾的标签,以“普通合唱团”的身份自信登台。这一选择,无疑是叙事的高潮,更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叩问:真正的平等,绝非同情式的包容,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无差别竞技。于是,教育便超越了知识与技能的简单传授,升华为对生命尊严的坚定捍卫,成为照亮每个孩子心灵的温暖火光。
蒲公英意象:从困境到诗意飞翔
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残障题材的书写常常陷入两种极端的漩涡:要么沉溺于对苦难的过度渲染,以博取同情之泪;要么流于空洞的励志鸡汤,将复杂的人性简化为单一的奋斗与成功。而《蒲公英花园》的独特之处,在于借“蒲公英”这一意象,为残障书写开辟了一条从困境通向诗意的路径。
蒲公英,既是孩子们合唱团那充满希望的名字,更是贯穿全书的灵魂所在。它的种子,看似脆弱无比,却能在风的助力下自由飞翔,落地生根,绽放出顽强的生命力。孩子们在花园里吹散蒲公英时,会循着飞絮的触感哼起不成调的歌,那些洁白的绒毛落在脸上,成了他们“看见”飞翔的方式。这种轻盈与坚韧并存的特质,与视障儿童的生存状态形成了绝妙的共鸣。
小说中,蒲公英的意象多次与“光明”相互交织、相互诠释。章华在梦境中对飘散的蒲公英花瓣的追逐,隐喻着她对完整生命的无尽执念;孩子们在舞台上那勇敢的一摘,摘下的不仅是墨镜,更是挣脱“被凝视”命运的束缚,宣告着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坚定追寻。最为深意悠长的一幕,当合唱团在国际比赛中载誉而归时,舞台上飘落的不是俗套的鲜花,而是蒲公英那洁白轻盈的飞絮。这一场景,彻底将残疾叙事从“克服缺陷”的悲情框架中解放出来,转而高扬生命的自在之美——恰似蒲公英,无需迎合土地的期待,它的价值就在于那无畏的飞翔本身,向着未知,向着自由。
复调与通感:独特魅力的双翼
《蒲公英花园》的艺术魅力,不仅源于其主题的深刻洞察,更得益于其精湛的叙事技巧。作者采用复调叙事结构,以章华的教学历程为清晰主线,巧妙穿插孩子们的内心独白与家长的社会视角,构建起一个有机的、多声部共鸣的叙事世界。
例如,小胖沉迷于网络直播却又最终回归合唱团的情节,既是对他个体在名利诱惑下的迷茫与挣扎的生动展现,又深刻揭示了底层家庭在面对残障子女教育时所承受的沉重生存焦虑;校长从最初的质疑到后来的全力支持的转变,则暗含着体制内教育者对特殊教育价值的重新认知与思考。
在语言层面,作者善用通感手法,巧妙弥合视觉与听觉的界限。当描述音乐时,“童声如露珠滚过荷叶”“合唱声浪像春潮漫过堤岸”等新奇的比喻层出不穷,让声音具备了触觉与视觉的质感。孩子们唱《西北雨》时,“直直落”的旋律让他们摸到雨滴的冰凉,“火金姑”的唱词让黑暗中浮现出萤火虫的微光。这种语言实验,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与感染力,更以一种极具创意的方式暗示了感知世界的多元可能——当一种感官暂时关闭,其他感官便以更敏锐、更丰富的方式打开,去探索那广阔无垠的世界。
结语:光明的种子与飞翔的宿命
《蒲公英花园》最终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充满希望与力量的结论:生命的残缺或许是无法改变的宿命,但对美的感知与不懈追求,却能让人超越生理的局限,触摸到那永恒的光明。当章华在完成她的使命后悄然离开盲校时,她的背影与孩子们在舞台上绽放的光芒形成了一幅极具象征意义的画面——教育者的价值,不在于永恒的陪伴,而在于播下希望的种子后,默默等待它在适当的时候破土而出,绽放光彩。就像她教会孩子们在黑暗中通过脚步声定位彼此,这种无需视觉的默契,终将成为他们独自飞翔时的隐形翅膀。
邓鼐的儿童文学书写,既是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继承,亦是对现代教育困境的回应。这部作品,恰似一曲余音未了的交响乐,其尾声不在纸页之内,而在每个读者心中回响——提醒我们:真正的光明,未必依赖双眼;而生命的原野,永远向无畏的飞翔敞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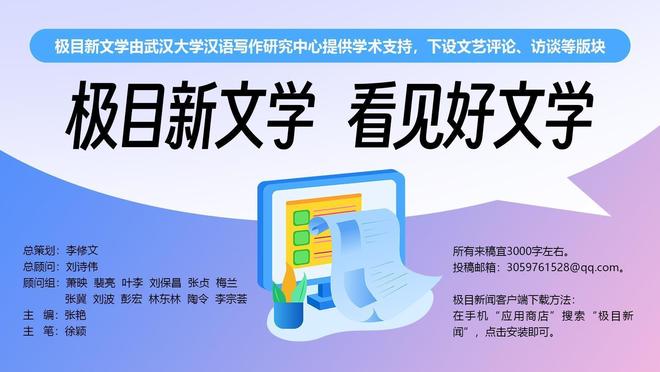
(陈婉清,芳草杂志社编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在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武汉市评论家协会理事,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文艺报》《收获》《山花》等报刊。)
(来源:极目新闻)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