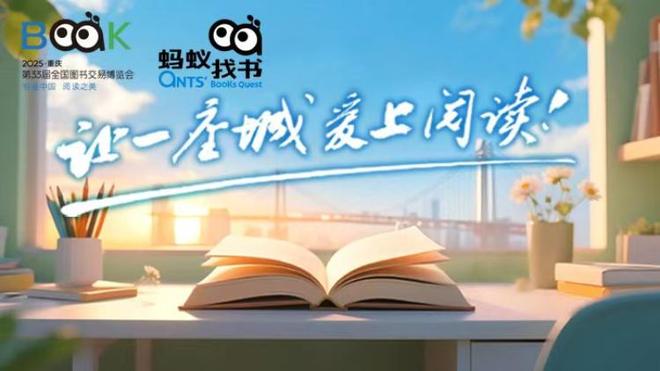
书香漫过的岁月
文/蒋萍
重庆的暑气是不讲道理的,像在蒸笼里浸过的绸缎,闷而湿地包裹着整个城市,再沉甸甸地压在皮肤上。这样的日子里,没有什么比冷气裹着墨香的书店更适合悠闲度日的了。顺着冷气的纹路,岁月里的旧时光一点点漫了上来。
童年的书报亭支着褪色的灰布篷,老板总是随手翻看着报纸,散漫地等待着来客。我总在书柜前磨蹭,指尖划过每本杂志的脊线,仿佛书架上放的不是书,而是满架的热闹——《读者》的温情与智慧,《意林》的机敏与创新,《故事会》的人间百态……
从学校到菜市场的转角,有一家广益书店,我放学后总会在书前逗留,那时妈妈还没工作,爸爸一个月才三百块左右的工资,往往我会存下零花钱,挑选半天才狠下心买一本,留着短发的老板娘总是微笑着等我看书。记得小学毕业,我特别痴迷于看《男生女生》(金版),里面不是充满套路的青春文,而是各种诡异恐怖的推理悬疑文,几乎每一期我都会买,权当盛夏的空调。以至于后来不等我开口,老板娘就会把新到的《男生女生》给我留着。
上初中后,妈妈怕耽误我功课,便将我的书都关进了“小黑屋”,可那些印着故事的纸页像吸铁石,让我总忍不住迈开步子。
晚自习前的饭钱是三块,我就精打细算,只买个一块钱的面包或饼干,正好节约吃饭时间边写作业边在心里盘算:三天,差不多就能换一本杂志。这样的结果自然是——饿,晚自习回家后我总要再吃一碗酸豇豆面,连汤都喝得精光。且衣柜里藏书的衣服已经遮不住这些买来的书了,比侦探还“贼”的妈妈自然猜到了我悄悄攒钱买书的秘密。
没想到低着头等着被数落的我听到的只是妈妈的叹息:“人家都是买零食,你倒好,买一堆不能吃的书!”不过,第二天中午,我仔细一数晚饭钱,五块!还没抑制住心里的惊喜,妈妈便推着我出门:“要买书就说,别再饿肚子了。”原来“虎妈”的爪子里,也藏着棉花般柔软的心。到大学后她还总笑我:“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以后得喊个棒棒来扛哦。”话里带笑,眼里却亮闪闪的。
对我来说,那时的书真的就像黄金屋,我所有的教参和下学期的预习课本都是找别人借的,那时我便明白了“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借来的总要掐着归还日期拼命读,那种又甜又急的痒,比吃了颗没化完的糖还让人惦记。直到多年后才懂,那是灵魂初次尝到牵挂的滋味。
再后来,超市楼上开了新华书店,背着书包浸泡在书海,那里就是我的另一个天堂了。
对着字典啃《红楼梦》,囫囵吞枣地看名著,丝毫没有看懂人情世故或豪情壮志。有时看得腿麻,就蜷在地板上看小人书:《江姐》里的竹签,《鸡毛信》里的羊,《小萝卜头》的铅笔,都比课本的背诵全文鲜活有趣。
我常站着挑选,等看得入迷就寻个角落坐下,背靠着书架,一翻书就忘了时间。
一次看老师推荐的《边城》,只记得湘西的溪水好像从纸里流出来,四周都是美景与朴素的风,翠翠站在渡船上,和我一样懵懂,只是我不懂,为什么翠翠不能像我一样,跟喜欢的朋友一直玩下去?想着想着,窗外的天就暗了,惊觉整个书店只剩我一人时,妈妈的脚步声也近了:“看啥子哦,饭都搞忘了吃!”当然,我妈妈总是知道挨着一家家书店找我,就像去一个个网吧逮我弟弟一样。我对书的痴迷,我父母都无法理解,毕竟他们并不爱看书。
从长春来的支教老师说:我还是第一次见树在冬天还是绿的!我忽然懂了《在山的那边》——诗里的他乡,原来就是脚下的故乡,每个思想在文字碰撞中总能有不同的情感经验。
大学时,我常在轨道交通列车上读书,因为没有汽车那么颠簸,不会晕车,每次都觉得回家的距离太短,书都没看完就到了。
儿时总幻想有座图书馆,书多得看不完。现在,书店那窗明几净的读书环境,算圆了我儿时的梦。就连县城都有了宽敞的阅览室,用笔记本办公的年轻人正用移动图书馆写着大学的作业。现在除了收藏的纸质书,我也常用墨水屏阅读器,在放假时用电磁笔备课做批注。我从不强迫学生阅读,毕竟每本书都有它喜爱的读者,这才是百花齐放的美。
书脊在时光里慢慢泛黄,然而文字依然如同星辰,不论山水,不论贫穷富有,始终照耀着每个心灵,让每个时代的灵魂都保持着相同的温度。此刻,阳光斜落在书页上,坐在一角的不正是我教过的学生吗?在如此明亮的时代,随着一页页翻书声,仿佛我们早已走过万水千山:广益书店的挑选、借书的牵挂、妈妈的理解、新华书店的等待、轨道交通列车上的静谧……那些书香岁月,早把一座图书馆,砌进了心里。
作者简介:蒋萍,笔名小夭,重庆市丰都县作协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现任教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建乡蔡森坝完全小学校。作品散见于《中学生博览》《外国文学》《文学家》等。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