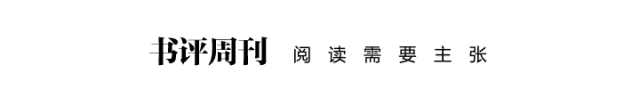
我不在墙上挂日历了,不再挂了。
前些年每年都挂日历,但总是忘了翻页,常常想起时,日历仍停在两三个月前。谁会真的在乎日历上的数字?
日历和日子不是一回事。日历上排列整齐的数字,几月几日星期几,那些数字在印出时就已经死了,一堆日期的尸体。
我之前挂日历不是为了看日期,是为了看画,日历是墙上的装饰而已。然而,最后连画也看腻,视而不见了。
撰文 | 三书
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

南宋 李德茂《芦洲蜂蝶》
《蝶恋花·春暮》
(南唐)李煜
遥夜亭皋闲信步,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
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
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低低语。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还是空白的墙更好。
谁说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人类没有日历也照样生活了成千上万年。没有日历,我们活得更完整,更天人合一。
让我们忘了日历,感觉一下什么是日子。古老而新鲜的日子,永远是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即便有,过去未来也与现在同在。日子不在乎今天是几月几号,也不匀速前进,有时快些,有时慢些,有时好像悬在某种永恒。
李煜这首词写一个春天的夜晚,他独自在亭皋闲步,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事情发生时,自然界就会向我们敞开,万物才会真正被看见,我们也才能听见寂静之声,那更深的音乐。
先来看后主对这个夜晚的命名。“遥夜亭皋闲信步”,遥夜,一般注释为长夜或深夜,意思接近,但读诗读的不是意思,是意味,是感觉。遥夜而非长夜,肯定有遥远的意味。“遥远”既可以用于空间,亦可用于时间。想象一个那样的夜晚,你睡不着,独自在户外踱步,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也不知身在何处,此刻离一切都很远。这大概就叫“遥夜”。
当一切离得很远,你就会离自己很近,离时间很近。你的呼吸变得无比真实,而时间呈现出虚幻的本质,你恍惚不再知道自己是谁。可惜后主没能进入那种恍惚,对人间的眷恋把他困在这里。
“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这两句的语气,无限嗟息,才过清明节,忽然已是暮春,花谢纷纷。“早觉”,有的版本作“渐觉”,若是渐觉春暮,就不会说“才过”,诗句也就不是诗句,而成了散文。
光阴似水,愈想珍惜,愈觉流逝。“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数点雨声,为风收住,残云映以淡月,疏疏来往。片时佳景,过眼皆空,不能不使人心惊。
仰观之后,再看周围,夜色中树影重重,花香愈浓。“桃李依依春暗度”,这句听得见季节齿轮的转动。桃李依依,指的是香气,花香如在挽留,如在告别。
“谁在秋千,笑里低低语。”秋千有一种纯真之美,出现在诗词里尤美。苏轼的《蝶恋花》写春景,亦写到秋千,词曰:“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都是女子在荡秋千,但闻其声不见其人。苏轼写的是昼景,且带点戏谑的味道,“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此自是一种风流,不知是在嗔怪墙里佳人还是在嗔怪春天,这里的不分明颇妙。后主词写的是夜景,影影绰绰,低低语笑,更觉得好,且词中亦恼:“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这首词作者存疑,通常依《全唐诗》和《尊前集》记载,认为是南唐后主李煜。也有认为是李冠或欧阳修的。我们在此归于李煜,因其清丽疏淡,缠绵哀婉,与后主词相类。不过不必较真,一首好诗既不属于时间,也不属于某个人,一首好诗属于它自己,而我们爱的也是诗本身。
笙歌散尽,始觉春空

清 邹一桂《杏花燕子图》
《采桑子》
(宋)欧阳修
群芳过后西湖好,
狼籍残红,飞絮濛濛,
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
始觉春空,垂下帘栊,
双燕归来细雨中。
欧阳修语出惊人,百花凋零之后,正伤春时节,他却一反常情,说道:“群芳过后西湖好”。何以见得?
且看西湖此时:“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这里的西湖,不是杭州西湖,乃是颍州西湖,在今安徽阜阳西北,宋时极游观之盛。1071年,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致仕,退居颍州,寄情湖山,作《采桑子》十首。
游春盛况已去,西湖归于空寂,这首词写的便是静境。狼藉残红,飞絮濛濛,欧阳修的语气,感觉并非凄凉,而是热闹之后的轻松。坐在湖边,春风拂面,风中垂柳阑干,飞絮濛濛,与盛游相比,别有一番情味。
下片人去春空,“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诗的声音在于“始觉”,有忽然之感。虽然狼藉残红,但笙歌游人未去,春天便还是繁华的,纵使已至暮春,也竟浑然不觉。而当笙歌散尽,游人皆归,只剩下西湖,柳絮飘飞,此时才觉得空。
这种感觉很像我小时候过年,初七初八亲戚差不多都走完了,年味其实已经很淡,但因每年正月十二要唱大戏,所以仍觉得在过年。那种暂得长久的窃喜,延续到正月十六,戏一唱完,年就彻底过完了。戏台拆走后,留下空空的场地,总令我惆怅不已。
欧阳修晚年参禅,悟透悲欢离合,这首词写暮春,取境不俗,无甚惜花伤春之态,反觉旷怀。结语“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更加疏淡,至寂之中,真味无穷。
《采桑子》十首,可谓欧阳修晚年一大力作,组词前有一段“西湖念语”,类似开场白,交代了创作缘起与心态,语曰:“西湖之胜概,擅东颍之佳名。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
宋代民间有联章体鼓子词,即联合两首以上同样词牌的词,歌咏同类事物。欧阳修这组词合咏西湖美景,为文人创作联章体词立下典范,其后效仿者众。
晚春绝句二首

清 恽寿平《落花游鱼图扇页》
《晚春》
(唐)元稹
昼静帘疏燕语频,双双斗雀动阶尘。
柴扉日暮随风掩,落尽闲花不见人。
元稹诗中的晚春真静,他好像来到了一处弃屋,主人不知去了哪里,只剩下自然界的草木鸟雀,当然还有风。吹过弃屋的风,使弃屋更空。
空屋令人徘徊,看门前台阶,看这柴扉,依稀想见这里曾有过的生活。晨昏四时,炊烟人语。庭院里树还在,花开花落,春去春来。
初读这首绝句,我想到的就是以上情景,因为弃屋对我有莫名的吸引力。无论何时何地,看到弃屋我总要停步,倒不是嗟叹沧桑,甚至不觉得荒凉,而是耽于那寂静,耽于循着遗迹去回想。这并不难,想象就是回忆,回忆亦即想象。
然而,元稹也许不是这个意思,读第二遍,我感觉到诗里有人,不是诗人自己,而是一个女子。她坐在房里,垂下疏帘,我们看不见她的样子,但听得见她内心幽怨。她的心声由诗人代言,一个表达别人如同表达自己的人,便是诗人。
以女子的视角,再来读这首诗,意味与弃屋不同。弃屋里没有人,亦空亦满,而有人却如同没人的屋子,亦满亦空。昼长人静,她却是个无聊赖的存在,帘子放下,疏处透进日光,檐间燕语频频。雀子在檐阶争斗,扬起尘埃。这些都是活的,幸福的燕子,欢快的雀,美丽的尘埃。
贫穷的柴扉,也是可爱的。“柴扉日暮随风掩”,天要黑了,一阵风把柴扉掩上,这风也是有情的。最后,“落尽闲花不见人”,此人应是女子的意中人,等了一个春天,他也没有来,花成了闲花,花的情意也荒失了。春天就要过去,眼看花落尽,仍不见他来。
韩愈的《晚春》绝句,没有这般悲哀。“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诗中的晚春,仿佛大舞台,草树都努力在台上表演。拟人手法,虽然活泼,却不怎么有趣,我嫌他说得太尽,嚼破则无味矣。
三四句写杨花榆荚,语气调侃,意似讥讽,不知究竟何所指。明末清初文学领袖朱彝尊评最后两句,曰:“此意作何解?然情景却是如此。”(《批韩诗》)不强作解人,批得真好。
春天就这样,日子被打开,那些死去的,或者我们以为死去的,那些记忆和欲望,再次被唤起。水流花开,草长莺飞,春天完成它自己。
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艾略特的意思,我想是在询问生命的意义。当神性被放逐,在这崎岖的荒原,生命为什么还要发芽,为什么还要开花?作为人类,我们无法得知,无法猜测,因为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一堆破碎的形象。
重回诗经原野
看天地镜像
听万物回响
“周末读诗”第三辑
《既见君子》
(点击封面可购买)
《既见君子:诗经十五国风行读》
作者:三书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5年1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三书;编辑:张进;校对:赵琳。封面图为傅抱石画作《柳畔》,有裁剪。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推广。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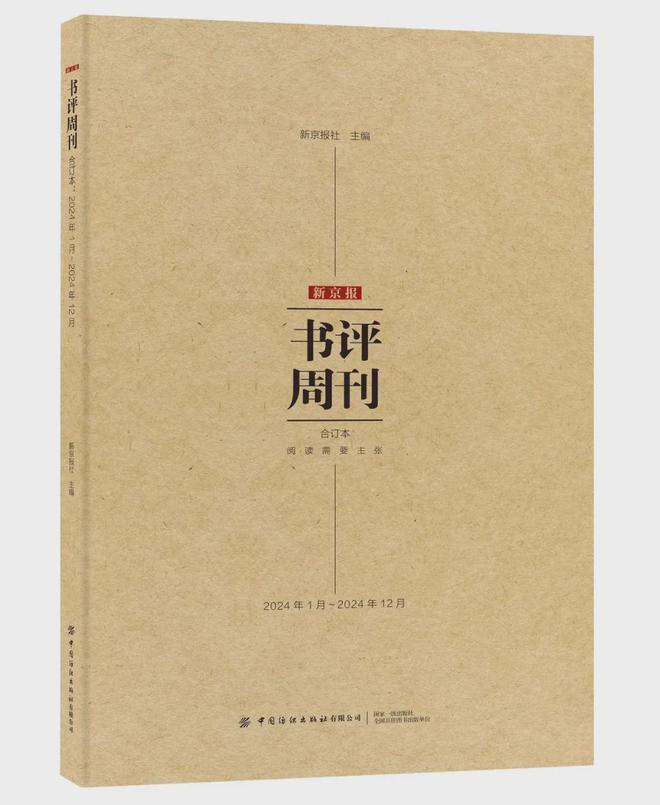
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
(文化责编:王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