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到热度过去,网络的水面又渐渐恢复表面的平静,埋葬了这一个别里科夫之后,又有多少个隐秘的眼神在等候着下一个套中人的浮现呢。」
“你的倒计时已经在倒计时了”
“是的,我就是你们的小蓝姐姐廖景萱……小蓝姐姐为什么非得我演?”

最近,《巴啦啦小魔仙》小蓝姐姐的扮演者廖景萱再度出圈。
最开始人们认识她是《巴啦啦小魔仙》中聪明、勇敢、善良的“童年白月光”小蓝姐姐,她不仅是主角成长的护卫者,更是人们现实中对“大姐姐”形象的理想化投射。
在出演《巴啦啦小魔仙》之后,廖景萱没有继续走红,逐渐从公众视野淡出。但最近,一些未被实锤的负面传闻和在直播中一直“吃老本”、蹭小蓝姐姐热度的话题再度把廖景萱推上舆论的热潮。

(廖景萱在《巴啦啦小魔仙》中饰演魔仙小蓝)
有人觉得她在“贩卖童年情怀”“吃‘蓝’血馒头”,有人并不善意地调侃“廖景萱第10086次首谈出演小蓝姐姐”“廖景萱好像被恶毒女配‘夺舍’了”,也有人在她的直播间开黄腔、造黄谣,对这么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进行人身攻击。
人们一边诋毁着她,同时又一边高高举起,掀起一阵又一阵“怀念小蓝姐姐”“可是廖景萱的遗憾又是什么呢”的热潮,用共情的表象遮掩消费他者的实质,不知疲倦地制造着“套中人”。
01
反向“神化”:观看与被观看的权力关系
这回,小蓝姐姐扮演者廖景萱因为一些直播翻车的抽象梗“翻红”出圈,在网上被一些亚文化群体列为和三梦奇缘、万人迷、完颜慧德等并列的“新赛季新英雄”,还大批量地传播她诸如“你的倒计时已经在倒计时了”的直播切片。
这种现象看似是在“造神”,但其实是一种反向的神化。网友们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个人魅力、社会价值等而认可和崇拜她,而是建立在一种审丑逻辑上的恶搞,表面上高高举起、奉为icon,但实则是将其归为“异类”、对其人格进行了降格。

(以”幻神“知名,行侮辱之实)
这种神化与被神化之间包含着一种不对等关系。廖景萱、三梦、完颜慧德、那艺娜,她们大多出身普通,学历不高,媒介素养也比较有限,她们的语言行为与主流网络的那一套存在着一定延迟和错位。
这意味着她们对互联网爆炸一般更新着的热梗和套路的应对能力是比较低的,她们暴露在高度曝光的直播间里,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和权力,一举一动被人拿着放大镜观看。
而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则如同开了“上帝视角”,他们熟知互联网的语言、“梗”的传播规律以及对一些细节进行二次加工的技巧,和被观看的对象之间拥有着不对等的视觉关系,这给人带来一种支配感和“全知全能”的错觉。
有人顶着一些负面、甚至有人格侮辱意味的昵称刷礼物,让对方在不明所以之中大声念出来;有人造黄谣、开人身攻击的玩笑;有人诱导ta们做出奇怪的动作、表演歇斯底里,或者在二创的时候对ta们进行恶搞丑化式的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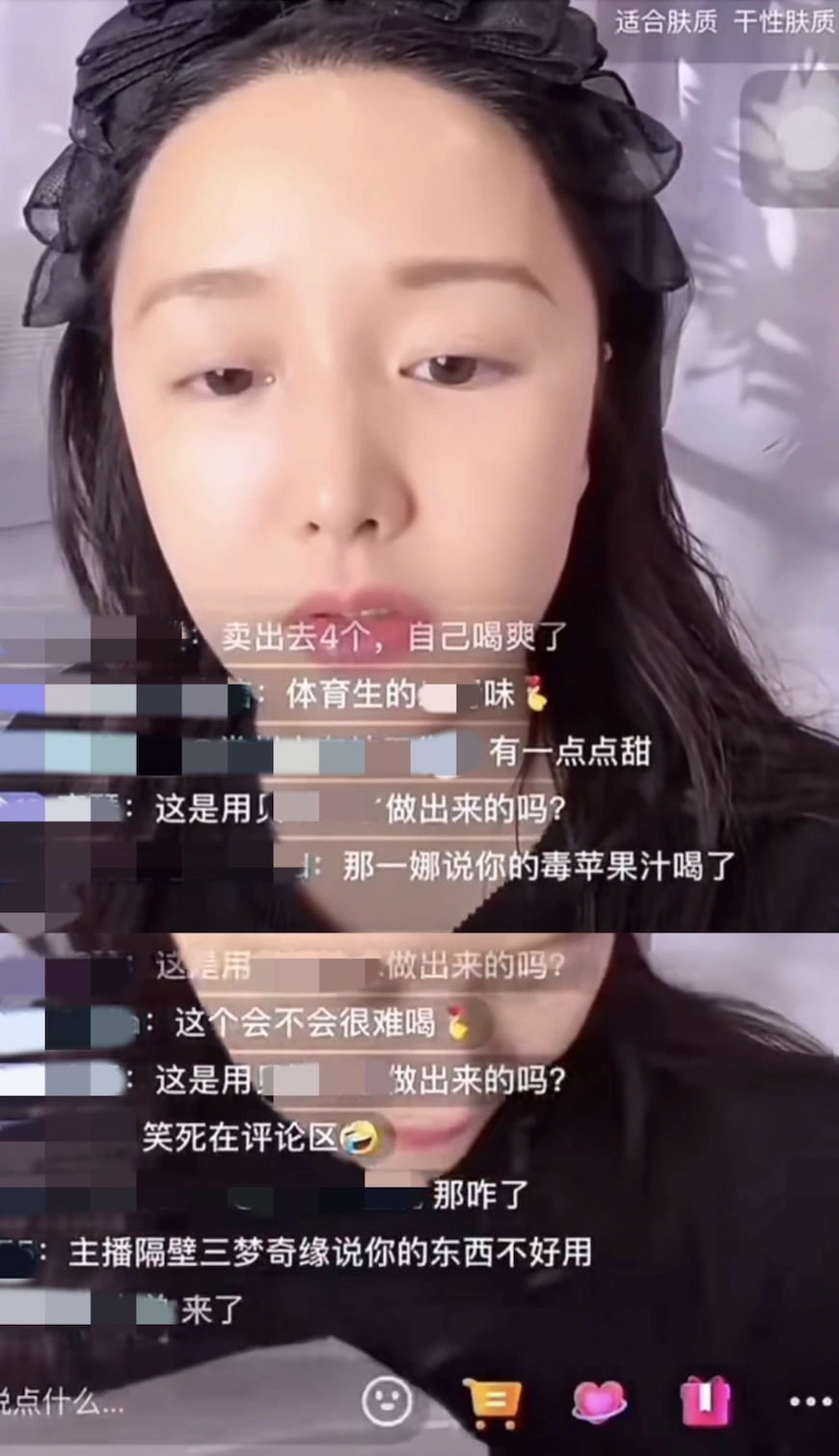
(廖景萱直播间中恶意的弹幕)
这在某种程度上算得上是一种网络层面的欺凌。一个人处在一览无余的暴露环境中,另一部分匿名者可以随意对其凝视、调笑和“狂欢”,不假思索地参与这场平庸之恶。关于观看与被观看的全景敞视的监狱里,直播间的每个人都是那个身居高位、睥睨而视的巡逻者。
这种反向神化的后果就是对被神化的对象造成更深的剥夺感,让其彻底丧失自我定义的力气,只能活在一个个梗和黑图里。
就如同契诃夫写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别里科夫被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社交习惯所“套住”,而网红们也被这种外界强加的定义和人设“套住”,或许也曾感到不适,却又无法完全脱下,有不能,也可能有不想,因为一旦脱下这层“套子”,便意味着失去互联网意义上的不可代替性、关注度和收入来源。

(“套中人”别里科夫)
于是ta们无法剥离这种时刻进行表演的义务,就像别里科夫一样,逐渐地将这个“套”内化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学会了顺从,学会了自嘲,学会了迎合。这是一种精神与人格层面的折损,ta们不再被当做一个真实的“人”来理解和接纳,别人只看到最表层的那一副壳。
而等到热度过去,网络的水面又渐渐恢复表面的平静,埋葬了这一个别里科夫之后,又有多少个隐秘的眼神在等候着下一个套中人的浮现呢。
02
再造网红:人格化与道德化的心理“赎罪”
网友们一边对小蓝姐姐进行着一种反向的神化,将她的行为当作猎奇、调侃和二创的素材,一边又同时说着“小蓝姐姐就是我的‘亡妻回忆录’”“对小蓝姐姐滤镜太大了”“不管怎样,小蓝姐姐永远是我的白月光”“也许廖景萱只是有一点不甘心”,为廖景萱献上了同情、理解和所谓的尊严。这是一种人格上的双重“再造”。
这个过程在很多网红身上都被操演过。完颜慧德凭借有些“滑稽”的方言口音和古板的行为火了之后,抖音为她拍了一个个人纪录片,里面揭露了她不完美的原生家庭和孤僻不合群的性格,随后网上一大片“原谅”“共情”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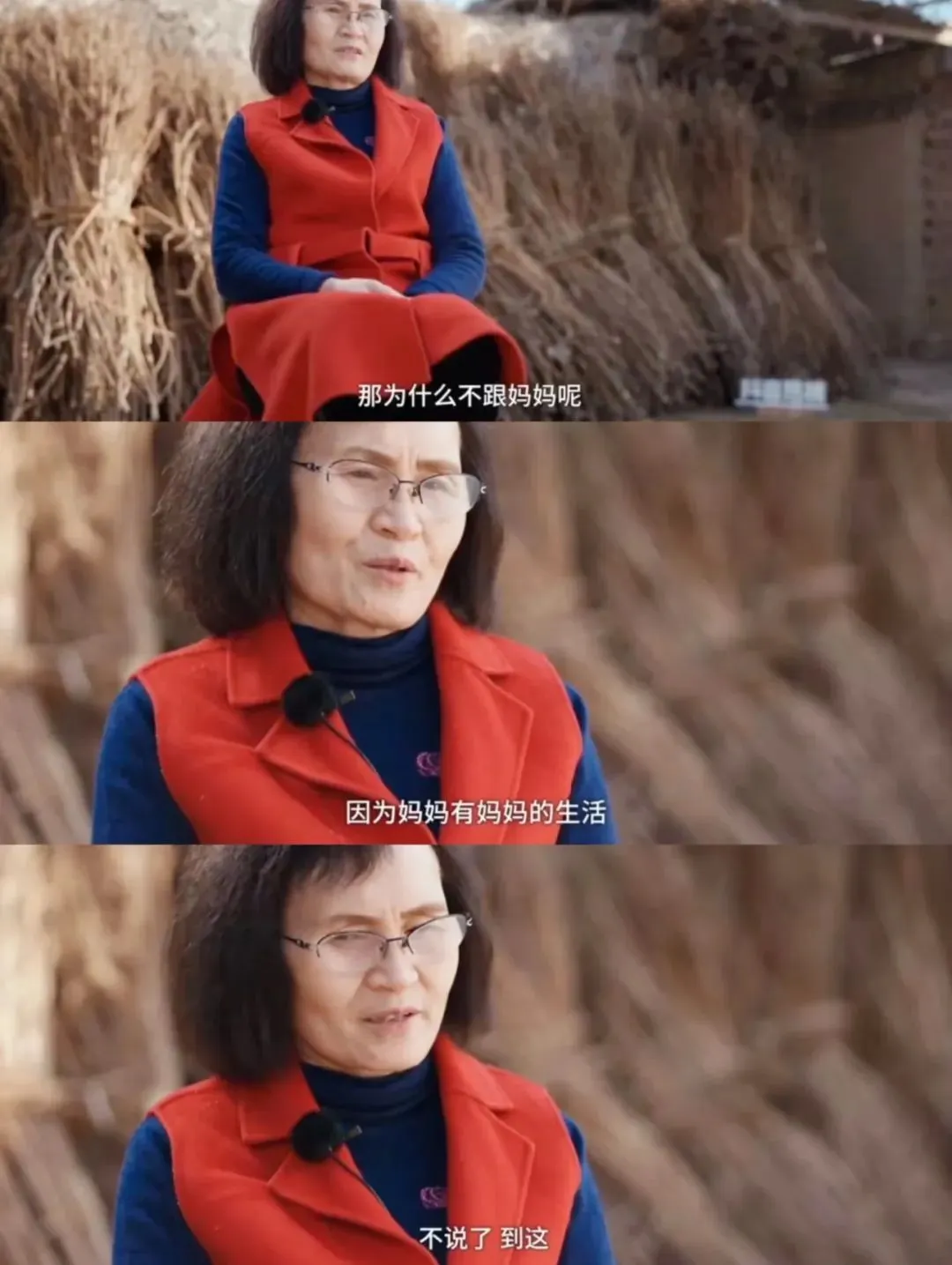
(纪录片《完颜慧德很烦恼》)
智博在她的纪录片里说着“就是不想被生下来”,揭着自己失败的亲密关系、求爱而不得的伤疤;

(纪录片《荆棘鸟受伤了》)
迅猛龙特蕾莎在考研复旦成功之后诉说着和母亲之间紧张的中式教育关系;

(纪录片《生活闪亮时》之美丽的收获)
小蓝姐姐廖景萱也是,凭借“抽象”和下沉的梗在网上火了之后,马上就有一批“白月光”视频出现……

(怀念小蓝姐姐的视频)
当下,一个“网红”通过反常规、非“主流”的行为火了,人们乐于见得将其“非人化”、夸大ta身上的“不正常”,咀嚼着这些互联网带来的人之“猎奇”性,但这达到某个阈值之后,人们立刻会有一些行为再将这个人物重新赋予人格化、道德化。
但有趣或者矛盾的是,人们最开始关注这个人物的出发点和道德、人格完全无关,甚至恰恰是因为ta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常规道德、反正常人格的。
或许这是一张作为“观者”的网友们心理上的赎罪券。这些网红最初能够走红一部分原因是ta们的某种“失格”,人们去道德化地、无负担地消费着ta们的话语逻辑、抽象行为甚至长相外貌。
但长期如此就会给人带来道德层面的不安和压力,所以又开始对这些网红进行心理上的补偿和单方面的致歉、进行一些典型的伤痕叙事式的再造,捏泥人一样为ta们找补上距离“常人”的残缺的一角。
人们再一次拿起放大镜,但这回寻找的是ta们的童年阴影,原生家庭,容貌焦虑,情感创伤,自卑与超越……
但这种失控和调适的一来一回的操作同时也暴露了当下社会对人的评价体系的单一。大众对“人”的想象还是二元的,要么可怜可笑可悲,沦为互联网上的“小丑”,要么可歌可泣可敬,凭借着创伤故事升华人格。
那些原本复杂模糊的个体在网络上只能以这两种方式存在,表面上人们在追捧新偶像,但实则仍在套用旧道德。

(完颜慧德说)
就像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与怪物一样。弗兰肯斯坦人为地“制造”出所谓的怪物,却不愿承担情感上和伦理上的责任,“怪物”在经历抛弃和非人化之后最终因为无人给予情感上的确认和回应,走向了自我毁灭。
在这场弗兰肯斯坦式的、一场关于梗与人设的“实验”之中,网友们一边以他人为“养分”创造着笑料,一边又试图从笑料之外再索取出眼泪和共情,洗白自己曾经消费一个他者的事实。
故事的最后,这个到死都没有名字的怪物说,自己将驾着一艘冰船驶向北极深处,在那里点燃柴堆,让火焰吞噬自己的身体,彻底消失在世界上。他说:“我的灵魂将得以安宁,即便它仍能思考,它也绝不会再像这样思考。”
我们似乎越来越习惯把人当作工具或载体,承接我们的笑、我们的痛、我们的爱与恨。在这样的循环中,我们既是弗兰肯斯坦,又是怪物,我们既在“制造”,也在一直一直地被抛弃。
(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
来源:知著网
(娱乐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