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屏银幕,观众终于喊出了那句“够了”!
电影院的空调还在呼呼吹着冷风,小王却攥着《酱园弄》的票根出了一身汗。不是因为剧情有多紧张,而是当镜头又一次怼向雷佳音那张略带疲惫的脸时,他突然想起早上刚刷完的《长安的荔枝》——同样的眉头紧锁,同样的欲言又止,就连叹气时嘴角下拉的弧度都分毫不差。“这哥们是把一个角色演了十遍吧?”散场时,后排观众的吐槽精准戳中了他的心声。这个七月,雷佳音的曝光度比40℃的高温预警还密集,可观众的耐心,早就被这份“密集”烤得冒烟了。
 三年前,观众提起雷佳音还带着点宠溺。《我的前半生》里的陈俊生,把“窝囊渣男”演得让人心疼,超市里捏碎方便面的名场面,甚至成了打工人宣泄情绪的模板。那时候大家爱叫他“大头”,觉得这称呼里藏着“接地气”的亲切感。可现在打开社交平台,风向早就变了——“建议雷佳音直接承包央视一套到八套”“水浒传108将他一个人能演70个”“看到他皱眉就知道,这角色又要受气了”。这些带着戏谑的吐槽,藏着观众最真实的疲惫。
三年前,观众提起雷佳音还带着点宠溺。《我的前半生》里的陈俊生,把“窝囊渣男”演得让人心疼,超市里捏碎方便面的名场面,甚至成了打工人宣泄情绪的模板。那时候大家爱叫他“大头”,觉得这称呼里藏着“接地气”的亲切感。可现在打开社交平台,风向早就变了——“建议雷佳音直接承包央视一套到八套”“水浒传108将他一个人能演70个”“看到他皱眉就知道,这角色又要受气了”。这些带着戏谑的吐槽,藏着观众最真实的疲惫。
细究起来,雷佳音的角色库确实像被按了复制粘贴键。《长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是个被官场压榨的小吏,背着手踱步时的佝偻劲儿,和《人世间》里的周秉昆如出一辙;《第二十条》里的检察官,表面唯唯诺诺,骨子里藏着执拗,活脱脱是《热辣滚烫》里那个窝囊教练换了身制服。有网友统计,过去三年他主演的18部作品里,有14个角色带着“憋屈”“隐忍”的标签,重合度高到让人恍惚——到底是角色需要雷佳音,还是雷佳音只能演这类角色?
更耐人寻味的是观众态度的转变。2017年陈俊生走红时,恰逢“丧文化”流行,大家在这个“窝囊前夫”身上看到了生活的无奈,甚至生出“他比那些油腻霸总真实多了”的好感。可到了2024年,当“内卷”“躺平”成了高频词,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还是同款“窝囊”时,共情就变成了反感。“白天在公司受气,晚上回家看电视还得看他受气,这日子没法过了”——某平台高赞评论道出了核心:观众需要的是情绪出口,而不是反复咀嚼别人的窝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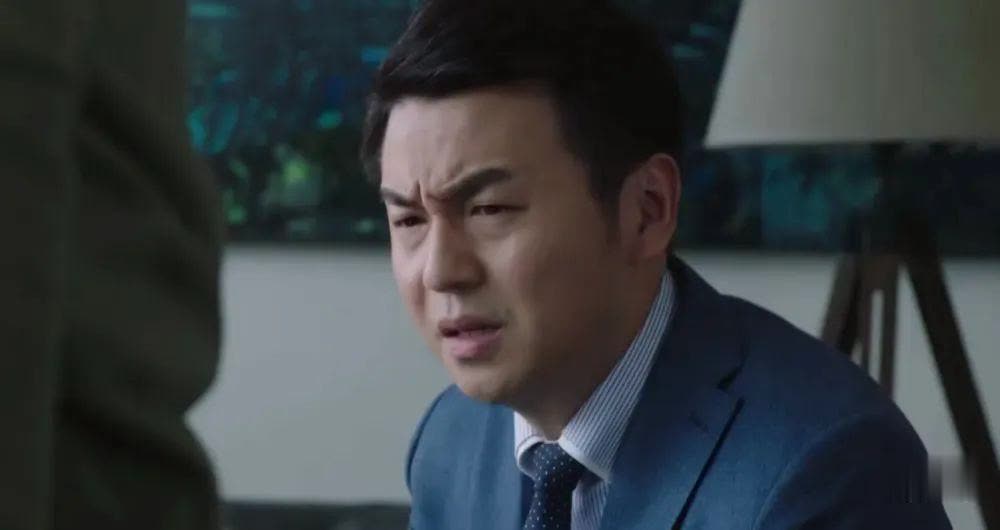
雷佳音不是没有能力突破。《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张小敬,糙汉的狠戾与柔情被他演绎得入木三分;《绣春刀2》里的裴纶,吊儿郎当的外表下藏着精明,至今仍是影迷心中的“白月光”。可这些“非窝囊”角色,在他近年的作品列表里像稀有动物。有人说是他被舒适区困住了,也有人说,是市场主动把他推进了这个“窝囊”的牢笼。
当观众还在纠结雷佳音的角色重复度时,圈内人早就看透了这背后的逻辑。某影视公司制片人私下透露:“现在谁敢用没经过市场验证的演员?雷佳音这样的,演技在线,没绯闻没黑料,性价比高到离谱。”这番话揭开了一个残酷真相:雷佳音的“霸屏”,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而是资本在风险与收益间算的一笔精明账。
宁浩和雷佳音的交情,堪称娱乐圈“资源置换”的典范。2011年《黄金大劫案》选角,徐峥一句“我认识个叫雷佳音的,戏不错”,让这个当时还在跑龙套的演员拿到了人生第一个男主。为了报恩,雷佳音在《心花路放》里零片酬客串了个小混混,镜头不多却成了经典。这种“互相成就”的模式,在圈内迅速发酵——《绣春刀2》原定反派演员临时罢演,监制宁浩第一时间推荐了雷佳音,结果裴纶这个角色成了影片最大亮点。从那以后,“宁浩系”的作品里总有雷佳音的位置,与其说是情谊,不如说是“自己人用着放心”。

更关键的是那层绕不开的资本关系。自由酷鲸影业的股东名单里,雷佳音的名字赫然在列,而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正是导演路阳。《刺杀小说家》《长安的荔枝》这些“路阳作品”,与其说是找雷佳音主演,不如说是股东给自己“加戏”。有业内人士笑称:“别人是跑组试戏,雷佳音是坐在办公室看剧本挑角色。”这种“既是演员又是老板”的双重身份,让他在资源争夺战中占尽先机。
就连张艺谋的“谋男郎”头衔,也藏着资本的蛛丝马迹。欢喜传媒的股东名单里,张艺谋、宁浩、徐峥的名字排在一起,而雷佳音与宁浩的铁关系,让他顺理成章地成了“自家人”。《悬崖之上》里的张宪臣,《满江红》里的武义淳,看似是导演的选择,实则是资本网络里的自然流动。就像网友调侃的:“别人挤破头想进圈子,雷佳音直接成了圈子的一部分。”
这种“安全牌”逻辑,在影视行业遇冷的当下愈发明显。某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影视投资同比下降18%,但雷佳音主演的作品融资成功率却高达92%。资本宁愿花高价请他演重复的角色,也不愿给新人一个机会。“就像奶茶店永远在卖珍珠奶茶,不是因为它最好喝,而是因为它最不容易出错。”一位编剧的比喻,道尽了行业的无奈。

张译宣布息影的那天,微博热搜上“张译vs雷佳音”的词条挂了整整一天。不是两人有什么恩怨,而是观众突然意识到:同样是演正面角色,张译能在《狂飙》的安欣和《三大队》的程兵里找出细微差别,而雷佳音的“窝囊”却像复制粘贴。更重要的是,张译敢喊停——“再演下去,我怕观众吐了”,这份清醒,在当下的娱乐圈显得格外珍贵。
对比之下,雷佳音的“我觉得演好一类角色也不错”就显得格外刺眼。这背后,是整个行业对“原创”的漠视。某编剧协会的调查显示,2024年新备案的剧本里,63%存在明显的“跟风”痕迹——《长安的荔枝》火了,立刻冒出一堆“古代打工人”题材;《人世间》爆了,“窝囊男主”成了香饽饽。就像古偶剧泛滥时的“三生三世”套路,资本永远在复制成功,却忘了观众的味蕾早就麻木了。
年轻创作者的困境,更让这种“复制粘贴”雪上加霜。邵艺辉在写出《爱情神话》前,曾靠卖电子烟维持生计,她的剧本被三十多家公司拒之门外,理由都是“题材太新,没人敢赌”。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某平台数据显示,90后编剧的作品通过率不足15%,很多人被迫转行写短剧,因为“至少能按时拿到稿费”。当有灵气的原创被挡在门外,市场上剩下的,自然是雷佳音们演绎的“安全牌”角色。

更让人忧心的是,这种“安全”正在吞噬多样性。中年女演员还在为“35岁后只能演妈”发愁时,同龄男演员却能在“窝囊”“硬汉”“精英”几个标签里反复横跳,甚至像雷佳音这样,靠一个标签就能横扫市场。某影评人犀利指出:“当我们吐槽雷佳音时,其实是在抗议这种不公平——为什么男演员可以舒适地重复,女演员却连重复的资格都没有?”
观众的愤怒,本质上是对“被敷衍”的反抗。我们不想在电影院里看到熟悉的皱眉,不想在电视剧里听到雷同的叹息,更不想让屏幕上的世界,比现实生活还要单调。就像那位在《酱园弄》影评里写道的:“我花几十块钱买票,是想看看不一样的人生,不是来复习雷佳音的演技课。”
雷佳音的霸屏,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行业的病灶:资本的短视,创作的懒惰,以及对观众审美趣味的轻视。但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漫长的季节》里秦昊的颠覆性表演,《繁花》里胡歌的突破,都证明只要有诚意,观众愿意给演员机会。

或许,我们不需要雷佳音立刻转型,只需要行业能慢下来——给新人一点空间,给原创一点耐心,给观众一点惊喜。毕竟,没有人天生喜欢重复,我们只是暂时没找到更好的选择。当屏幕上重新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角色,当年轻演员敢挑战舒适区,当资本愿意为“陌生感”买单时,雷佳音的“霸屏”争议,自然会烟消云散。
而对于我们观众来说,能做的或许就是——当又一部“似曾相识”的剧出现时,勇敢地按下快进键。毕竟,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值得更精彩的故事。
(娱乐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