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天津日报
重磅品荐
文物里的烟火人间(图)
王小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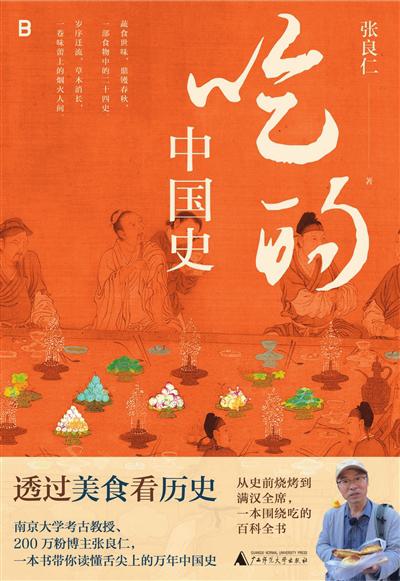 |
| 《吃的中国史》,张良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 |
历史的风烟总在王朝的更迭中消散,但灶台上升起的炊烟却从未断绝。当我们翻开《吃的中国史》,那些被青铜器铭文、陶片、残片、墓葬遣策封存的饮食记忆,便在考古学家的笔下化作鲜活的生活图景。从青海喇家遗址那碗四千年前的小米面条,到清宫御膳房档案里的满汉全席,作者张良仁以考古为匙,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饮食文明的时空之门,让我们在酸甜苦辣的滋味里,看见文明演进的密码。
■ 当文物开始“说话”
2002年,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的考古发现曾震惊学界:“一个橘红色的陶碗里藏着面条状遗物,色泽新鲜如昨,经检测竟是小米粉制成”。四千年前的黄河岸边,先民们面对黏性不足的小米粉,究竟如何将其塑成面条?这个未解之谜让考古现场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作者想象着喇家先民在黄土台地上,“用石磨盘研磨粟米,在陶罐中揉制面团,或许借助草木灰水增加黏性,在蒸腾的热气中完成这场面食的最早尝试”。这碗面条不仅是食物的遗存,更是文明的切片——它见证了西北旱作农业区的先民如何利用有限的粟黍资源,创造出改变饮食结构的面食雏形。
当考古队员打开一号汉墓的云纹漆鼎时,“完整的藕片清晰可见,呈乳白色,孔眼清晰,和今天的藕片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后续的多次搬动中,藕片不断地减少,等到用卡车运到博物馆后,藕片已经全部消失——它们在两千年的浸泡中氧化,一见阳光便炭化瓦解”。更令人称奇的是陶罐中的杨梅“罐头”,“颜色紫红,果肉丰满,带着青绿色的果柄,仿佛刚刚采摘下来”,让人遥想西汉贵族在夏日宴饮时,如何用冰镇杨梅消解暑气。
这些沉睡于地下的文物,在作者笔下化作了有温度的生活场景:厨师在案板前切配食材,侍者用漆盘端送珍馐,宴会上酒酣耳热之际的笑谈,都随着文物的细节复活。
■ 考古现场的味觉重构
厨房从来都是文明的实验室。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交织,让饮食史摆脱了空洞的想象。当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发明陶器,蒸煮法便成为改变饮食史的伟大创造。河姆渡遗址的陶釜底部,“焦黑的锅巴颗粒完整,肉眼可见,那是7000年前最早的米饭残留”;良渚古城的稻田里,“整齐的沟渠和灌溉系统长达数公里,先民们用‘草裹泥’技术堆筑堤坝,将沼泽改造成万亩良田,使水稻产量较河姆渡时期提升2.2倍”。到了宋代,铁锅的普及带来了烹饪革命,“北宋用煤炼铁,生铁年产量从西汉的5000吨跃升至15万吨,铁锅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种传热极佳的炊具让‘炒’成为主流技法,‘锅气’赋予菜肴独特风味,至今仍是中餐的灵魂”。
食材的驯化与传播,更是一部文明的奋斗史。北方的粟黍、南方的水稻,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奠定了中国农业的基础。当小麦穿越中亚草原来到黄河流域,“董仲舒建议武帝推广种麦,氾胜之在关中培育出耐旱的‘宿麦’,到了唐代,‘小麦入税’标志其成为北方主食,《烧尾宴食单》里三十九道面食,尽显麦作的辉煌”。美洲的番薯、玉米在明末传入,“福建人陈振龙将番薯藤缠在缆绳上偷运回国,乾隆年间推广至西北,这种‘不挑地、易生长’的作物,在灾年救活了无数百姓”。
每一次物种的交流都伴随着技术的革新:河姆渡人用骨耜翻耕水田,磁山先民在粮窖里储存5万公斤粟米,明代福建人将番薯藤缠在缆绳上带回中土,这些智慧都沉淀在民族的生存基因里。
饮食礼仪的演变则是文明进步的镜像。两周时期的列鼎列簋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鼎中牲肉、簋中谷物,成为贵族等级的象征,虢国国君墓出土的七鼎六簋,正合‘诸侯之礼’”;宋代市井饮食的繁荣,打破了门阀饮食的壁垒,“汴京夜市的‘州桥小吃’通宵达旦,‘白汤饼’‘炸油饼’香气弥漫,勾栏瓦舍里的平民百姓,用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食,吃出了市民社会的蓬勃生机”。到了清代,满汉全席的诞生更是民族融合的味觉结晶,“满席的烧鹿肉与汉席的清蒸鱼同列,蒙古诸王与汉族大臣共饮马奶酒,饮食超越了果腹的范畴,成为‘满汉一家’的文化象征”。
■ 历史里的饮食记忆
饮食史从来不是只写珍馐美馔,更记录着生存的艰辛。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河南境内赤地千里,《申报》记载灾民‘煮人肉以食’,考古发现的荒芜村落遗址,印证了这场一千万人饿死的惨剧,让我们深知粮食安全始终是文明的底线”。1942年的河南饥荒,“旱灾与蝗灾肆虐,百姓啃树皮、食泥土,300万人命丧饥荒,这段历史与今日河南粮仓的丰盈形成残酷对照,提醒着我们‘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但在苦难之外,饮食也是慰藉心灵的良药。苏轼在黄州发明“东坡肉”,用廉价的猪肉烹出人间至味,在贬谪生涯中以美食对抗命运的颠簸;陆游在山阴农村写下“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描绘出民间宴客的温情画面,“农舍里杀猪宰鸡,热酒烫壶,木桌上摆着新麦做的炊饼,邻里笑谈声穿透纸窗,构成了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这些文人与美食的邂逅,让饮食超越了物质层面,成为文化精神的寄托。李白在胡姬酒肆痛饮葡萄酒,“西域传来的葡萄在长安酿成美酒,酒杯碰撞间,是丝路驼铃与长安月光的交织”;乾隆下江南偏爱江南竹笋,“《乾隆三十年江南节次膳底档》记录他一日两餐必食竹笋,帝王的口味里藏着江南的水土灵秀”。
朝代的兴衰往往在餐桌上留下印记。唐代长安的胡饼店飘出麦香,“‘时行胡饼,俗家皆然’,白居易学做‘辅兴坊胡麻饼’,面脆油香,寄给友人时还附诗一首,尽显盛唐的开放包容”;宋代汴京的正店酒肆夜夜笙歌,“七十二家正店高悬‘彩楼欢门’,官酒户岁用糯米三十万石,夜市里‘白矾楼’的酒博士穿梭如飞,倒映着商品经济的昌盛”;清代扬州的满汉全席奢华至极,“一百零八道菜肴涵盖山珍海味,熊掌驼峰与燕窝鱼翅同席,既展现康乾盛世的底气,也暗藏着帝国最后的狂欢——当乾隆在千叟宴上赐宴三千老人,火锅蒸腾的热气里,是王朝对‘太平盛世’的终极想象”。
■ 在碗碟间看见中国
《吃的中国史》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史书的宏大叙事,将镜头对准了灶台、餐桌、市集这些“小”场景。当我们看到喇家先民为制作小米面条而摸索面团塑形,“小米粉黏性不足,他们或许尝试过添加野菜汁或动物油脂,在无数次失败中寻找最佳配比,最终成就了‘中华第一面’”;看到宋代厨师在铁锅前挥舞炒勺,“猛火快炒间,青菜的脆嫩、肉片的鲜香瞬间激发,这种‘镬气’烹饪法,让寻常食材化作舌尖上的盛宴”;看到清代御膳房为皇帝寿宴准备千道菜肴,“御厨们凌晨便开始熬制高汤,燕窝要泡发三日,鱼翅需文火慢煨,每道菜的摆盘都暗合阴阳五行,饮食在此成为礼仪与权力的具象”,会突然意识到:所谓文明,正是无数普通人在烟火日常中创造的奇迹。
这本书仿佛一场跨时空的对话。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寻找食物残留,“贾湖遗址的陶罐里,9000年前的葡萄酒残留物带着野葡萄的酸涩,那是先民最早的酿酒尝试”;历史学家在文献里爬梳饮食记载,“《齐民要术》中的‘蒸饼法’与敦煌文书里的‘胡饼价目’,拼贴出北朝饮食的多元面貌”;而作者则像一位高明的厨师,将这些素材烩成一锅滋味绵长的文明之汤。当我们在书中读到“辣椒用短短百年征服中国人的餐桌,在四川与花椒相遇,成就了‘麻辣’传奇;在贵州与缺盐的山地结合,化作解腻的‘糊辣’蘸水”,读到“豆腐汤、炒豆芽等市井之食登上宫廷菜单,乾隆南巡时竟对‘炒豆芽’赞不绝口,让御膳房添入常膳”,会忽然明白:饮食的变迁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与农业技术、政治格局、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合卷之际,眼前浮现的是书中那些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河姆渡人在干栏式房屋里蒸煮米饭,“陶釜中冒出的热气模糊了木窗,孩子们追逐着飘落的稻花,老人用骨镰收割成熟的稻穗”;长安市民在西市购买胡饼,“饼炉前围满百姓,炉匠将撒满芝麻的饼坯贴入炉壁,金黄的胡饼一出炉,便被抢购一空”;广州商人在十三行码头装卸蔗糖,“褐色的糖块堆成小山,水手们哼着民谣,将中国蔗糖运往东南亚,换取香料与珠宝”。这些场景连缀成一条文明的长河,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条河的继承者。
《吃的中国史》让我们懂得,所谓历史,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英雄史诗,而是藏在一粥一饭里的生存密码,是刻在味蕾上的文明记忆。在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这本书如同一场温暖的提醒:面对食物时,不妨慢下来,想一想食材从何处来,历经了怎样的迁徙与演变,承载着多少代人的摸索与创造。因为每一种味道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每一次咀嚼的瞬间,都是与历史的一次温柔触碰。这或许就是饮食史的魅力:它让我们在烟火气息中,触摸到文明最真实的温度。
(美食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