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2025年的全国高考和中考相继结束,又一批中国孩子迎来了人生的分岔路口。从小学读到大学,在“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的文化教育中逐渐成人,走向社会,用人类学家任柯安(Andrew Kipnis)的话来说,这是中国社会普遍的一种“教育欲望”。普通初高中、大学生的生活,也更加受到公众的关切。近年来,不论是“小镇做题家”,还是“困在绩点里”,故事的主角,都是这样一批相对“主流”的学生。
2010年,当时刚刚完成硕士学业、在香港研究学习的董轩第一次来到“少林寺之乡”河南登封。在这里,他看到了“教育欲望”的另一种版本:进山沿途,一家紧挨着一家的武术学校中,挤满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子。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武校是一种职业学校,但和很多职校不同的是,武术学校似乎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职业指向,“有些学校会在招生简介上写上可以考虑当兵、高考单招等,但总体上来说,其实学生和家长们对出路是比较模糊的”。
这些学生从哪里来?为什么会选择一条相对“偏离主流”的路?他们正在经历怎样的成长状态?在短暂的登封之行后,这些问题一下子击中了董轩。
采写|刘亚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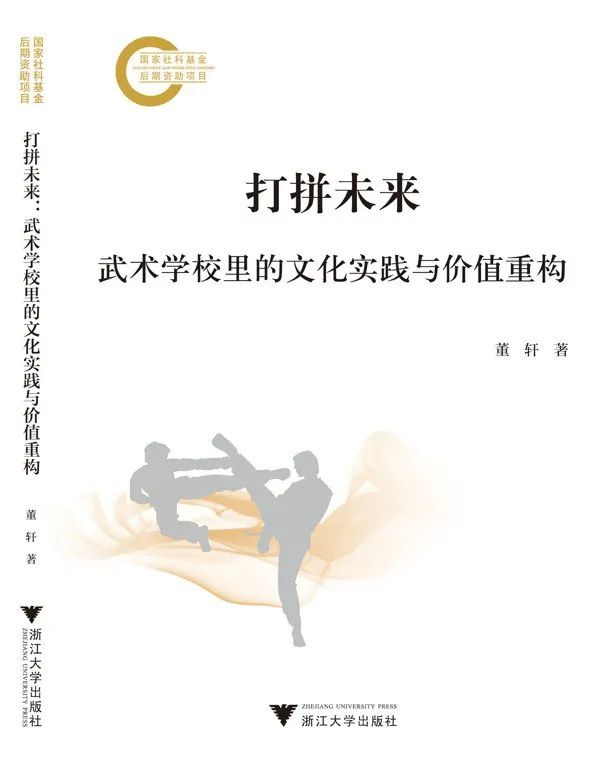
《打拼未来:武术学校里的文化实践与价值重构》
作者:董轩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2011年,任柯安的《治理教育欲望》(暂译,Governing Educational Desire)出版,董轩随即给任柯安发去邮件,表示希望研究中国的武术。随后,他顺利地来到澳大利亚,在任柯安的指导下开启博士生涯。
2020年,自称“浑元形意太极门掌门人”的马保国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成为“顶流”:他与搏击教练王庆民约战擂台,30秒内被击倒3次,随后在直播中以狼狈的状态,说出了“不讲武德”,“耗子尾汁(好自为之)”等网络热梗。在网友后续的调侃与狂欢中,对曾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传统武术,大众的质疑一时达到顶点。
董轩认为,其实公众对武术学校的认知一直存在刻板印象和误解,或是过分浪漫化武术教学,或是过于嘲笑或贬低,学术界更是鲜有人会将其当作严肃的研究对象。即便在他开展田野调查的十几年前,情况也是如此。在“重文轻体”的主流教育理念之外,武校的环境确实有其特殊性。“好学生”和“坏学生”的评价,在这里变得微妙。在普通学校里被认知为绝对“差生”行为的打架,在这里却可能是一个学生“优秀”的副产品:他可能在武学训练课堂上表现极为优异。武校对身体训练的强调,也让“开棍”这种在外人视为体罚的做法,在这里成为一种特殊的严厉惩罚。

《少林寺》(1982)剧照。
不过,在武校的特别之外,董轩从朝夕相处的学生们身上,看到了更多的“普遍性”:许多因为父母务工留守的孩子,因为被认为“难以管教”,被家里无奈送到这里,他们讨厌武力,却对文学、艺术情有独钟;大多数学生平日里沉默寡言,承受枯燥繁重的身体规训,却在周末放风的网吧、KTV中互诉衷肠,痛哭流涕;被送来武校的女生只为了给弟弟“陪读”,或是为了圆父亲一个“功夫梦”……
2024年,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学者徐平利出版了《寻找裴斯泰洛齐》(书评周刊曾推出专题《重寻职业教育》对话徐平利,《因为偏见与傲慢,人们认为“职校”输送的就是产品》)。在书中,他在历史中打捞起被忽视已久的现代“职业教育之父”裴斯泰洛齐。在职业教育的肇始,裴斯泰洛齐提倡的是一种与生命高度联结的、审美的职业教育观念。工业革命后,随着人类社会对经济效率比拼的重视,这种观念日渐消退。职校生遭遇的冷落,几乎同步发生。
今年1月,经过漫长的修改,董轩有关登封武校的研究以《打拼未来:武术学校里的文化实践与价值重构》的书名出版。这本书封面朴素,用董轩开玩笑的话说,“很惊讶会有人发掘到它”。对于书中研究的武校生群体,时至今日,他们也同样很少被“看见”。近日,我们和董轩聊了聊他的研究。董轩说,高中时,他是不折不扣的差生,这段经历驱动了他的很多研究。他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学校里的差生群体。“他们都不是现在舆论热点里‘困在绩点里’的985大学生,但需要我们更多的重视”。

董轩,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获吉林大学新闻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人类学,出版有《重构常识:教育民族志的方法与文本》(2021)《打拼未来:武术学校里的文化实践与价值重构》(2025)等。
“来武校,把身体练好就行”
新京报:在中国普遍“重文轻武”的背景下,武校常常是作为家庭“没有选择的选择”,很多家里人觉得管不好孩子,就把孩子放到武校寄存。武校的学生来源,从你研究以来,这些年有变化吗?公众对武校的认知,和你的研究发现有哪些偏差?
董轩:我当年的观察是,很多家长没有在练武的出路上对孩子抱有太多期待,而是会把孩子视作“寄存”在这里,锻炼几年,往后再去做别的事,走别的路。我当年访谈过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期待往往不是像标准城市中产家庭那样,有很明确或者特别高的要求,更多就是“不犯法”“把身体锻炼好”,因为“做什么都要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我访谈的时候听到最多的话。

《武术之少年行》(2008)剧照。
当然还有一些家长有别的期待,比如寻根式的,有东南亚的华裔家长,特地把孩子带到登封来,让他们体验“最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他们来说,学武也是次要的,重要的还是传统文化的根。
这几年,我们的教育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我做田野的时候,常规的学校好像还没有特别明显地重视体育,但这几年,从国家的教育政策到各校自己制定的制度,很多都对学生体育运动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希望达到“以体树人”,通过身体的锻炼,能让学生在观念、精神、道德上有一个提升。这和我当时在登封武校里看到的对学生身体的重视,有一些相似之处。也许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慢慢注意到了过去那种重视考试——“文”的学习——需要有一个重新的看待。不仅是对待狭义的竞技体育和体能训练,还有对我们身心健康、以体树人的重新理解,现在也需要被足够重视。
新京报:在武校,“道德”或者说“素质”是一个很关键的话语,它不仅被学生用于定位自身,也是学校“改造新人”的重要目标。前两年因为马保国遭遇的争议,“不讲武德”成了一个网络热梗。现在的武校师生怎么看待“武德”?
董轩:就我的观察来看,一些规模比较小的武术学校,师徒关系更传统一些,或者可以说小武校更希望复刻传统的师徒模式。一般在这样的学校里,无论是师父还是武校老板,多少都和少林寺的脉络有些渊源。他们特别强调师徒传承,对他们来说,“武德”的修行是放在师徒关系的框架下来考虑的,比如弟子可能需要给师父做一些家务,干一些杂活。他们都住在师父家附近,像传统的入室弟子或“家徒”一样。在手把手“教”与“学”的模式中,“武德”的内涵浸润在日常训练、劳作的各个环节。
还有一种情况是规模较大的武术学校,一般致力于建立更严格系统的现代管理制度。在这样的学校,教练更像一个班主任,区别仅仅在于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状态下,他要跟着几十个学生同吃同住,一起生活,出学校一样困难。这种语境下再提“武德”,往往带着现代学校管理的目的,比如不能随意打架,这是违背“武德”的,更重要的是违背校规的,和学生职业发展的评价也是挂钩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当教练跟学生讲,以及教练在理解“武德”的时候,他往往带着一种现代学校管理方式和目的。例如,他在谈论什么是有道德的时候,会说你不能打架。这不仅仅是在谈论“打架”是作为一个违反道德的事情本身,还有一个暗含的逻辑:“打架”,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是跟个人的职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当然还有一群人,是用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武德”的,比如去质疑有关对弟子的惩罚,哪些在今天看来合理,哪些不合理。所以在武校内部,“武德”的话语还是很复杂的。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新京报:武校训练的内容中,扎马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符号——它留给人的印象几乎是纯粹的“吃苦”。但“吃苦”本身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包括很多家长会被各种武校开设的“矫治营”吸引也是这个原因。学生怎么看待这种“吃苦”文化?你在书中还提到,武校的环境让体罚这种被常规学校视之为违规的做法合理化,“吃苦就是要挨打”,这种观念在中国有怎样的渊源?
董轩:从少林武术本身的修炼的角度来讲,扎马步、千层纸这些训练本身首先是一种身体技术。比如打千层纸,是很有讲究的,把很多层纸钉在一起用于练习出拳,纸的厚薄是相间的,很考验学生出拳的力道,是对身体技术的控制。其次,在身体训练的过程中,“吃苦”实际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叙事中被赋予了道德意义,这和中国文化强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内核逻辑是相通的。
我认为在中国社会里,在培养某种技术的职业学校,技术本身都会被赋予一些道德色彩。比如外界经常认为武术学校的人很容易找到工作,因为他们经过了某种“道德品质上的淬炼”。比如学过围棋的人,会被认为更有耐心。勤不勤奋、能不能吃苦,这些道德层面的评价现在也用作价值排序,以此区分好学生、差学生。
在武术学校里面,有时候情况会更复杂一些。武艺是否高强是一种评价标准。与此同时,教练们会把大多数学校的这套价值体系——学生听话或者不听话,能吃苦或者不能吃苦,勤奋或者不勤奋——引入进来区分学生。这是另外一套话语。不同评价话语,在武校是交织在一起的。练武的特别之处在于,“吃苦”是能被肉眼观察到的,你流出来的汗、痛苦的表情,都是“吃苦”的具象化。如果是学文化课,要怎么表现一个人学数学的“苦”?似乎没有身体训练直观。

《武术班》(2009)剧照。
新京报:通过你的研究,我感觉武校这个空间存在一些悖论,比如,它本身高度封闭,学生和社会的联系可以说被切断了。这其实导致武校里的教育方法形成了一些“特例”。送孩子去武校的家长,很多其实也怀着一种矛盾的期望,希望孩子受锻炼,又怕他们被虐待。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有关武校体罚学生的争议频发,作为研究者,你会怎么看待武校的很多教育方法?
董轩:武术学校确实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怎么能够让一个擅长打架的学生,只在有规则的擂台情境下使用武力?我能观察到的就是使用“武德”这个话语,认定武校里的优等生除了是武艺高强的,更是懂得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的。他们会跟学生说,一个真正职业的武者不是懂得怎么“用劲”,而是懂得“收劲”,也就是点到为止的艺术。但现实情况还是有复杂性。我曾经看过判决文书网上关于武术学校的民事赔偿的判例,这个数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很多都涉及受伤事故。
在我十几年前做田野的时候,从学校的管理层的角度,他们已经明确要求教练们不能体罚。但是对一线教练来说,体罚确实是最简单的一种管理方式,所以这中间是有张力的。不同教练体罚的“水平”也不同。比较资深的教练,相对会更好地掌握分寸。
我在书里也提到,体罚在武校叫“开棍”。有经验的教练“开棍”不会把学生打坏,但也能把惩罚的效果达到。需要用这种惩罚处理的,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打群架。
这些年因为有了新媒体,各地的武校经常会有一些关于体罚的争议爆出来。我有一个个人的观察,如果是在最传统的师徒关系里,师父惩罚弟子往往很讲分寸,因为主要是为了点拨、教化。但在一些舆情事件里,我们经常看到的不是“师父-弟子”关系里发生的惩罚,而可能仅仅是体罚者的情绪发泄,怒火指向学生的身体。这和武校的组织形态的转型是有关系的。比如我调研的时间点,一些武校为了吸引潜在生源,会把自己包装成“戒网瘾学校”等等,向家长们宣传的是能进行孩子行为的“矫正”。这时候,曾经的师父就变成了“管理者”一样的存在。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和武校生们一起唱KTV的经历,在这里你看到了他们更丰富的另一面,他们表达了与学校里完全不同的、更强烈而真挚的情感。这是不是反过来说明,武校在情感教育上有很明显的缺位?这种缺位是一种不只存在于武校里的普遍现象吗?
董轩:当年我碰到的武校学生们有一个共性,话都非常少。这首先给我带来的一个麻烦就是访谈的难度陡增,基本上很难做一个像我们这样一两个小时的长对话。但如果跟他们相处久了,你会了解到他们并不是来武术学校才变成这个样子的。他们中很多人是留守儿童,被隔代抚养,或者是父母即便和他们住在一起,平时也不是非常关心他们,慢慢他们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书里提到,他们特别喜欢去上网,有时候甚至不惜冒着被全校通报批评、挨体罚的风险也要翻墙去上网。上网并不单纯只是玩游戏,而是能在虚拟空间里寻找到一些亲密关系的联结。所以,武校里孩子的集体沉默,其实起源于校外。
当然,从武校本身来讲,在我和他们的师生打交道的那些年里,我几乎没有看到他们提到孩子们的“感受”,好像情感在这里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很多教练会说,他们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换句话说,在这些教练看来,武者在习武过程中可能本就需要压抑自己的情感,比如,受伤了不能哭,哭会被认为是软弱、脆弱的表现。在普通学校里,一个班主任批评了一个同学,会考虑是否刺激了他,伤了他自尊,在这方面更敏感了。但在我调研时期的武校里,这种考量是不大会出现的。
这是不是对武校孩子的一种情感压抑呢?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不好下武断的结论。我想可能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觉得这是一种压抑,对于不想练武的人来说,也许确实是一种压抑。武校里确实也有很多不快乐的孩子,比如我在武校里的一个室友,他就是一个不情愿被送来武校的孩子,练武不是他的兴趣,他对文艺更感兴趣。他跟我说他坚持不摘眼镜,因为戴眼镜的人是“有文化的”,和那些“武夫”不同,他就是过得很不开心。
职业教育提供的环境可能比较单一,但学生们是很复杂的。情感上的压力,会导致这些少年需要寻找各种突破口。家境好的大手大脚地花钱,不断换手机。
我没有研究过别的职业学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同类学校存在的共性问题。对于武校来说,可能学校的高层也会想,这些孩子本身是带着一些“问题”来到学校的,所以武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改造”问题学生,让他们能“重回社会”。在这种视野下,那些学生在这里感受到的“痛苦”,可能正是“改造过程”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受苦”便是一个指向重回主流社会的重构过程。
武校里的女孩子们
新京报:不论是在公众印象还是学术研究中,武校似乎都是充满尚武的“男性气质”的。在这种环境下,去学武的女生群体的处境变得微妙。你的研究发现,武校的女生一方面希望自己适应学校男性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些抵抗,比如不认为自己是“女汉子”。她们是如何安放自己的这种身份认同的张力的?
董轩:在校时间的长短,以及年龄,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武校里的女生的状态。我当时看到的很多太小的女生,并没有很强的性别意识,受到这种困扰少一些。但是青春期的女生,很多都会有这种困扰。因为武校的评价体系里,练得好、打得好很重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存在甚至“追捧”这样的榜样,女孩子也会想效仿,至少能得到老师们的赞赏,她们会去尝试着让自己显得更像武校里的男生。但是有一些细节还是能透露出张力,例如,每到周日的时候,下午放假,我经常会看到很多女生穿着用现在的话来说特别“萌”的拖鞋或者睡衣出现在操场上,和平时整个人的状态非常不一样。
我书里也提到了一些研究,比如,Ezzell研究了美国高中女橄榄球队队员,发现她们通过构建“独特的身份”,例如强调自己是异性恋、有“传统”的女性吸引力等来区分“女生”与需要“男性气质”的橄榄球运动员这两个身份。受到尚武文化的影响,武术学校的女生必须发展出一套表演坚韧的策略,以在这种男多女少、崇尚狼性的文化的环境里保护自己。但她们也无意识地重构了所谓“女性气质”,比如我访谈过的小薇,本身练武练得很好,男生给她起“男人婆”的外号,她对此表示拒绝,在她眼里,这是练武的女生特有的“独立”。

纪录片《龙之女》(2013)画面。
之前有一个纪录片叫《龙之女》,就专门拍摄了少林武术学校的女生群体,这里面就呈现出了复杂性。此外,之前一个记者拍过一张照片,也给过我很大的震撼,同时,我也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隐喻。那是一个武校里拿了全国冠军的女生,接受采访的时候,手里抱着一只特别大的泰迪熊,在她身后的墙上,是一个李小龙露着腹肌的照片。

李小龙经典电影《猛龙过江》(1972)剧照。
不过,因为我是一个男性研究者,诚恳地来说,我不一定能完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真相,我只能讲我观察到的事情,很多事情我并不能直接去猜测。不过,有一点非常确切的感受,这些武校里的女生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经历着无奈。比如我书里提到的小芳,家里把弟弟送来武校学武,担心他学坏、受欺负,就把小芳也送过来“陪读”。还有“女承父业”的小龙,爸爸是一个武术迷,把她送来学武是为了圆自己的武术梦,但她并不喜欢学武。尽管这些女生都是十几岁的未成年人,但似乎都在“照护”别人的梦想。这可能是武校里的学生能折射出的更大的社会问题。
“在武校里等待成年”
新京报:武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出路常常和“做功夫明星”相连。但学生想象中武校出路越是浪漫化,在残酷现实面前经受的落差就越大。这种“功夫梦”在武校学生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今它还有感召力吗?
董轩:在我做田野研究的那个时间点上,如果问武校的教练,他一般会说,他当年学武(更早一些时候),就是想要“成为李连杰、成龙”。但到了他们当教练的时候——尤其是电脑技术已经很发达——本身武术片的拍摄语境就在变,影视剧里对武术的身体要求在变低。那时候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卧虎藏龙》,那是一个功夫片转型很成功的案例,他们意识到,原来不那么会打,也是可能出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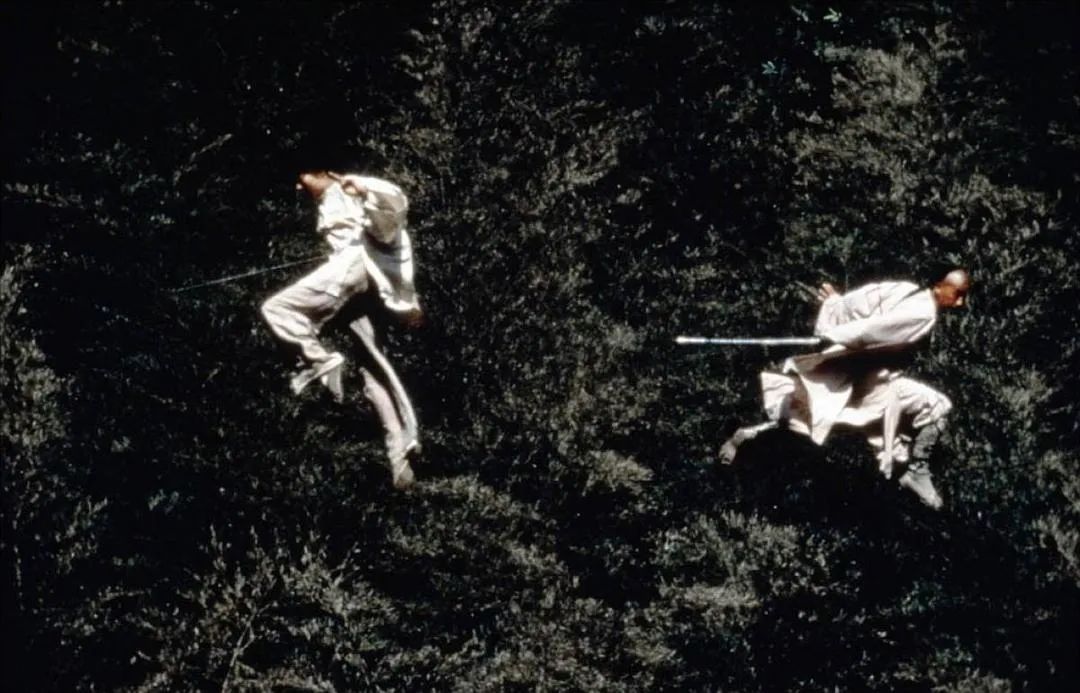
《卧虎藏龙》(2000)剧照。
所以那时候,武校里的孩子们即便真的是想学武,也对“打成名”不太乐观,但他们会有自己对于梦想的“重构”。我当时就碰到一些孩子跟我说,他们希望在登封这儿接受武术训练之后,再去山东学跑酷。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完全不知道跑酷是什么,但他们已经很兴奋地在跟我谈论了,向我科普跑酷运动有哪些“大神”、需要怎样的身体技术等等。
有些孩子的成熟让我惊讶,学武其实只是一个铺垫。比如有个孩子跟我说他未来想开一个拳馆,这放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也是一个那个年纪的小孩很罕见的梦想。但是他说得很认真,他说他爸爸跟他一起分析,觉得要对这个行业先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所以还是应该先来学一下武。
他们会很细致地分析他未来有什么规划,准备怎么落实。在田野里和他们朝夕相处,其实从我个人情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外人刻板印象里的那种“功夫梦”。但梦想依然是重要的,比如跑酷,梦想或者希望是生活的支撑,是用一种对未来的想象、规划来编织当下、个体感受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其实都是一样的。

纪录片《中华武术》(1984)画面。
新京报:你全书的结尾叫“在武校里等待成年”。我觉得“等待”在此的内涵特别丰富,可否展开谈谈?
董轩:学者Woronov(暂译,沃伦诺夫)之前研究了南京两所职业学校的学生,他用“消磨时间”(doing time)来描述职校学生的在校状态,认为这种貌似没有“生产性”的“消磨时间”实际上是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劳动形态。对职校的学生来说,职业教育的学历可能并不代表知识或者技能的提升,但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学生的韧劲。所以,尽管职校学生每天在课堂上睡觉、打发时间,做一些看起来浪费时间的事儿,没有“学习知识”,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付出“劳动”,没有收获。职校的“无聊”反倒磨炼了这些学生抵抗生活不确定性的耐心,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面对毕业后服务业的高度流动性。
这个研究的启发是,西方现代性对时间的理解,让我们追求人生的每一秒都要有效率,都要创造价值,一旦我们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就是不对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但问题是,何谓价值,何谓浪费?在南京职校的这个研究里,学生们做的事情被界定为消磨时间。在武校,其实很多人也觉得学生们学的东西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这些真的是浪费时间吗?从人生的角度来说,悖论也许是,有时候这种“等待”的状态也是必要的,而有很多时间利用率拉满的努力,却往往是“消磨时间”,消耗掉的不仅仅是时间、对世界的好奇心,还可能同时磨掉了优雅的失败和“漫不经心”生活的能力。
我不能简单判断武校学生的状态是不是同样是一种“消磨时间”。说它是人类学意义上的“阈限”状态可能更恰当——它是一个人生的“中间态”,连接着人生的两个阶段。学生们在武校,可能并没有指向一个明确的未来,但这段人生,对于他们来说,也各有意义。
新京报:在前人研究几乎空白的情况下,研究武校学生这样一个“非主流”的学生群体,给你的学术与思考带来了哪些影响?
董轩:这个十几年前做的研究带给我的影响可能是多个维度的。首先是我会不断反思师生关系,我现在也是研究生导师,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在中国语境里常在“师门”这个概念之下被讨论,既有“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意思,也可能还有“内”“外”的符号边界感。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武校看到的所谓好的或者不好的师生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演化发展,都会不断提醒我怎么去做一个我认为合格的导师。
第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会参与一些学校教育实践的讨论。我经常会在讨论的时候提醒:一个政策或制度在一线实践中会有怎样的非预期效果?当年我研究的武校学生群体,其实也映射着这样的非预期效果。例如,一个学生可能因为大的环境的变动,在老家和父母的打工地之间来来回回折腾,最后偏离了大多数同龄人的人生轨迹,走上了一条比较“非主流”的路。
第三,我自己现在主要做基础教育研究,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各种学校听课、参与学校改进的研讨。我可能会更多关注那些学校生活中“被忽略的学生”,比如,老师设计教学的时候,要把可能反应慢一点、跟不上的学生考虑进来。做公开课展示教案的时候,要把比较内向的孩子考虑进来。我现在指导学生的选题,其实也有这个趋向,他们做过口才学校学生、艺考生、高考复读生等群体的研究,他们都不是现在舆论热点里“困在绩点里”的985大学生,但需要我们更多的重视。
采写/刘亚光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
(教育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