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峥,香港大学教授,沪港创研院首席科学家。曾任亚马逊云科技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创始院长、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小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局点》《租界》、中篇小说《特工许向璧》《封锁》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现居上海。
按:What We Can Know(《我们能知道些什么》)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今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们邀请了香港大学计算机张峥教授来一起聊聊,关于这部小说,关于麦克尤恩,以及由这部小说引出的一些想法。
这部小说的叙述者身处2120年。世界已历经气候灾难性变暖引发的社会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洪水”。英国已被淹没,只剩一些零星岛屿。此时全球人口锐减,物质极度匮乏,虽然生态已开始缓慢复苏。在这个时代,人类开始选择过一种依靠合成蛋白维生的、平静而略带忧郁的田园生活。
汤姆·梅特卡夫(Tom Metcalfe)是大学教师,也是一个时代的“异类”,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痴迷于一百年前,也就是21世纪初那个物质过剩、行动自由的“黄金时代”。他毕生的学术追求是寻找文学史上一块缺失的拼图:著名诗人弗朗西斯·布兰第(Francis Blundy)在2014年为其妻子薇薇安(Vivien)五十岁生日创作并朗诵的一组十四行诗——《致薇薇安的冠冕》(A Corona for Vivien)。
汤姆与他的伴侣兼同事罗丝·丘奇(Rose Church)一起生活。罗丝虽然同样研究21世纪,但她更关注时代病理——试图理解为何21世纪初的人类在明知灾难临头时,仍陷入集体认知失调。
随着汤姆深入挖掘幸存的数字档案——那些存储在尼日利亚服务器中的碎片化邮件、日记和录音——小说的时间线回溯至2014年及其前后,逐渐揭开了布兰第夫妇生活的真实面貌。读者看到的并不是传说中的神仙眷侣,而是一段充满权力不对等的残酷关系。弗朗西斯才华横溢却极度自负,是一个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才”;而薇薇安,这位原本有着敏锐才智和学术抱负的女性,在漫长的岁月中被迫成为了丈夫的保姆、秘书和情绪垃圾桶。汤姆的调查层层剥茧,不仅重构了那场生日晚宴的细节,更触及了深埋在数据堆栈/历史层积下的丑闻、创伤和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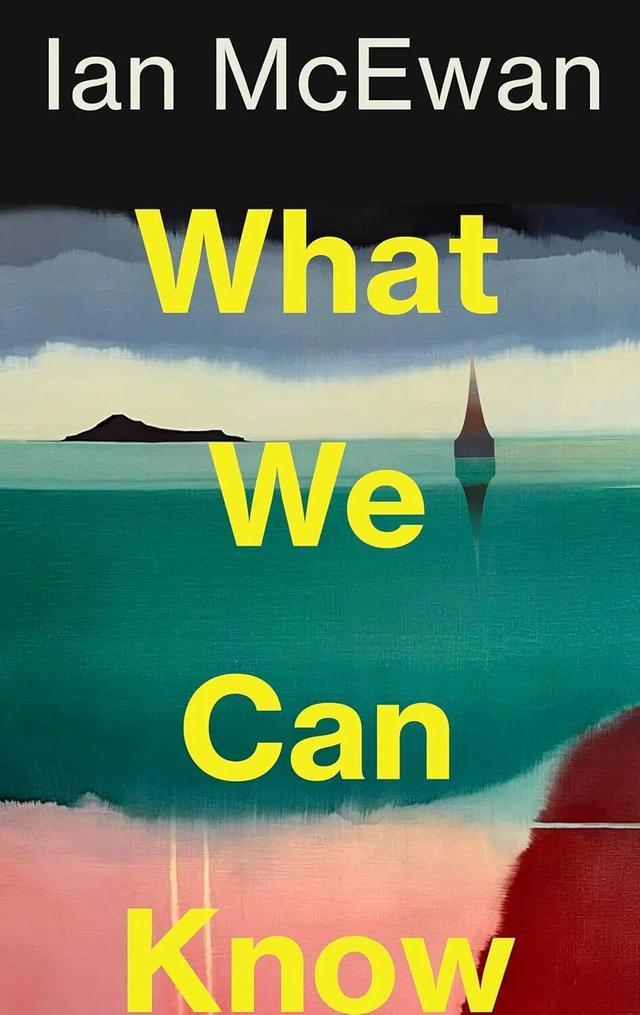
失忆与“形而上学的忧郁”
小白:从1975年出版第一部短篇故事集,到今年这部长篇What We Can Know,伊恩·麦克尤恩整整写了五十年。这件事情十分令人鼓舞,不论这小说本身有多悲观,也不论它似乎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形而上学的忧郁”气氛,Metaphysical Gloom,麦克尤恩创造了这个首字母大写的专用名词,在小说里使用了两次,作为未来人类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代诊断”。读完这部小说,我确实被那种“忧郁感”萦绕了好几天,而且确实有点“形而上学”。张教授,我知道你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有效利他”,不知道你读了这部小说有什么感觉?
张峥:我不是一个“有效利他”的信徒,那一派对我来说过于理性也过于烧脑。我只有一个很天真的执念:人性多变、复杂,但如果运气好,“外部”环境条件成立,善意和正能量的普遍涌现和“泛滥”是能发生的,进步是可能的。
小白:换句话说,你相信技术与制度条件下的“可修复性”。
张峥:“外部”这两个字我给打上引号,因为排除外星人降临,我们是我们自己的环境,“外部”就是“他人”,而他人也基于同样多变善变的人性——所以这不是一个外生的稳定锚。这么一来,咱们地球人这个系统能不能防止自我毁灭的命运,其实是非常可疑的。我对人性没有幻想,我并不乐观,但也不觉得黑色乌托邦是必然的。我的执念不是“会好”,而是“能好”——可能性没有被封死。
做我们这一行的,大致会有一种想象,认为技术能带来社会进步,所谓技术向善,即使一错再错,总抱有一种执念觉得这是可能的。
小白:你这个概率论式“天真”,也很理性烧脑。不相信人性,相信正态分布偏差有可能会让“善意涌现”。
张峥:这恰恰是这本小说对我的冲击点之一:在对未来的想象中,老麦对AI做了什么、能做什么,着墨不多但都是“点穴”之笔,百年后在灾后低能耗、低基础设施的世界里,AI是完全矮化掉的,可有可无。然而他的逻辑链条似乎都很成立。
What We Can Know直指我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惯用的自我欺骗自我粉饰,一层层解开来,哇,好难看也难堪的一幅图景。然而,且慢,下面还有一层等着你。这是老麦一直的主旋律,所以我倒好奇了要反过来问你,为什么这一本给了你更大的冲击?
小白:“知识分子状况”和“AI”果然是你的关注焦点。小说对未来AI使用场景的想象确实让人吃惊,但好像也合乎逻辑。
先回答你的问题,可能因为它特别能打动我,也可能是因为小说里弥漫的那种“失忆恐惧”。这种恐惧似乎一直隐含在叙事底层,隐含在叙述者人格中。
小说中一个重要角色珀西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而另一个人物,诗人布兰第,认为每个人都经历过某种版本的“珀西式失忆”。小说中未来2120一代,尽管上代人遭遇全球性灾难,却因为某种“基线漂移效应”(shifting baseline effect),把他们出生时的环境状况视为正常,失去了对历史、对环境变化、对曾经有过的“自然之美”的记忆。男主人公汤姆虽然对过去充满热情,却也只能怀有一种“对从未经历过事物的怀旧”,一种anemoia。
更要紧的是,整部小说的叙事本身似乎也在经历一种缓慢失忆的过程。小说开始时,叙述者几乎采用了一种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上帝视角,或者说“数据库全知视角”。他对叙述对象和环境无所不知,百年前那些人、那些事,被永久储存在“云”上。但是后来随着故事推进,叙事视角渐渐模糊失焦,变得越来越“不可靠”。麦克尤恩从个体、世代、历史情感乃至叙事机制本身,全面展现了人类看起来无法避免的失忆命运。当记忆不再可靠,伦理与审判还能依赖什么?
你刚刚说麦克尤恩在“毒舌”底下还有一层,那是什么?老麦对“知识分子”的尖刻讽刺,你好像有更深体会。
张峥:我觉得人性的可塑性、多变性和“他者”构成的环境强相关,换一个场景就不自觉地要换一身马甲(或者说一层皮肤)。我所属的这个小小职业部落,可以混迹于高校和高端工业界研究院,我的观察和自省是一层皮肤绝对是不够的。你所属的作家部落,也会转换场景,成为评委、嘉宾,随时披上需要的盔甲,换上合适的皮肤。老麦的毒舌之所以刺痛,是因为他写的不是“别人”,是我们换皮肤时那一刹那的自知。
小白:或者不自知。
张峥:老麦的这个小说中有一个拐点:假设量子计算已经实现。我一直认为量子计算真正的冲击点在于:现有的密码系统来不及更新,隐秘世界被迫透明化。老麦很巧妙地借力揭开了一层:女主人公除了自传之外,和友人、家人、情人的通讯被解密之后一览无遗。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些被透明了的碎片并没有解谜,倒反而引出了更多疑惑。
但这并不是最底层的——她最后埋在地底下等后人发现的日记,某种意义上的忏悔录,才是最逼近内心的一层。但果真如此吗?在落笔的瞬间,她对未来可能不存在的读者是如何想象的?那一层想象,难道不也是一层皮肤?
小白:她写在日记里那些事情当然是“不可靠叙述”。她这个行动里既有报复,也有面对未来读者与她丈夫、诗人布兰第的话语权争夺,动机十分复杂。
张峥:说得太对了,所以,what can we know?我现在能理解你说的“忧郁感”了——失忆恐惧是其中一层。但在老麦的想象中,更让人不安的是历史走了一个奇怪的螺旋式下沉:这个黑色乌托邦的大结构是文明的踉跄退化,从巅峰跌落之后支离破碎。这还不够,还要加上后来者对失忆的全盘接受而且毫不在乎。
小白:珀西所患阿尔茨海默症也是螺旋式下沉,踉跄退化,到最后支离破碎。
张峥:是啊。所以,what can we know?少之又少——对他人,对自己,对未来。
小白:你前面说到“环境”,互动人际环境,更大的环境,正是这小说最用力的地方。麦克尤恩一向擅长处理这些东西:特定的微观互动环境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动机、预期、行动、社会表演。过程被不断“微分”,令人难以察觉。就这么一点一点,最后却让人物跨过一条原本以为他绝无可能逾越的人性“大裂谷”,再也无法回头。
麦克尤恩那年来上海,记得他闲谈时提到现实主义。然后犹犹豫豫地说出“超级”这个词,当时你也在场,还记得么?他觉得虚构现实主义仍然有效,不过当时他说,他有些模糊想法,还没法说清楚。
张峥:你这么提一句,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小白:当代重要作家里,像麦克尤恩这样仍然对现实主义抱有充分信心的不多。大概从1990年《无辜者》起,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让虚构现实主义传统追上现代生活。我们刚刚说他对人性事件的“微分”,这实际上也是叙事技艺上的拓展,比如说“视角”,为了更好地“观察”世界和人际环境,就要有更精细的“镜头”,传统的“全知”“受限”“人称”之外,更要能在焦距、角度、透度上不断微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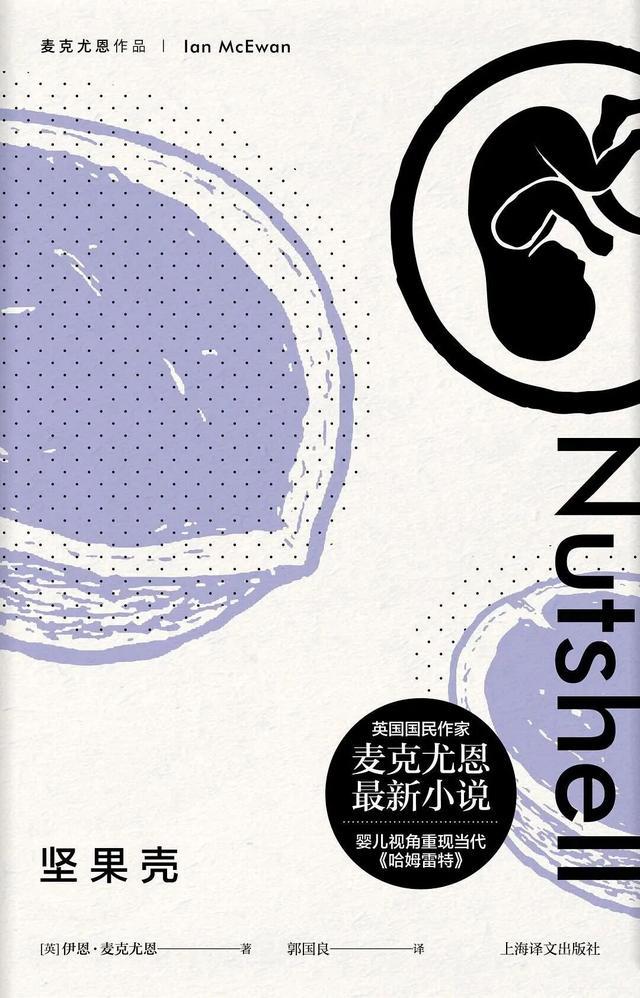
麦克尤恩近年作品,大约从《坚果壳》开始,似乎又出现一些变化,变得更有思想小说的味道。像现在这部作品,其中有些情节片断,似有更多隐喻意味。有些片断甚至有点“米兰·昆德拉”。我记得他与扎蒂·史密斯对谈时提到过昆德拉。不过这可能只是某种文体深刻变化的表面迹象,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小说的“认知光锥”,这个词是从别处借来的,我们回头再聊这个问题。
张峥:我也想到老麦提到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那些片断,断桥、幻觉、“船头下方行走”的魂魄,主人公以青年霍姆斯为偶像。我读过霍姆斯的《好奇年代》(The Age of Wonder),讲后牛顿前达尔文时代诗人和科学家之间的互动和纠缠,那是一个从现代视角看非常纯粹的年代,所谓职业科学家也是在那个时代结尾才出现。老麦骨子里有理科生的逻辑性,尚能成为一个成功小说家,又何尝能否定一百年后的后来者中没有一两个反骨,会重新拾起诗歌,被昔日的光彩鼓舞而复辟并前行呢?
小白:对,那些片断,还有比如“薇薇安”的帆船意象。
小说一个重要主题是它的名字,What we can know,在小说中的未来,往昔所有人,他们的一切“数字足迹”都储存在“云”上,叙述者“汤姆”开始时语调十分自信。作为小说中一名大学教师,他想让他生活在二十二世纪的学生们深入了解历史和人性,他设计了一场生动的教学,在教室里展现修拉点彩画,然后告诉学生百年前人们的“数字足迹”,也像印象派绘画上的点彩笔触,最终会把历史中人完整呈现在他们眼前。如此他便可以唤醒他那些迟钝的、遗忘了过去的学生。显然最终他失败了。
张教授,你对这些问题怎么看?这些越来越庞大的数据存储,越来越好的数据挖掘算法,你对生活在一个完全透明的无隐私社会,有什么看法?如小说中人提出的问题:它们能不能记录和传承“人性”,让人们跨越时间和空间联结成整体?
张峥:是不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你的问题:文字能否承担起文明复兴的载体?就麦克尤恩这个小说的设定来说,它似乎是唯一的载体。那么,如果量子计算把所有加密的盲盒都撬开了,透明了所有的文字,文明传承的机会会不会更大?毕竟,作为小说家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这种危机感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危机感有点像现在码农们担心学了小半辈子的堆代码的手艺在AI工具面前完全崩盘一样。
我绕个弯儿,先做一点关于大模型的硬科普:在大量语料里习得下一个词的预测能力为什么会涌现出类人的智能来?
其实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过我。需要转换一下视角:假如有一个上帝之眼,能完美预测下一个词,那它能做什么呢?在你的问题之后,它也能准确预测我的回答。换句话说,“下一个词”不必局限在同一个叙述者的文本里,而是可以跳过问和答的边界。这个“上帝牌接龙器”,就是第一代大模型试图用海量数据去模拟(参考了、但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复刻人脑)的工作电路,那些电路对我们现在也还是黑盒。
第二代大模型,所谓的推理大模型,是在第一代穷尽了所有的数据之后的一个突破。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把思考过程——这种原本看不见的“暗数据”——也作为语料拿来训练。我们不必细说强化学习的机制,本质上就是让模型在生成答案之前,先生成推理的步骤。
第二代大模型的威力,我想你肯定有所体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透明化一定带来提升、带来深挖的能力。但我们很多时候的行动和思考并不靠语言,还缺“肤感”。就比如我明知咱们的乐团不行,还经常要去音乐厅听一场,我的解释就是我是“带我的皮肤”去听的。这句话有点怪,不过我想懂的人自然明白我的意思。
我觉得语言还不够。那假如大模型进化到第N代,从文字到皮肤、到一切肤感都能复刻,会怎样?老麦没把对技术的想象推那么远,因为我想他已经回答了:不怎么样。因为他对人性的悲观在于人性包括了对传承的懒惰、无所谓、健忘等等。
小白:不止这些,麦克尤恩也意识到人工智能是一种行星级技术,在他想象的那个未来,人类回到互相分离的孤岛上生活,这种技术本身也已可有可无。
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跟你有些不同想法。我觉得大模型要从人类的社会文化“本性”去理解。智人跟别种动物不同,他们互相“通信”,如此才有了文化和社会,如此他们才会在20-30万年间发展成地球统治者。而“通信”就必须有“编码”。智人一开口说话,语音就是离散编码。所有的编码堆在一起,就是社会和文化。
但是到了工业时代,社会和文化的规模突然极度放大,编码信息量的规模、尺度放大到如此程度,或许这就是造成那一百年人类社会和文化极度动荡的“热力学”原因。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人们设想了各种解决方案,共产主义思想的全人类解放“工程”,圣西门主义的工程师专家治理规划,资本主义的价格/市场“看不见的手”方案,包括二十世纪人们发明和建立的复杂社会管理科层系统,包括文化和语言领域的结构主义、控制论,网络以及挖掘网络数据的算法,一直到世纪末诞生的人工智能。现在,大模型看起来好像能够解决问题:在那个高维空间里,一切被编码的都能被控制和处理,在社会管理方面,马斯克DOGE可以说是这种想法的最激进试验。
张峥:我的观点可能更简单一点,人类社会目前面对的大动荡的原罪在于各种各样的极化,交流(你称作“通信”)是人类文明得以从启蒙走向繁荣的必要手段,数据化的结果是把其中的副作用指数级别的放大了,这个我后面再谈,你继续。
小白:但我有一个疑虑,就是“离散”编码,那就一定有被压缩、被丢失的冗余信息。我们人类的智能、创造力,有没有可能因此也一起被压缩,被丢失?有没有可能,从我们大脑“湿件”里生成的、那些难以被“编码”的东西,梦境、幻觉甚至各种人格分裂症状,都与创造性想象同源?在大模型框定的地图上,人类还能不能开疆拓土?
张峥:落到字符就是离散化,肯定有信息损失,不过在我看来不是问题的根源。大模型的输入输出都是离散的字符,但内部运作的隐空间是连续的,理论上是可以表达无限的可能,所谓“一沙一世界”。
小白:不过在技术迭代事件不断扑面而来的时代,就连这些想法也是快速更迭。前几天仔细听了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那个三小时对话,又去找了他一些论文和录音来看。隐隐觉得他的说法也很有趣,也许真有一个“柏拉图空间”,各种智能、代理、模式都是那个空间在物理世界的投影。人类本来也没有“发明”,只有“发现”,或者说通过某种“接口”,从柏拉图空间朝物理世界一片片把模式拉下来。但这已是哲学问题,我们今天不聊,哈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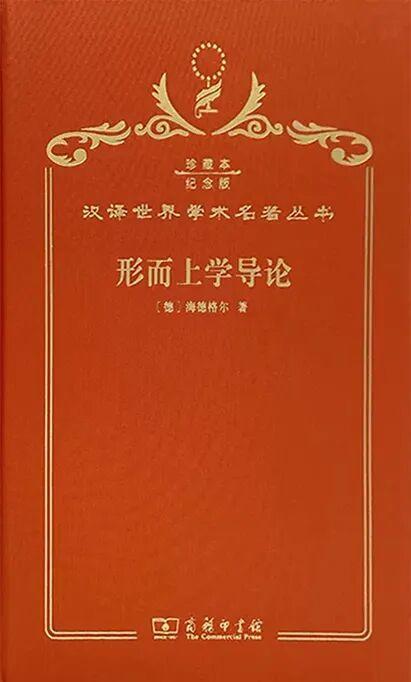
行星级技术与叙事规模
小白: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提到过现代人与“行星级技术”的相遇。后来他在1960年代接受《明镜》采访时,把二十世纪中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都归因到这场“相遇”事件中。
我们现在看来,“事件”可能会比海德格尔想象的更漫长。它不仅持续至今,而且将向未来不断延续。海德格尔说行星级技术把人类从大地分离,“连根拔起”。
采访中提到他与勒内·夏尔——法国诗人和抵抗运动战士——在普罗旺斯长谈。他们聊到当地正在建造的火箭发射台,聊到乡村被摧毁。海德格尔说他们不是感伤主义者,也不会美化田园牧歌,但是人类被连根拔起,这件事情正在发生,这将是一切的终结。而且像你前面说的一样,勒内认为诗歌有望成为拯救力量的候选人。
我知道你也是诗人,你看到这小说结尾部分有关诗歌和散文的说法了吗?There are occasions when prose must eclipse poetry.(有时候散文必须侵蔽诗歌。)
张峥:年少的时候写过一点长短句而已,真不敢称诗人。
小白:我们在麦克尤恩这部小说里,不仅看到小说家与海德格尔、与勒内·夏尔同样的、对这种“失去家园”状况的悲伤,也看到老麦正在思考如何用小说形式来展现这种情景:小说中有一个“元小说时刻”,其中人物说Derangement could not have been addressed by fictional realism.It was inadequate to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虚构现实主义无力讲述“大混乱时期”,因为它不足以应对问题的规模。)
Derangement是小说中一个专有名词,小说中这个“大混乱时期”在2030年后被广泛使用,专指21世纪上半叶,此时全球变暖、灾难加剧,人类社会出现“集体认知失调”。麦克尤恩那段话是说,现实主义小说对“大混乱”失效,面对如此大规模、大尺度难题,小说无能为力。这想法可能来自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那本《大错乱:气候变化与不可想象之事》(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高希本人也来过上海。
张峥:这两年外国作家来得好像少了。
小白:说它是“元小说时刻”,因为麦克尤恩在这部小说中,正像是在实验一种新写法,试图超越传统的虚构现实主义。
你一开头就提到小说处理人和环境的关系。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通常处理的都是小环境,即便有所谓“长河”小说,讲述个人、家庭或者社群在整段历史长河中的命运,其叙事在实质上仍然只是发生在微观环境内部,宏观环境只是作为背景被并置,把宏观转译为微观命运。虚构现实主义从未真正处理过宏观环境。
但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叙事在各种尺度不一而互相关联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它把宏观非人类行动者纳入现实主义,同时在多种尺度间建立连续可推演的因果链。这似乎是一种崭新、也大有希望的现实主义小说。我们在此初见形制,麦老以77岁高龄作此“变法”,真是令人钦佩。
张峥:作为一个极其业余而且科幻只占阅读时间一小部分的文学爱好者,我没法置评。
不过,我倒觉得有一点值得一提。之前我读他的《像我这样的机器》,非常惊讶于老麦对技术细节的把握。在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工种叫Project Manager,这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头衔,他们的工作是把用户体验和工程实现衔接好,让用户上手更容易、更直接。PM做得好不好,会直接影响一个产品的接受度。如果说老麦在处理一个跨越很大的“大混乱时期”,那他花的笔墨极少,可是逻辑性又非常强,给这部小说很强的骨干支撑。
小白:正是,你确实是一位“资深首席科学家”(哈哈哈),对项目“工程骨架”的复杂度有直觉。
张峥:我举几个例子:为什么核战终于发生?因为AI不约而同地给出了“最好的防守是进攻”的决策建议。这也导致AI最后被各国国有化、限量使用(所以他还是相信一点人类的理性)。气候变化一定是按现在科学家预测的那样走向吗?不必,自有核战的后果来帮你提速。为什么消停了?因为世界成为了万岛之国,战争的负担急剧上升。为什么技术后退了?因为世界变成万岛之国,谁和谁都脱了钩。为什么创新变慢了?因为世界变成万岛之国,岛民基数这么小,聪明人孤掌难鸣。等等,等等。
当然,还有量子计算的到来,解密了今天的所有加密文字,过去的文本一览无遗,这是小说家麦克尤恩对文本本身的反思基础。
可以说,老麦作为一个小说家,对技术的把握不是单点的,而是全局性的、有连续性和逻辑性的。我有一次回复旦,在一个活动里做嘉宾,被问到对未来的想象,我说那是科幻小说和思想家们的“重灾区”,各种说法都有。但最最黑色乌托邦却又有逻辑的,在我目前读到的,就是老麦这一本了。
虚构现实主义与“认知光锥”
小白:要谈叙事环境尺度,先要谈人对周遭环境的直接感受能力。
根据PubMed(美国国家生物医学文献库)上一篇2023年论文,它假设智人诞生至今25万年(这数字大概取了各种不同人类考古学假设的中位数),这篇论文通过全基因组数据分析,说25万年间人类平均世代时间为26.9年。拿25万年除以26.9年,我们假设大概能得到,智人诞生至今人类一共有将近9293个世代。
在所有这些世代中,只有两代人看到过阿波罗8号从太空拍回的地球照片,获得过真正的“全球视角”。就像前面所说那篇采访里,海德格尔也说他第一次看到这幅照片时候的震惊,感觉到自己被“连根拔起”。
我们还可以这么说,在这9293代人中,最近3代人的幸福安定程度,此前9290代人无法想象。冬天晚上把家里暖气开到20摄氏度、热水开到50摄氏度,在增压喷头下舒舒服服淋浴时,我们可能不会想到,在清朝连皇帝也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
张峥:我觉得洗澡时室温可以开到25摄氏度,哈哈哈。
小白:我们如今生活在这样一个微观环境里,日常生活稳定有序,对自身周遭小环境似乎有很大掌控感。这跟由此上溯三代人的感受完全不同。仅仅在三代人以前,他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危机甚至可以说“杀机”重重。那时候每个成年人都会有几个在幼年时候就夭折的兄弟姊妹,一场感冒都让人无法抵抗。如果是一个农民,十年里可能有一半年份会遭遇水旱饥荒。但是从另一面看,他们的宏观环境又似乎十分稳定,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
就这点来说,最近这两三代人恰恰相反。我们的微观环境相当安定,但宏观环境似乎动荡不宁。我读小学的时候就能从《参考消息》上读到欧洲恐怖主义活动,现在更是全球各地的各种坏消息每时每刻发到智能手机上。瘟疫早就逸出社区,成了全球性事件。我记得扎蒂·史密斯有一个短篇,不知其名的灾难从天而降,整个故事弥漫着一种不安。
张峥:你说得特别对,我们这几代人在技术进步的喂养下微观生活变得极其丝滑,可是剧变的轮子似乎时时刻刻从头顶碾过来,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反差。
小白:传统虚构现实主义是在这两三代人之前发明的东西,它的整个叙事逻辑,都只为处理人物周围的微观环境。它们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认知训练装置,让人们去学习如何应付处理这个小环境。它从不擅长真正去应付那个大环境,面对宏观环境给人们所带来那种动荡不宁的感受,传统现实主义捉襟见肘,这也是小说读者越来越少,大家总是说“生活比小说更精彩”的一个深层原因。
但是从另一面看,到目前为止,人所发明的、能够真正建构复杂生活的叙事,仍然是小说。如果以后大家都不读小说,我们的“叙事”很可能变得越来越简单。我打个比方,一个年轻人新进机构上班,他与资深同事发生某种办公室冲突,这其中自然有复杂细微的人际互动因素,小说原本很擅长处理这些东西。可现在小说原本占据的位置,被一些貌似宏观、实际却很简单的叙事替换了。于是复杂的人际因素,最终被解释成“老登”和“渣男”的故事。这只是一个简单而常见的例子。
我的想法是,如今似乎需要另一种现实主义小说,一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多种尺度上处理叙事的小说,并不是仅仅将它们并置,而是在多种尺度之间构建——就像你先前说的——具有连续性、合乎逻辑的叙事关系。
在宏大尺度上,把包括气候、病毒、AI算法这些“非人类行动者”,提升到与人类角色同等的叙事地位,与小说人物身处的微观环境密切交互。像你前面提到AI逻辑链条引发核战,那么统计学概率和算法逻辑也代替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人性,成为推动叙事之手。
张峥:作为一个读者,我同意小说的复杂叙事能力几乎独一无二。读托宾的《魔术师》,麦克尤恩的很多作品包括这一本,能让我感觉到主人公们的呼吸和体温。不过,我加“几乎”二字,意思是文字也有捉襟见肘的时候。我读完《我的天才女友》不久电视剧正好出来,有些激烈的冲突场面(比如那场婚礼),电视剧完胜,但这个四卷本的精彩笔墨都花在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用心理活动的细腻笔触撑起从少女到老年那么长的跨度,电视剧怎么看都觉得平淡、隔膜、无法代入,最后放弃,而你知道我的习惯——弃书弃剧很少,比这个烂得多的剧一旦不慎入局,都会毫无道理地坚持到底。
这就引出两个问题:在“连根拔起”的时代,小说能不能做到复杂叙事?紧接着就是:还需不需要复杂叙事?
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答案是肯定的。《魔术师》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还有一类我特别喜欢的书,是所谓的“叙事非虚构”(narrative nonfiction):本质上是历史,但和干巴巴的传统历史书不同,作者用小说的手法贴身描述人物本身,用慢镜头刻画“连根拔起”的过程。我读过埃里克·拉森(Erik Larson)的所有作品,去年还读过一本我很推荐的A.J.Baime写杜鲁门的The Accidental President。对我来说,越是“连根拔起”的时代,越需要小说家入场。
小白:说句实话,我一直觉得虚构/非虚构是出版业商品分类,区别只在一种是“有料”虚构,一种是“无料”虚构。
张峥:话说回来,我需要有复杂叙事的小说,不代表大家需要,作家要靠市场吃饭。这是有点悲催——也算是对第二个问题不是回答的回答。“连根拔起”的时代大家的阅读需求会有变化,也联动了表达方式。
说一个可能不为人知的“常识”:飞机上的餐食,比一般的要咸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航空公司发现,在噪音环境里,人的味觉会变迟钝,平常的盐量不够。你有没有注意到上海作为一个江南城市,大众餐饮里川菜、湘菜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
小白:你的意思是说,在这个高速时代,“乘客”们都需要重口味?
张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常说自己是小调体质,听古典乐一般会喜欢第二乐章,练爵士明明大调也会弹出小调的味道,等等。所以前不久毛尖和许知远“交手”,按理说我站哪边是没有疑问的(虽然我早过了把自我感动当日常的阶段),但我偏偏也很喜欢毛老师的尖舌利嘴,那种快活和尖刻并存的爽感。为什么呢?可见我也变了。
小白:我站在毛尖老师这边,不解释。哈哈哈。
张峥:回到关于现代微观生活与剧变世界的感受差异,我特别同意。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大概需要更新了:技术把底层需求都安排好了,可是我们真的觉得安全吗?感知即现实——丝滑的微观生活并不能消解那种悬浮感。
至于之前那么多代人的体感如何,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信息时代,轮子飞转的声音到达得更快、更响、更刺耳。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讲,早点知晓坏消息——不管真假——都是有益的,因为没什么比存活更要紧的了。所以坏消息从来都自带飞毛腿,到了网络时代,真真假假的消息之多、获取或被获取之容易,我觉得早就过了一个阈值,溢出了我们认知的忍受度。我看过一个结果,谣言比真相的传播速度要快,猜猜多少倍?六倍!
而我们已经上瘾了——谁能超过五分钟不看手机呢?
前一段时间在北京有一个活动,讲的是人才引进问题。我说好的人才在当下必须有一个特点,就是很焦虑。世界极化到这个程度——政治的、经济的、身份的,各个维度都在撕裂,而且相互叠加——人们觉得必须选边站、选地方、选身份。物理的迁徙,心理的漂移,都是症状。今天地缘政治的乱局、民粹民族主义的浪潮,根子都在这里。
既要、又要,而且不可能全要,如何不焦虑?这就是“连根拔起”的滋味。
如何抵抗悬浮,抵抗失控,是一个很重的命题;多撒盐多放辣,竖起耳朵听飞轮的滚动……都是会上瘾的假解药。
小白:我那天听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还有一个被他说服、至少是被他打动的地方。他假设一种“认知光锥”,这个词他是从相对论那里拿来的,我想相当一部分是隐喻和联想。在莱文那里,认知光锥是你能采取“积极行动”的 最大目标范围,而不是单纯指认知边界。你的目标只有10-20微米,那你是细菌;你能在几百码范围内积极行动,那你是一条狗;如果你说你能关心地球上所有的人,那你可能不是人,是某种“神”。
因为他说,比如有一件灾难发生在10个人身上,你会有一些痛苦反应,可是如果这件灾难发生在10000个人身上,你的反应不会增加1000倍,如果1000万人,你也不会增加100万倍。你的反应能力是线性的,不会跟随范围尺度倍增。你也无法在1000万人的目标范围内采取积极行动。
我觉得莱文在这里表达的观点,越出其生物/物理/认知的学科边界,甚至具有了某种道德哲学意味。它隐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关于小说里打动你的911事件场景,也关于先前聊到的小说叙事对环境尺度的处理能力。甚至也可以解释这部小说里“大混乱时期”一代人,面对全球变暖灾难会集体认知失调,因为那超出了“认知光锥”。
张峥:迈克尔·莱文那个播客咱们一起听了,我打算有空再回去听一遍。我补充一点点小科普,人脑对数字的理解有一个数字线的概念,自然数(比如1,2,3……)在上面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更无法有体感地体会“天文数字”。我在某处读到过数学家的大脑对数字的感觉和普通人不一样,是立体的,也许是天分,也许是训练。
莱文的“认知光锥”是不是道德哲学我谈不上来。按我们共同的好朋友严锋教授的话来说,就是无论如何,底线在于不可以“在坟头跳舞”,死了一个人和死了1000万个,不应该有区别。
再补一句:坐拥万亿级参数、推理动辄千瓦的大模型能行吗?答案是也不行。我最近有一篇和大模型合作研究大模型根本缺陷的论文,其中一个结果是:大模型对数字的理解偏离了数字空间的严谨要求,更“过分”的是,大模型有一种“计算性裂脑”现象,可以把一个算法解释得头头是道,但自己执行起来肯定会犯错,知行不能合一。
但它能做到“不在坟头跳舞”,因为大模型们虽然对齐的文明价值有偏差,但这个在基线之内。
所以,what can we know? 读完这本小说,余震绵绵,知道了一大堆负面的、否定的,也难怪你要忧郁一小把。
小白:总之,What we can know 不是一个信息问题,它是我们能够“承受和行动”的范围尺度。当行动尺度与灾难尺度不匹配,认知失调可能会变成一种理性策略,而忽视其道德失败。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虚构现实主义的小说叙事来放大我们的认知光锥?
本文原刊于《长江文艺》2026年第2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来源:张峥、小白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