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是朱颜改》是张曦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入其20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10篇,内容大致聚焦于外地移民初到上海,定居上海的奋斗及心路历程。10篇小说似乎各自独立成章,但又可视为一整部作品,人物及其命运具有连贯性。作者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探索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在魔都的生存沉浮,从稚嫩激烈到沉稳成熟,没有一条路是为她们预备的,但她们仍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期待,并踏实走在自己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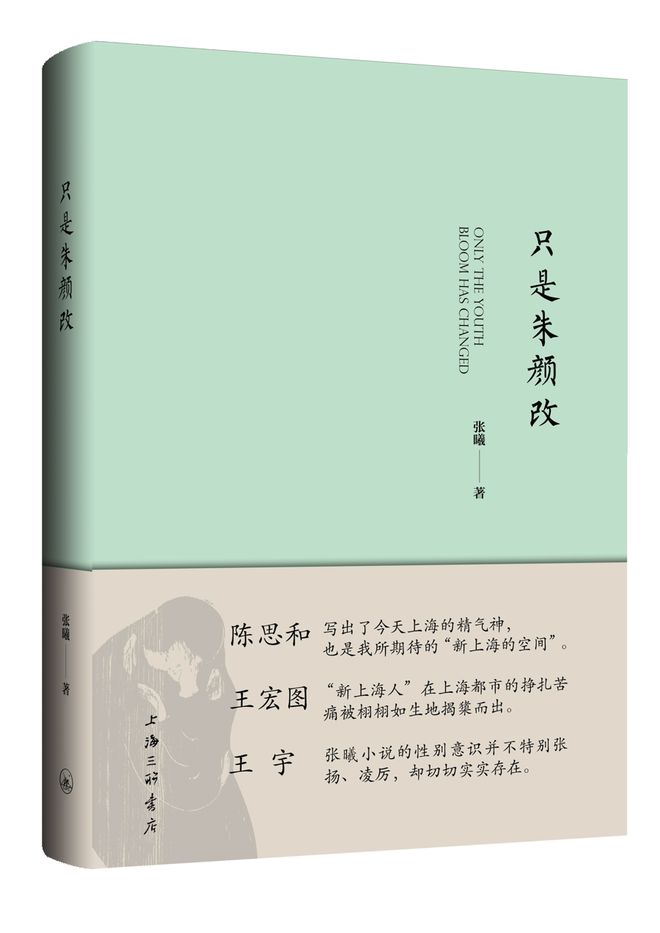
《只是朱颜改》,张曦 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内文选读:
序言
张曦的创作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创作数量不算多,但每一篇都在她的创作道路上留下了扎实的脚印。最近她从自己的作品中选了十篇短篇小说结集成书。我有幸先读为快,在这里可以简略谈点自己的感想。
张曦出手不凡。2002年《小艾求职记》刊发在《上海文学》第9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张曦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当时她还在复旦攻博,文字刻意绮丽,写的也是身边场景,她塑造了一个从外地到上海寻找发展机会的女孩小艾,换句话说,是我们今天大批激流勇进的新上海人群中的一员,一个先驱者。即使在二十多年以后读来,岁月的磨损没有减弱我对这个人物的印象,我依然被人物的真实和生动所感动。小艾没有在上海名校就读,她来自中部城市一所大学,“有一种对于上海的难言的渴望”。于是她极其理性地安排了自己的进军上海之路,从中原地区的小城市,一步步向外走:先是考取了省城一所大学,又到南京读硕士研究生,接下来她的目标就是上海了,她瞄准了这个妖娆美好的城市……这里,作家用“妖娆美好”四个字描述了小艾心中的上海印象,继而也成了她笔下一系列外省女孩心目中的上海城市风韵,这从她所写的一系列上海故事里都能够体味出来。小艾“这一个”人物性格,作家下了这样的定义:“小艾的野心,就像她的热情一样,埋得很深,但是非常固执。”

为了强化人物性格的典型性,作家还做了一个近似冷酷的铺垫:“她的家在中原一个贫穷的、荒凉的城市,她的父母是一对怨偶,整天为了芝麻大的事情打闹不休。她对父亲的愚蠢和无能、对母亲的淫荡与粗鲁感到痛心和隔膜,更对那个死气沉沉的城市,充满了厌恶和鄙夷。她想自己真是投错了胎,一切全乱了套,上天待她实在太轻率了,她必须格外珍惜自己。”这就是小艾——外表看上去纤弱、幽怨,白裙飘飘,似乎还表现出不解风情的单纯女孩,内心深处却发出凄厉的怨毒的呼喊。“投错了胎”与“格外珍惜”构成绝对的张力,“上天”不眷顾,就靠自己努力,自己就成为自己的“天”。
“投错了胎”是一种特别绝望的自觉,似乎是一种无可选择的原罪。当一个女孩对父母怀着这种近似恶意的理解,对故乡血地充满厌恶与鄙夷,那么,她的精神成长道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义无反顾的决绝之境了。她珍爱自己,绝不是爱那个在小城里长大的自己,而是狂热地爱着自己尚未展示的未来,一个即将与“妖娆美好”的新环境融汇一体的自己。我之所以要特别举出“妖娆美好”的上海性格,是因为上海这个城市本来可以展示多面复杂的性格,但在小艾及小艾们的心眼里,单单选中了“妖娆美好”的一个侧面,她和她们并没有想好如何在这个现代大都市里安身立命,创造精神财富,她们只是迷惑于繁花似锦的梦幻和想象。正如小说里有一个比喻:她穿着极其素净的白毛衣、牛仔裤,背景却是烂红的大朵玫瑰(窗帘),流光溢彩的,她想她是要融进这样一种五彩的背景中去了。

其实生活会告诉小艾们,这种流光溢彩的繁花梦,她是很难融入进去的。但是作家没有这么冷,小说的最后,小艾对能不能入职她所向往的出版社已经不感兴趣了,她开始沉醉在谈婚论嫁的准备之中了。这种喜庆式的结局,似乎有点好莱坞式,不过,留下来一丝阴影在张曦同时期创作的另外两部作品里都得到微弱的反射:那个叫小艾的女人又一次出现在《阳台上的女人》的文本里,不过那已经是一个发胖、俗气的单身女人了。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小艾看作是同一个原型的话,那么,《小艾求职记》里那个意气风发进军上海的女孩,从求职梦到结婚梦的悲剧下场可想而知了。在另一篇小说《芳邻》里,那位来自陕西农庄叫作施自红(柿子红的谐音)的女孩,与小艾做的是同一个梦,人生态度也同样决绝,她渴望着进入妖娆美好的繁花生活,还把另一个女孩也拖进梦境,但结果是,两个外省男子用年轻生命的夭折打破了她们的美梦。这样的结局似乎有点刻意安排,但揭示出一个真相:所谓的“妖娆美好”的表象后面,仍然是凄厉和绝望,甚至有一点疯狂。
我比较没有把握的是领略《办公室里的七朵花》。这篇小说也是张曦同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它含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故事写的是一个初入职场的外省青年,面对一位迟暮美人的疯狂心理。这个名叫郑莲心的女人,生就古希腊雕刻般的美貌,无可挑剔的华丽与高雅,还有非凡的背景,在外省青年的眼里,“她站在那儿,高大、壮硕,如一座饱满的山丘,即便秋老也有满山的醉紫烂红。”可以想象郑莲心年轻时代的“妖娆美好”,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座城市,而且是外省青年百般羡慕却始终无法进入的卡夫卡式的城堡。从外省青年先是惊艳、继而企图占有、最终失败的疯狂心理三部曲中,读者不难体会小艾/小施/小王面对上海/郑莲心似曾相识的激烈的情绪反应。我之所以称这篇小说具有象征的意义,是因为郑莲心这个形象含混而暧昧,在不同场景下她都是叙事者主体情绪折射出来的多面镜像,她的迟暮而性感的模糊形象,与《小艾求职记》里的“妖娆美好”印象一样,构成了张曦笔下的新上海人眼里特别的上海之象。
(本文节选自《只是朱颜改》序言)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