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书话丨汪薇:温暖的伤痕——评《一池秋水》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自我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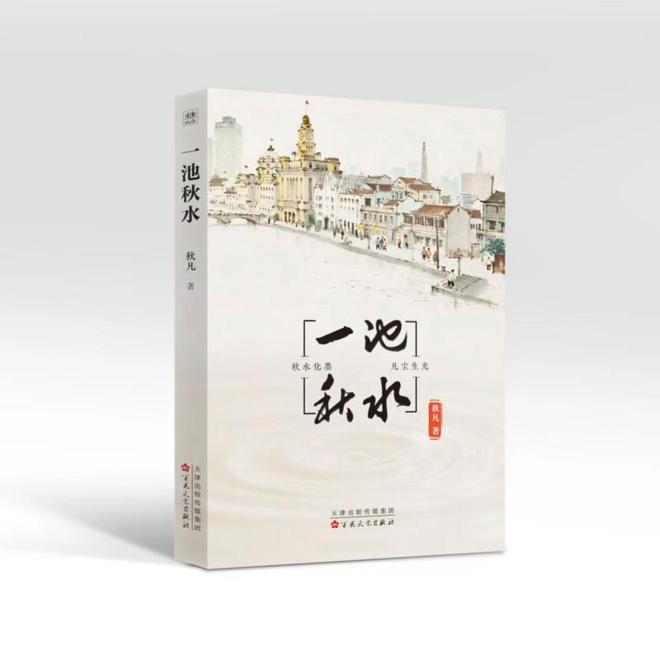
温暖的伤痕
——评《一池秋水》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自我建构
文/汪薇
秋凡的文字是极富诗意的,单是她的散文的标题就足够引人好奇了——《卸了“锅儿”过大年》《时光缆索上的那双眼睛》《今生,站出树的姿态》《她的口袋里永远藏着一颗糖》,这些题目像一扇虚掩的窗,让我们忍不住想推开,去一窥究竟她笔下到底写了怎样的故事。
这位重庆开州女作家,似乎很热衷于去书写那片她所生长的土地上的人或事。在她的笔下,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更多的是底层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她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纯真世界,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勤劳、勇敢、善良的化身,里面的所有花朵、树木、大海都是可爱且浪漫的。《一池秋水》中的每个故事,作者在里面扮演了许多角色,她是女儿、姐姐,也是妈妈、妻子……但印刻在这些身份之上的,却是一位站出了像“树”一样姿态的倔强女孩儿。我想,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散文集,我会说,“这是一部不屈服于命运的女性心灵成长史”——是自我救赎,亦是与过去和解,对未来期待。
唯美主义倾向是秋凡散文中抒发个人情感、刻画人物形象、描绘寻常事物的一个显著特征。作者从女性独特的细腻视角向我们展现了女性世界独有的诗意想象,这主要表现在其擅长挖掘和描摹生活中的寻常物象,于细微中见精致,从而达到诗意的升华。她写童年的乡土生活,不是直白地情绪表达,而是把情感藏在“美”的意象里。如“清澈的河底聚着一群小鱼喁喁私语,随着一个女孩的响指霎时散开……我学着母亲的模样撒上些洗衣粉揉搓起来,然后用小小的手将袜口浸入水流,看着袜子鼓胀起来,像网住了一只水精灵(《一池秋水》)。”又如“甜高粱,把自己站成了一个优雅的舞者……阵阵晚风吹来,舞者的裙摆发出了‘沙沙沙’的响声(《夏之物语》)。”这些带着触觉、听觉、视觉的细节刻画,让读者仿佛也置身于那片土地,感受到了河水的清凉、作物的清甜气息。
作者还擅长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赋予平凡的乡土事物和劳作场景以精致的美感,将自己的审美情感融进了文本的艺术化加工中,不仅为读者建构起了一个纯粹、生动且温馨的乡土,还蕴含了作者对童年那段虽短暂却充满美好回忆的乡土生活的眷恋。即便是写原生家庭的苦涩记忆,作者也有意识地带着一种诗意的审美。比如在《寂静之地》中,“我”穿着心仪的鞋子,身轻如燕,如一朵轻盈飘逸的云。然而画面一转,这朵云却变成了一只心事重重的风筝。“身轻如燕”“轻盈飘逸的云”,体现了少女穿上新鞋的愉悦满足,作者把这种对物质满足的情感转化为空灵、柔和的审美体验,让愉悦情绪不再是抽象的感受,而是有了一种像云一样飘起来的轻盈感。但紧接着,“云变成心事重重的风筝”,又把这份轻快拽回现实,风筝的“飘荡”是自由,可“长线的尽头”牵系它的不是风、不是大地,是“躬身忙碌的菜农”。这里的意象反差特别妙,身体越轻,心事却越重。新鞋的快乐,和父亲卖菜换钱的辛苦,像风筝和线一样紧紧绑在一起,甜里裹着现实的涩。
秋凡的大部分散文作品,是其对代际叙事和自我建构的自觉书写。秋凡的散文,看似在写父亲、母亲、燕子、娅苏等“他者”,实则却是以文字为媒介,实现对自我的建构。她以原生家庭的创伤为起点,以成长中的体谅与和解为路径,在写他人的过程中照见自己,在与过去对话的过程中完善自我,最终建构出一个“敏感细腻、坚韧通透”的理想人格形象。
秋凡从不回避原生家庭的创伤:父亲常年在外打工,陪伴的缺失让父女关系疏离;因弟弟被烫伤无法做重体力工作,成绩优异、热爱读书的她被迫辍学,甚至她还要承担弟弟一半的学费。这段记忆,是她心中长久的疙瘩,是少女时代倔强与委屈的根源。在其散文中,作者反复回溯这段记忆,通过直白的叙述向读者袒露那些未曾言说的少女心事,似是在诉说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对于这段青春创伤的记忆,作者并非简单地陈列,而是经年以后带着对人生的阅历重新审视父亲当初的选择。父亲偷偷藏在酒水柜里的一万块钱,以及父亲电话里的那句“以前苦了你”,或许是一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对于女儿笨拙却又郑重的愧怍(《父亲还债》)。在《寂静之地》的结尾中,作者写道:“当回忆的思绪从18岁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下旅行归来,我又拥有了一次成熟的父女对话。”我们未尝不可把这视作是作者借助文字对过往的创伤记忆作出的一种心理补偿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她从被伤害的少女,成长为能体谅他人不易的成年人。
秋凡写身边的人,无论是发小燕子,还是创业女性娅苏,都带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投射。她笔下的人物,都是“坚韧、善良、懂得体谅”的形象,而这正是她想要建构的理想自我。写燕子(《燕子年年归》),她突出燕子的倔强与柔软。与父亲争吵而放狠话“不养你”,却在父亲患尿毒症时奔波照料;写娅苏(《灿烂的生命之花》),她强调其在绝境中的韧性。从小被遗弃、养父自杀,却从打工妹成长为“巾帼新农人”,带动乡邻增收。这些人物都有其各自的闪光点,对苦难不放弃,对亲情不记恨,对他人有担当,而这正是作者自身品格的一面“镜像”。她写燕子“血浓于水的亲情不会变,只能改变自己”,其实是在表达自己的亲情观;她写娅苏“水泥缝里也能开花”,也是在肯定自己从辍学打工到文字创作的这段成长经历。这种通过他人塑造自己的方式,使她得以在文字中不断强化理想中的自我形象,最终完成了对自我建构的自觉书写。
秋凡的散文以温情见长,善于用舒缓的表现方式展现底层人民的生活百态与人性光辉。这份温情主要源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人性之“善”的颂扬,其二是对故土深切的“乡愁”。在《一池秋水》中,人性的善良表现为一种超越苦难的坚韧品格。《生活那条河》中的老王,妻子为救母狗意外离世、儿子闹心不争气,然而这些生活的苦却没有压垮他,反而默默承担起了抚养孙女长大的责任;《有一种亲情若李子》里的大奶奶,同样遭遇命运的重创。丈夫不幸遭遇车祸离世,女儿也被人贩子拐卖,独自守着一片果园。她表面严厉,吓唬偷李子的“我们”,却在“我”真诚前来购买时坚决不收分文;更在“我”因考试成绩不佳不敢回家时,主动送来李子和米糕,温言劝慰,甚至出面与“我”的父亲沟通。此外,《刀要在石上磨》中的陈伯、《手执“篾竹条子”的田老师》中的班主任田老师……他们虽处境各异,却无不透露出根植于乡土与人心的“温良”。这种温良,不是未经世事的单纯,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选择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之重,是一种在石上磨、在事上练的人性光辉。
“乡愁”是贯穿这本散文集的一条重要主题,作者反复在回忆中写自己儿时的乡土生活,于她而言,故乡是未被污染的心灵净土,那里保存着她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与温暖的亲情记忆。她笔下的乡愁充满生动细节,无论是姐弟挑水时的嬉笑、偷果被狗追的狼狈,还是弟弟为被宰的鹅“悼念”的童真,都是其情感的具体呈现。最终,所有这些记忆都指向了现实的物象——老屋上的那把锈锁、那片荒草地坝和整个“太极村”(《我的太极乡愁》)。通过这些意象,作者将个人的乡愁升华为对一代人精神原乡的普遍书写。
秋凡的散文,其内里是自我建构的坚韧内核,外层是唯美主义的温润光泽,而包裹其间的,则是温情叙事的柔软暖意。正如她自己写道“夏季的物语,皆是光阴的故事”。在17岁那年的盛夏,秋凡离开了她的故乡。从此,她踏上了寻找自我的漫长征途。所幸,她最终找到了自己。
我很高兴在这本散文集中,见证一位女性的成长和内心世界。她,或许仍有不完美的地方,但人生中究竟有什么是尽善尽美的呢?
作者简介:汪薇,绵阳师范学院文学院中文系学生,绵阳师范学院青春文学社社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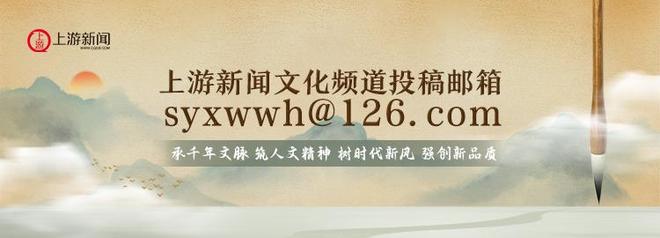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