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百度APP畅享高清图片
曾记梧桐秋意暖
文/刘燕子
梧桐叶落秋已深。
操场边那几棵梧桐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便簌簌作响,时不时飘下几枚黄叶。
下午三四点钟时,太阳斜挂,光线是那种有气无力的金黄,照着一群正在为“三跳比赛”练习的孩子。我是他们的班主任,刚接手这个六年级一班不久,很多孩子的名字都还叫不出来。该如何训练学生,也拿不出具体的方法,只能站在一边,看他们摇绳、跳绳。
此时,他们一个个小脸憋得通红,头发被汗水濡湿了,贴在脑门上。
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摇绳的两个大个子绷着脸,似乎把全身的力气都灌注到那条大绳上,身体随着手臂的摇动使劲晃动着。那本该欢快如燕的跳绳,此刻却像条沉重的鞭子,甩在地上,发出一声声疲惫的、拖沓的“啪嗒”声。
“老师,我跳不动了。”班级最活泼的一个男孩子,半弯着腰,扶着膝盖,大口喘着气说。眼睛里,那簇平日活泼跳动的火苗,此刻暗暗的,快要熄了似的。
“我也是,肚子里空空的,没力气了。”旁边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姑娘也小声附和,声音软绵绵的。
看着那一张张汗涔涔的、有些发白的小脸,我心里一紧。正是长身体的年纪,下午折腾了这么久,那点午饭早已消耗殆尽。一种母亲似的本能,压过了初为人师的几分无措。我得做点什么。
我匆匆交代了体育委员几句,回到校园里的宿舍。翻箱倒柜才翻出一袋大米、一罐白糖。那个时候我参加工作不到两年,很少做饭,没有冰箱,家里基本没存留食物。我回忆起同事做饭的样子,点燃煤油炉。烧水、淘米,守着一朵如豆的小火苗,锅里的水半天都没冒泡,偏偏窗外的秋风钻进来撕扯着火苗。我赶紧找来一块纸板围在炉子旁。锅里好不容易升腾起水汽,米粒上下翻滚,慢慢舒展开身子。水汽氤氲上来,扑在脸上,是湿漉漉的暖意。
费了好大的劲儿,一锅稀饭终于煮好了。家里连咸菜都没有,我抱起罐子,撒了一层白糖。梧桐树叶仍旧在窗外喧哗,一股醇厚、朴实的香气充满了小小的厨房,给这个透出清寒的下午增加了几分暖意。
我端起盛满稀饭的大锅来到操场边时,夕阳正把最后的金光,慷慨地洒在地面上。孩子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
“是稀饭!”他们惊喜地叫着。
一双双小手小心翼翼地捧着碗,鼓着腮帮子,呼呼地吹着气。然后,便是一片满足的啜吸声。那个喊饿的男孩子,喝得最急,鼻尖上都沾了亮晶晶的米汤;那个羊角辫的小姑娘,则小口小口地抿着,眯着眼,像一只在午后阳光中晒得惬意的小猫。刚才笼罩着他们的那层疲惫的、灰蒙蒙的雾气,仿佛被稀饭的热气一冲,倏地消散了。他们的脸颊重新红润起来,眼睛里的那簇小火苗,又“噗”地一声,重新亮起来。
后来的训练,情形便大不相同了。跳绳甩在空中,是清脆的“嗖嗖”声;落在脚下,是轻快的“哒哒”声。他们的身姿,又恢复了那种属于少年的羚羊般的弹性。
那年的“三跳比赛”,我们班拿下了全校第一名。那个跳双摇的女孩子,甚至还一路跳到了县里,捧回了奖状。在一些老教师眼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缺乏教学管理经验的新教师,凭什么把学生训练得如此优秀。
多年过去了,很多细节在我的记忆里都已渐渐模糊。唯独那个下午,那锅热气腾腾的稀饭,那些捧着碗的、满足的小脸,以及弥散在清冷空气中的、朴素而温暖的米香,却像一幅被时光精心装帧的画,越发清晰地挂在心壁。
如今,我早已不是那个青涩的新教师。当校园里的梧桐叶绿了又黄时,我依然记得那个下午。教育,并不总是庄严的训诫。有时候,它就是这样简单,简单到只是一锅及时的稀饭。
那清冷秋日飘落的梧桐叶,见证了一个新教师的成长:老师与学生的距离,也许只隔着一碗稀饭。古人说:“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在我眼里,老去的只是秋色,沉淀下来的却是超越岁月的温情。我与学生用一锅稀饭的温度,焐热了彼此生命中值得珍藏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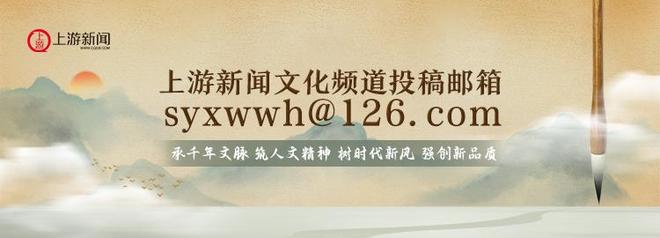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