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谈长篇新作《橘红》:让史料里的广州“活”成小说
日前,鲁迅文学奖得主、天津作家王松的最新长篇力作《橘红》在粤剧艺术博物馆隆重首发。这部历时近一年创作,最终成稿38万余字的小说,以广东道地药材“橘红”为线索,以粤剧在津门的传播为纽带,纵横勾勒了从广州西关到天津胡同,秦、周、那三大家族六代人跨越一百八十余年的悲欢离合与命运流转,是一部融汇粤剧、中医等岭南文化的厚重之作。

广州西关三角市大巷的“荣宝源老号”,是秦厚仪家族世代经营的药栈,却因一场意外戛然而止。秦家之子秦天贽自幼痴迷广府大戏,遂与好友胡喜堂(艺名“风情喜”)同入“尖头馆”学戏,艺名秦远驹,终成小有名气的粤剧艺人。他收养的周晓林,改名秦小驹后,更开创粤剧名家唱腔 “月儿腔”。秦小驹受邀赴天津广东音乐会献艺,与中医世家、前清太医之女那尔妏相知相恋,却被战火无情拆散。时光流转,在天津出生的秦小驹曾孙秦朗,身为药学博士,决意踏上归乡之路,回到广州探寻先辈们跨越百年的传奇足迹……
从广州西关到天津胡同,从中药橘红到粤剧“月儿腔”,《橘红》是一部闻得到药香,听得见粤韵的双城记。其中既有粤剧艺术,亦有商帮传奇,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穿插其中,几代人的命运流转展现岭南文化的生生不息,既有地域文化特色,亦具有动人的情感,环环相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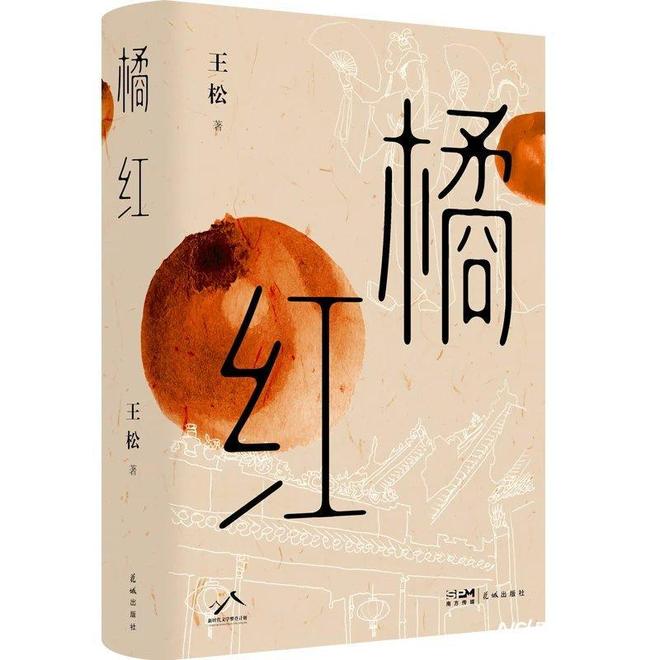
然而,这部充满浓郁“粤味”的作品,却出自一位北方作家之手。为何要挑战如此题材?又如何能打破地域文化的隔阂,令笔下的粤剧、中医、市井生活扎实可感?
新书首发之际,王松接受了南都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分享了《橘红》从构思到落地的完整“诞生记”,揭示了创作背后长达数年的案头准备、十余次深入岭南的田野采风,以及一种将历史“唤醒”为鲜活故事的独特能力。
王松特别指出:“广州市委宣传部领导对小说创作给予了关心与支持。责编陈诗泳不仅寄送了书籍资料,还提供了大量地图,这些地图在创作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国其他出版社没有像花城出版社这样为作者提供如此多帮助的。可以说,这部《橘红》是广州市委宣传部、花城出版社与我共同完成的。”

-访谈-
阅读广州史料感受到“唤醒”力量
南都:你为创作啃下了“两大箱资料”。我们好奇的是,你如何将这些坚硬的史料、地方志信息,转化为小说中流动的“生活质感”与“岭南心气”?能否分享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某条街道从文献记载到小说情节的“诞生记”?
王松:我写作时习惯先查看地图。在写长篇小说《烟火》时,尽管故事发生在天津,我依然要仔细研究地图,以便在脑海中构建出人物活动和故事发展的大致方位。写《橘红》时,我下载并打印了数张大型的广州地图,挂在书房里,每天看。在研究地图时,我会特别关注那些引发我兴趣的地名,比如荔湾湖,它位于西关大屋旁,附近有条名为风水基的小街,后来我到了广州实地寻访这些地方,这样地图上的信息就在我心里“活”了起来。
资料也是这样。我的责编陈诗泳给我寄来了广州西关十三行以及清末民初时期广州的市井生活和传统文化资料。书堆如山,我一开始很茫然。尽管我去过十几次广州,但总是浮光掠影,没时间深入游览,对这座陌生城市的了解有限。于是我思索能否将天津与广州联系起来,建立某种文化上的关联?
很快地,我在阅读这些资料时,感受到一股“唤醒”的力量。比如,我从资料中读到,广东会馆的建立源于广东商帮。当年,康熙年间为鼓励广东商人来天津经商,甚至提供减税优惠。广东人富有冒险精神,借此政策结成商帮,从海上来到天津,生意遍及河北、北京。他们所建的广东会馆,原是广东商会的所在地。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我做过十来年的导演,为了拍摄天津春节晚会,我们常去广东会馆取景。天津的广东会馆古色古香,充满岭南文化风格。当年我以导演身份去,看的都是选景、机器架在哪儿,而这次则完全是从文史角度去考察的。
尽管文献资料都是广州的,但我并未感到陌生,因为广州与天津这两座城市极为相似。它们都是沿海城市,同为早期的通商口岸,都曾经历过殖民统治,且都设有租界,因此在殖民文化方面也存在诸多共通之处。天津有海河,广州有珠江,珠江汇入狮子洋,海河注入渤海。在近代史方面,中国近代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天津紧密相关,同样,广州也是众多历史事件的发源地,例如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便是在广州崛起,黄埔军校亦在此地创办。因此,我认为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的唤醒。
致敬粤剧宗师,主角映射马师曾身世传奇
南都:你选择“旅津广东音乐会”作为连结两座城市的纽带,这个独特的视角是如何捕捉到的?粤剧除了作为情节纽带,在表达文化在异乡的“坚守与流变”这一主题上,有何特殊的象征意义?
王松:天津作为戏曲城市,市民对戏曲情有独钟,我又是天津文史研究馆的馆员,长期研究天津的传统文化,如戏曲、曲艺等。当时,责编陈诗泳发给我一篇关于上世纪20、30年代广东粤剧在天津传播的论文,我发现论文作者正是文史研究馆的一位老先生,年逾八旬,曾是戏曲伴奏,我有机会打电话向他请教。这篇论文在我写作中起到关键作用,以粤剧在天津的交流情况出发,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自初中起,我就很喜欢红线女和广东音乐。那时正值“文革”后期,红线女又是香港归来,被视为资产阶级,我们偷偷跑到同学家里,拉上窗帘,关紧窗户,打开黑胶唱片,红线女的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美妙至极,尽管当时我一句粤语也不懂。后来,我翻阅了一本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画报合订本,其中有一期专门介绍了红线女,让我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写《橘红》时,责编陈诗泳寄来的第二箱书就是关于粤剧和红线女的,其中不乏红线女与马师曾的资料。马师曾是红线女的老师兼爱人,他们的师生恋故事颇具传奇色彩。马师曾的故事令我深感震撼,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艺人的优秀品格——“戏比天大”。他不仅是戏的精灵,擅长表演,还能触类旁通,撰写剧本。我对红线女心怀喜爱,但对马师曾则是高山仰止。我详细研究了马师曾的生平。《橘红》的主角秦小驹,其养父秦远驹,祖父秦厚仪,故事从秦厚仪展开。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撤离西关十三行,使之成为空壳,只剩华人商人。秦家祖籍顺德,到十三行经营药材生意,这段经历就借鉴了马师曾家族的历史。我认为,马家能培养出马师曾这样的人物,必有深层次原因。马师曾历经磨难,甚至被卖到东南亚唱戏,流落他乡。书中秦厚仪身上有马师曾祖父的影子,秦家的身世映射了马家的历史,秦远驹和秦小驹则承载了马师曾的特质。通过反复研究马师曾的家世和生平,我借《橘红》一书向红线女和马师曾致敬。
北方视角的敏锐与敬畏:绝不“食过界”
南都:你曾十余次深入广州采风。这段经历对小说叙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有一个瞬间或场景,重塑了小说的写作计划?
王松:广州有一点我觉得太难得了。随着我对广州的深入了解,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广州对历史遗迹保留得极好。比如,我在小说写了一个历史事件: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八省迅速宣布独立,革命的火焰迅速燃遍全国。然而,唯独广东迟迟未有动静,这让朝廷看到了希望,于是派遣一位大将军前往广州,协助加强城防,巩固大后方。当时,革命者得知这一消息,策划了一场刺杀行动。实际上,这场刺杀是由一人独自完成的,这个人是谁呢?他是黄兴的外甥,年仅十七岁,就承担如此重任。那位朝廷派来的将军,沿着珠江逆流而上,抵达天字码头后弃舟登岸,改乘大轿,经仓前直街,到达接官亭,再从双门底拐入南门,那地方正是如今的北京路。我决心找到这个地方,费尽周折。有一次,冒着大雨,我终于找到了。令我震惊的是,仓前直街这条街道竟然依旧存在,地面上斑驳的石头,明显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磨砺,那些磨损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我在西关一带徘徊,尤其是在永庆坊、恩宁路那一带,每一条小巷、每一条小街我都走过无数次。我不断与地图和资料对照,渐渐地,书房里挂着的地图和书案上的资料都变得立体起来,仿佛在我脑海中活了起来。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写到这个程度,我必须亲自去实地探访。
在修改最后一稿时,我特意再次前往广州。那次我直奔白云山脚下,去看一看濂泉路。我在小说中多次提及白云山,革命者们最终牺牲后都安葬于此,我的几位主要人物去世后也同样长眠于此。因此,我必须亲自前往那个地方实地考察。对我而言,每一次到广州的各个地点,都能让我的地图和资料变得生动立体,这实际上是一个唤醒的过程。写作仅仅依靠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否则岂不是成了闭门造车?
南都:作为一位北方作家,你笔下的岭南文化(粤剧、中医、饮食)不仅没有隔阂感,反而让人感受到岭南文化“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力量。你认为“外来者”视角,在观察和表现岭南文化时,可以带来哪些独特的优势?
王松:我在写作时并未期望广州人读来能有同样的感受,毕竟视角不同,作为北方人,我对岭南文化的理解自然有所差异,但正因如此,我得以跳出固有圈子,对某些广州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保持敏感。当你对某种文化过于熟悉,可能会变得麻木,而我作为外来者,却能捕捉到独特的感受。同时,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出现硬伤。京剧是京剧,河北梆子是河北梆子,粤剧是粤剧,这些绝不能混淆,比如北方人对中医的理解与岭南医药文化存在差异,尤其在广州,药铺的行规极为严格。广东有“食过界”的说法,意指跨行谋利,这在粤剧和中医领域都是大忌。因此,我特意和责编说,初稿完成后务必请戏曲专家、中药专家以及广州市井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专家审阅,挑出毛病,避免硬伤。写广东的作品不必非得由广东人写,但绝不能让人看出作者对广州缺乏了解,那将是失败之作。
南都:小说有大量广州市井生活的扎实细节,在叙事语言的把握上你是如何考量的?
王松:由于我不懂粤语,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相关问题时,我常会致电责编请教,例如小说中的秦小驹发明的“月儿腔”,灵感源自天津街上卖药糖的叫卖声,“药”在粤语中发音类似“月”,故得名。
我并不主张使用方言进行地域书写,我期望最佳的叙事语言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读者能从中辨识出作家是南方人、北方人,抑或是来自天津、广州等地,但在叙事语言上,以普通话为基调,这一点无可置疑,否则难以走向更广大的读者群体,他们将难以理解,不知所云。地域完全可以在作品中进行体现,不必通过语言本身来展示。我是如此实践的,我的叙事语言以普通话为背景,但我的小说语言融合了北方戏曲、曲艺、评书等传统文化元素,呈现出一种较为松弛的市井语言风格。在表现地域特质的关键之处,我力求点到为止,画龙点睛。总体而言,我主张追求一种公共语言的表达方式,我只要保持王松的独特风格即可。
从荔湾湖到越秀山,“广州是一本读不尽的大书”
南都:“橘红”既是药材,也是书名,它似乎隐喻着一种疗愈、温润却坚韧的文化力量。你使用“橘红”作为核心意象和小说标题的原因是什么?
王松:橘红这种药材的颜色,是我为这部小说整体设定的基调。我特别喜欢《帝女花·香夭》这一段,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让自己沉浸在《香夭》这个唱段中,公主和汤世显在洞房里双双殉情,喝了砒霜之后唱出这一段,场景非常凄美。因此,我为小说定的基调就是这种凄美的调子。秦小驹和那尔妏的爱情故事同样充满了凄美。橘红的红并非那种热烈的红,而是一种惨淡的红,一种凋零的红,这种药物本身非常温和,这与小说的整体氛围非常契合。此外,当时的广东商人带着岭南药材来到天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橘红,化州橘红在老天津人中广为人知,都知道对治疗哮喘和咳嗽有很好的效果。
南都:完成《橘红》后,你个人最大的收获或改变是什么?
王松:写作时间历时近一年。提纲历经三稿修订,第一稿5万字,第二稿10万字,第三稿15万字,最终成稿达38万余字。在这一过程中,小说在我心中犹如一株植物悄然生长,这个过程和我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并行不悖,我记忆中总共14次前往广东,每次都带着待解的问题。起初,当我说要写广东时,众人皆不可思议。完成初稿后,有人对我说,接下如此重任实属胆大,而我越写越感到心有戚戚。广州是一本读不尽的大书,广州的底蕴太深厚,并非朝夕之间能洞悉的,一本《橘红》远不足以描绘,更不必说我作为外来者。所幸我对广东文化尚有一定了解,否则更是无从下手。《橘红》的完成为我开启了一扇全新的文化之窗。
南都:如果让你向读者推荐一个与小说有关的广州景点,你会提哪里?
王松:荔湾湖。在我心目中,荔湾湖堪称广州这座城市的一颗璀璨宝石。还有越秀山,我觉得很神奇,在广州这座繁华都市中竟然有这样一座山,闹中取静。广州市民也特别可爱,他们将这座山的自然环境保护得如此之好,如此幽静。这两个地方是我最钟爱的。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