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东道主邀请我们这些昔日学子重返芝大校园,尤其是回到社会思想委员会这个精神家园,加入这项集体任务(la nostra impresa):向这位毕生哲思不辍但终于卸下教鞭的内森·塔科夫教授好好道一声谢。先生待学生,不只是有教无类 ,简直是有求必应——在座的勒纳(Ralph Lerner)教授曾戏称他“不知如何说不”——他总是牺牲个人成就他人,遂使芝大政治哲学卓然于世。如今塔科夫教授告退庠序,恐怕芝大不复从前了。
我们感恩先生教会我们很多事理,其中就包括作为政治哲学范畴的“感恩”。当年我们一起推敲他与在座的林奇(Christopher Lynch)合译的马基雅维利诗篇,其中除了《论野心》(Dell’Ambizione, 1509)、《论机遇》(Dell’ Occasione, 1517后作),也有《论忘恩》(Dell’Ingratitudine, 1507)。现在看来,这三首诗一直是我漂泊华府常备的清醒剂。读一读便明白了:来到华盛顿,矿产协议签不签是一回事,最好穿上西装,多道几声“谢谢”。
乔尔·艾萨克(Joel Isaac)教授布置给我一篇命题作文:回忆追随塔科夫先生读过什么经典,谈谈先生如何影响了我后来的为学。我凛然受命,潜入记忆之海,拾掇出了三簇记忆。其中,以卢梭《埃米尔》开篇,大约最为合宜。毕竟,讲这些是为了礼赞我们共同的“让-雅克”。
关于塔科夫个人的政治立场,学界多有揣度,疑云密布。但我打从一开始便清楚,他是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初次拜会不久,先生竟邀请我这个大一新生加入他的《爱弥儿》研讨班,与三五位社思委的硕学鸿儒们同席论道——这是哲学的民主性。第一次讨论后,他便给我这个青壮劳力指派了任务,钦定我任书记员。彼时,我尚不谙塔氏“会议纪要”(minute-taking)之堂奥,只得搬出宋明大儒门生的看家本领——“大师”但凡吐露了只言片语,我便提笔悉数誊录,唯恐漏却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这大抵是一种“朴素施特劳斯主义”,从波斯、天竺到中土,古来有之。我每次诚惶诚恐地记上五千言,最后无一例外都要被先生勒令删至五百词,这才“传一乡秀才观之”。但我注意到,先生自己却总是逐字批阅我十倍长的“原本”,而且每到下一堂课伊始,他总是花费大约十分钟时间为我的长篇累牍一一指瑕纠谬。我还清楚记得头一回遭他指摘勘误的情形。先生从包里掏出原著和译文,并排铺开,翻至第二章,缓缓抬起头来,以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讲道:
汉松的纪要我读了,颇有可取之处,但也有两处值得商榷。其一,所谓“塔科夫教授见到芝加哥大学校园上的小兔子毛茸茸的,煞是可爱,却惨遭驱逐出校,深感悲悯”——我指的是芝加哥市区敝宅周遭之兔,非芝大校园之兔。第二处更为紧要:之所以谈到兔子,是为了理解卢梭对阿基里斯童年教育的想象。汉松写道:“卢梭提及阿基里斯捉活兔以易苹果,推论此子或为素食主义者”。然而卢梭未尝“提及”此事,只是请人绘了一幅版画嵌入正文而已。

幼年阿基里斯以活兔易苹果(Rousseau, Jean-Jacques.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Amsterdam: J. Néaulme, 1762, 382)
先生批评的是:卢梭原文未载此事,仅以插图描绘喀戎教导阿基里斯的场景。小英雄以兔易果,个中深意,见乎丹青,不废文墨。此事看似琐碎轻浮,但我颇有启悟。其时我尚未与塔科夫先生精读柏拉图,但已然初窥到了影像与观念之间的辩证张力。翌年,他开设了《法律篇》,再隔一年才是《理想国》,因此我们那几届学生是先游“第二城”后访“第一城”。这个次序大抵违背了柏拉图论述的培育卫士之道——卫士们自幼浸润至美之境,眼里容不得沙子(柏拉图《理想国》401d-403c)——但暗合《会饮篇》中第俄提玛的爱育进阶:先观形下之美,再登理典境界(柏拉图《会饮篇》211c)。
但话说回来,《爱弥儿》的哲训,先生与我也未能悉数恪守。塔科夫教授:您髫龄即读普鲁塔克,实在不该!至于在下,未及志学之年,不宜擅习外文。但我若是采纳了卢梭的建议,束发始学,恐亦无缘立雪塔门,更因不通欧陆诸语,无法随您漫步巴黎,遑论那些从地球各个角落像雪片一样飞来堵塞您家信箱的明信片了。说到明信片,在座各位或有不知:《美国心智的闭塞》第六十三页所载那位寄来一纸明信片,称布鲁姆“不是政治哲学教授,实乃旅行社经纪人”的神秘学子正是当年壮游意大利的塔科夫教授(Bloom, Allan.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63)。我与先生亦有这般旅行者和经纪人之谊。他一直勉励我仰观俯察那些孕育了伟大思想的各国风土。以此观之,即便是面对巍巍卢梭,我们也秉持了一些“创造性的异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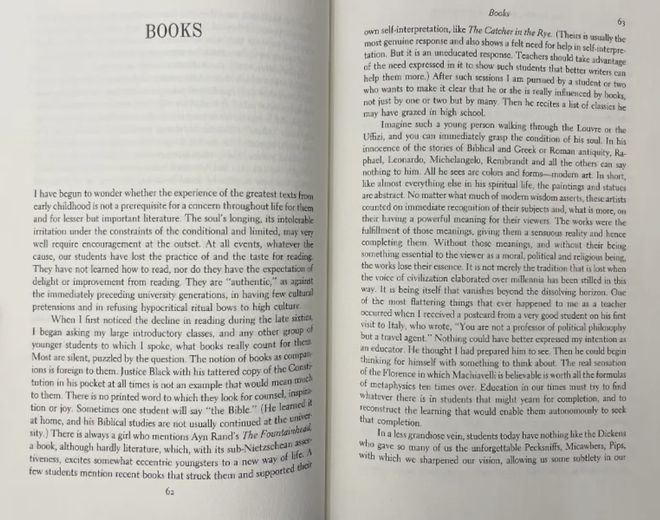
布鲁姆在《美国心智的闭塞》第63页中提及一位康奈尔大学学生从意大利寄回一张明信片,称他不是政治哲学教授,而是旅游中介,此人便是塔科夫。
读罢卢梭,我终于负箧曳屣赴欧游学,在索邦、狄德罗、楠泰尔与法兰西公学之间蹿纵盘桓,适逢先生亦旅法,遂得同游。先生私下相授颇杂:如“法国法定饮酒年龄为六个月”云云,我虽愚钝,也听得出是戏言。当然,我们也共同经历过一件严肃的事情。某夜,我正沿着圣马丁运河大作“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忽闻一阵轰鸣,随之警笛四起,血染街巷,原来是现场遭遇了2015年11月13日的巴黎恐袭。是夜,奥朗德责令四锁边境,事后才知他总统令未下,两名歹徒早已遁逃比利时了,倒是我们这些人困守愁城。事发一小时后,先生致询安危。再过一个小时,他又告诉我两名音乐厅的凶手已然伏诛。我渐渐体力不支,昏昏沉沉睡去。凌晨五时,又被他叫醒:据坊间传闻,有关部门允许部分航班起航了。若非他报讯,我才不会抱着满腹狐疑去戴高乐机场侥幸一试。在那里,我受了一个小时盘问,大费唇舌地解释为何一位留学巴黎的芝加哥大学中国籍学生一定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去米兰后,终于获准登机,飞赴意大利。可见,我们这位“让-雅克”对学生的关怀穿越国界,危难时刻尤见恩情。
从法国回到芝城——曾经的我也像曾经的马克·里拉,视芝加哥为当代之雅典(Lilla, Mark. The Shipwrecked Mind.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16, 45)——我先后投入了先生开设的《法律篇》和《理想国》研讨课。第一年精读《法律篇》时,先生允许我研究了一个 带有个人色彩的选题:雅典客人制定的留学制度。这位立法者只允许三观已经形成的大叔互访留学,而且只能在既定范围内搞学术交流(《法律篇》12.952d-953e)。至于第二年读的《理想国》,我写的论文也带有个人色彩,但更不正经:作为一枚吃货,我聚焦格劳孔的老饕特质,将“嗜食”(φιλόσιτος)与“嗜胜”(φιλονικία)“嗜誉”(φιλοτιμία)“嗜讼”(φιλοδικία)等激情横溢(πλεονεξία)的“血气翻涌”(πρόθυμος或ἐπιθυμία)现象联系起来,熬作一锅粥。我尤其感兴趣亚西比德“痴迷远方的病态之爱”(δυσέρωτας εἶναι τῶν ἀπόντω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13.1)?而这些形形色色的爱又如何回归“爱智慧”(φιλόσοφος)?如何将餍禄之俗欲锻成美德之真金——正如亚西比德投向苏格拉底灵魂深处的惊鸿一瞥(《会饮篇》215a-222a),又如克里提亚斯要剥掉卡尔米德衣衫,而苏格拉底却要剥开他灵魂一般(《卡尔米德篇》154d-e)?那时正值大选,我们经常听到政客对“赢”的渴望——赢,赢,赢,赢上一千年(《理想国》621d),赢到体倦手软,选民们只得央求:暂停胜利吧,让我们喘口气!至于这篇东拉西扯的论文有没有“赢”,这就不好说了。塔科夫教授给我打了高分,但评语却只有批评:“你还是没有说清楚,格劳孔对食色名利的各种爱欲,究竟是哲学家的资格,还是哲学家的失格?”

塔科夫与作者2017年4月29日在芝加哥南迪尔伯恩路343号。
实践起来,总要考虑方向方法,尤其是先后次序的问题。我那时想,先要明白什么是爱,才有望借爱欲之梯以叩哲学之门。这一条思路引导我关注“爱义之辩”,特意在多尼格(Wendy Doniger)教授的指导下研读了《摩奴法典》(मनुस्मृति)《政事论》(अर्थशास्त्र)《爱经》(कामसूत्र)这三部梵典,也促成二位重讲了一次他们曾几何时合授过的这门“西方与印度思想中的爱与法”。在座的罗·卡纳(Ro Khanna)议员:我就是这样开始研究您的祖先的!后来转赴哈佛,又在此基础上将“爱义利”三典的研究拓宽,上溯四部《吠陀》,下承中古注疏,广泛译读古典时期各部史诗。此后我尝试着比较研究中、西、印的正义观念,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当年与这两位恩师的三方会谈。当然,我最着迷的一个问题是爱的跨国维度:爱异邦是否高尚?亚西比德痴恋远方,难道注定是对内颠覆本邦、对外帝国扩张的双重虚妄?
这就涉及了如今的地缘矛盾和全球困境,但因为受到塔科夫教授的影响,我探索国际问题的路径,并不是拿来一个“国际”和“全球”的结构,按其自身机理分析时弊,而是从这些结构产生之前、之初,古人如何想象世界入手,看看不同城邦之间到底还能形成哪些规范性关系。另一个夏天,我与先生精读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我注意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四97章3-4节中,雅典与维奥蒂亚使者互斥对方违背了“希腊共同法”(νόμον τοῖς Ἕλλησιν、τὰ νόμιμα τῶν Ἑλλήνων),各执一词,遑不相让(《伯罗奔尼撒战争史》4.97.3-4.98.3)。我又发现,普拉提亚开城投降之后,反对斯巴达的不公判决,援引的也是“希腊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56.2、3.58.3、3.9.1)。这是希腊共有、共享、共治之法,还是现实主义的修辞把戏,抑或是介乎其中?塔科夫教授说,从未有人系统研究过“希腊法”,鼓励我整理出所有提及这个概念的希腊史料,最后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这便形成了我的毕业论文(之一)。后来,我也怀着这个疑问在《罗摩衍那》中觅得回响——猴王哈奴曼像如今的“积极分子”们一样,高举正义之旗破坏公物,罗波那依据楞伽国法判处极刑,但维毗沙纳却直言进谏,认为全世界的“路迦法”(लोकवृत्त)规定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辩论了几个回合之后,罗波那运用自己的“菩提”(बुद्धिः)理解了国际法,也认同了弟弟的说法:违背了“路迦”的“达摩”也不是好达摩(अधर्मः),可见宇宙秩序尚在,“大物其未可改也”(《罗摩衍那》5.50.5-9)。
反观时下,我们身处一个“不要问美国能为世界做些什么,而是问世界能为美国做些什么”的逆全球化时代:城郭之内,那些被知识经济一弃千里,被希拉里嘲讽为“一箩筐的可悲之人”揭竿而起;城邦之间,旧秩序欲倾,新蓝图未现,倒是中东、东欧硝烟四起。值此危难时刻,我们与同胞紧邻尚且龃龉,又该如何面对相互依赖也相互怀疑的异国他乡?我曾向塔科夫教授请教过一则载于希罗多德《历史》的奇异说辞:雅典外交官表示,若斯巴达不愿结盟修好,我等自可与波斯人“共享理智”(ὁμολογέειν)。鉴于波希对立,互为他者,此中妙趣便值得玩味了(希罗多德《历史》9.7)。当然,希腊人波斯化的例子也是有的,如拉克戴蒙之保萨尼阿斯、雅典之地米斯托克利。而风俗迥异的希腊城邦之间,文化转移也屡见不鲜:独具慧眼的施特劳斯就曾发现,“正如布拉西达乃斯巴达之雅典人,克里昂实为雅典之斯巴达人”(Strauss, Leo. City and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213)。倘若我们从个人上升到邦交的分析层面,也有不少史料可圈可点:起码雅典-萨摩斯盟约曾经明言:城邦之间可以“共同审议”(κοινῆι βολεύεσθαι)——在座高朋之中,那些只知雅典、不涉外事的北美民主理论家们敬请注意了,βολεύεσθαι这个动词大有来头,因为βουλή(议会)可是雅典民主的核心建制(Inscriptiones Graecae, IG II² 1, stoich. 57-61, 405/4 BCE)。
跨境思辨,反求诸己,此等壮阔胸襟,才是最激进的民主精神。于我而言,内森·塔科夫不惟是城墙根下踱方步的老夫子,更是游走在城邦之间的苏格拉底(Socrate mobile)。施特劳斯讲,城邦与哲人之间有一道鸿沟,但我们大可踏出城墙,在城邦之间的裂缝里燃起一盏哲思之灯。
撰文/李汉松
编辑/李永博
校对/贾宁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