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百度APP畅享高清图片
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沉潜二十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钱塘两岸》第一卷近日出版。他以钱塘江大桥为精神镜像,映照民族命运的跌宕起伏,力图史诗性地书写中国历史,完成对现实主义写作的又一次自我攀登。
在柳建伟看来,“时代的蓬勃向上,永远能支撑伟大的文学艺术创造”。前提是,作家要双脚踩在生活的大地,“用直面现实的方法,好好看清这个时代的主潮”。
柳建伟
我的“极端重要的作品”
上观新闻:《钱塘两岸》(卷一)书腰上“沉潜二十年倾力之作”这行字颇令人震撼。不知这“沉潜二十年”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储备和情感积累?
柳建伟:作家写什么样的作品,一是要讲缘由,二是要靠缘分。而且,作家写一般作品、写重要作品、写他认为极端重要的作品,所花费的时间和耗费的精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家写他认为极端重要的作品,往往要谋划准备若干年。毕竟,一个作家一辈子想耗个十年以上写的作品,不多。《钱塘两岸》就是我认为需要用很长时间去完成的“极端重要的作品”。
大约40年前,刚20岁出头的我,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初步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战争史的我,萌发了这辈子要写一部中国版的、长度超过百万字、出场人物超过一百人的小说的念头。这就是《钱塘两岸》最初的创作缘由。
上观新闻:这个念头就像一颗种子,落入了年轻的心田。
柳建伟:我大学读的是工科,知道想做成一件大事是极其艰难的。于是,我开始进行多方面的准备。一是想方设法读了六年文学——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了两年,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读了四年。二是广泛读史,只要是写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书,我都读。光读书还不够,我还尝试用纪实文学的形式,把自己对战争史的理解写出来。通过几部纪实作品的创作,我对部分战争史有了一定“发言权”。
我深知,如果只有以上这些准备,仍然无法写出我想写的战争小说。1995年后,我用了8年时间,一口气写了《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惊涛骇浪》4部长篇小说。这8年间,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长篇战争小说,都是好作品,但和我心里想写的战争小说不一样。
2003年,我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到八一厂后,我就沉下心当起了电影编剧,这一干就是很多年。但我知道,我还是要写战争小说的。
上观新闻:您在等待一个契机?
柳建伟:迟迟没动笔,其实有一个关键原因——对历史了解越多,就越难以确定把小说背景设在哪个地方。中国太大了,各地的抗战区别太大了,我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典型地代表抗战时期真实的中国。
说起来,这就是缘分的奇妙之处。2006年,浙籍导演谢晋找到我,要我担任一部讲述钱塘江大桥传奇历史的电影的编剧。为写这个剧本,在两年多时间里,我去了浙江近20次。不料,电影要筹拍了,谢导突然离世,我和谢导合作的可能再也没有了。
但这么多次的浙江行,让我了解了浙江,发现了浙江在抗战中的独一无二和与众不同。特别是钱塘江大桥从建成到炸毁再到战后修复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抗战史。我突然意识到:一条钱塘江,一座命运奇特的大桥,抗战期间钱塘江南北两岸的沧桑变迁,不正是中国抗战的典型呈现吗?
后来我又发现,只写抗战时期的钱塘两岸是远远不够的。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对整个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把这些历史阶段串联起来,钱塘两岸的故事才能更完整地映照出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新生的历程。
与谢晋导演一次次“相遇”
上观新闻:在这本书的采风、创作过程中,最触动您的是什么?
柳建伟:从决定写,到去年底写下这部小说的第一句话,这么多年,我在钱塘两岸遇到的难忘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这里只说一个人和两件事。
这个人就是导演谢晋。可以说,没有谢导2006年约我写有关钱塘江大桥的电影剧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钱塘两岸》。
谢导辞世5周年之际,我前往他的老家上虞凭吊。在上虞,我看到了一批关于浙东游击纵队的详尽史料。从那时起,我决定为浙江钱塘两岸写一部长篇小说。
后来,在构思小说的重要关节点,我又“遇到”了谢导。前年春天,我去浙江档案馆查资料,因为赶时间走了小门,偶然看到小门边展板上介绍的正是谢导的生平和成就。几天后,我站在上虞曹娥江边,决定把书中最重要的一个家族陈家的老家设定在曹娥江边。之后,小说的构思变得异常顺利。
上观新闻:与谢导的一次次“相遇”,似乎具有某种命运感。
柳建伟:另外还有两件事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整个创作过程。
第一件事是永康之行。我踏访了抗战时浙江省政府金华永康办公处和设在西天目山禅源寺的省政府江北办公处,才知道浙江省政府从1940年开始办了银行贷款给农户,发展战时经济,也才知道周恩来1939年到过禅源寺。从当时浙北地区敌我态势,便知周恩来此行是非常艰辛的,也充分展现了抗战期间浙江军事、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恰恰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
第二件事,是我几次到浙东游击纵队当年控制区域调查踏访。我知道了那时游击区有区域性流通的纸币,知道了那时游击区是要收税的。在上虞,我还参观了当时游击纵队开办的一个纸烟厂的遗址。抗战期间,共产党组织兴办兵工厂等提供战时物资的各种工厂,我在华北八路军根据地知道的不少。但像浙东这种办纸烟厂的,我从来没见过。别看这些事情很小,它们确实能证明当年浙江抗战的独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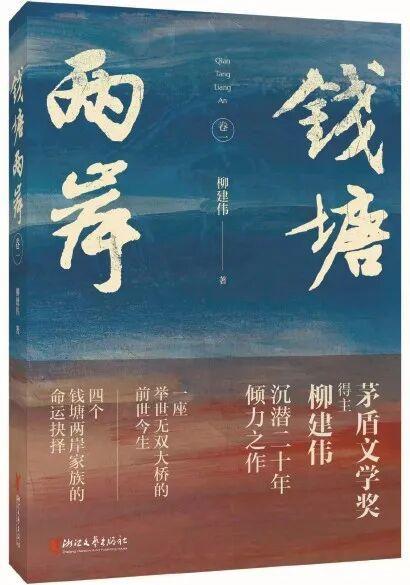
一座大桥的奇特命运
上观新闻:《钱塘两岸》第一卷以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为起点,以钱塘江大桥的修建与炸毁的传奇经历为重点,描摹了钱塘江两岸四个家族面对危局时做出的抉择。钱塘江大桥在小说中意义非凡。
柳建伟:这座大桥可不是一座一般的大桥。钱塘江古称罗刹江,生生把浙江分成了两部分。虽然,这条大江冲刷出了浙江两个富饶的平原,但这条江终究是天堑,到了近代,它就成了浙江进入现代的一种阻隔。在钱塘江上建一座桥,是浙江走进现代的必然需求。
在这座桥动工的1935年,日本已侵华。这就决定了这座桥的命运极为独特。这座桥最“醒目”的命运,就是多次挨炸:没修好,挨日军的空袭轰炸;修好了,为了不资敌,自己又把它炸断;抗战后期,日军把桥修得勉强能通车后,浙东游击纵队又设法炸了三次大桥……1949年杭州解放后,人民政府正式启动修复工程,1953年,大桥才彻底修复。
这18年间,这座大桥的命运事关国运,起起伏伏也就成了必然。这种奇特的命运,在世界桥梁史上也是独一份。
上观新闻:小说人物的命运也与大桥的命运紧密相连。
柳建伟:是的,它是我构思《钱塘两岸》的一个核心意象和主要人物命运变迁的重要依托。
主人公陈剑峰,先是负责带一个连保卫在建大桥和刚建成大桥的安全,后来又在杭州沦陷前一天参与了我方炸断大桥的行动。抗战后期,他参与了浙东游击纵队发起的炸桥行动。杭州解放前夕,他又参加了炸桥和抢桥的两次行动。1955年,陈剑峰被降为连级干部,带领着几十个人,负责钱塘江大桥的外围安全工作。
在这部小说里,大桥的命运和主人公的命运一直是紧密相连的。大桥的命运起起伏伏,最后终于通了,让钱塘江不再是天堑。而主人公陈剑峰的命运像坐过山车一样,转了好多圈,最后又落在了大桥上,和大桥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大桥的命运轨迹,其实也是主人公陈剑峰的命运轨迹。
因为钱塘江大桥在书中起的作用太大,我在这部小说中又设置了直接和大桥有关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主人公陈剑峰的二哥、留美博士、茅以升的助手陈奇峰,另一个是陈奇峰的美国妻子布兰妮。由于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影响,这两位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工作者的命运,也和这座大桥的命运,特别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最后,他俩没能参与钱塘江大桥的最终修复工作,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个“意难平”。
写成一部独特的“风”
上观新闻:在创作中您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关系?
柳建伟:历史真实和小说虚构的世界是有相当紧密的关联的。没有历史真实作为基本支撑,再厉害的作者也虚构不出来反映一个国家某一时代风云变幻的文学作品。这两者在作品中呈现什么样的比例,决定着作品的基本样貌。
以历史真实为主体的小说,应该算是纪实小说。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作家在历史小说方面有过不少成功的尝试,唐浩明、二月河、凌力和黎汝清都写过相当优秀的这类小说。还有一类小说,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在小说中只作为背景加以呈现。《钱塘两岸》属于第二类。在构思的过程中,我也曾考虑过是否让历史真实人物在小说中直接和虚构人物发生关系,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在小说中不让历史真实人物直接出场。
上观新闻:您曾说,“时代三部曲”是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整体性表达。这三部曲分别聚焦县城、省城和军队生活,并以《诗经》为喻,将《北方城郭》比作“风”,将《英雄时代》视为“风与小雅的合体”,将《突出重围》则比作“大雅和颂的合体”。那么,《钱塘两岸》可归入哪个类型?
柳建伟:描写战争时期和社会剧变时期人们生活的小说,完全可按《诗经》的分类来划分出类型。《战争与和平》中的主要虚构人物,生活在中上层的占比很大,可算“风”和“雅”的结合体。《静静的顿河》中主要人物都出自一个河边的村子,应该归为较为纯粹的“风”。二十几年前,中国作家创作了一批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主要背景的长篇小说,像《亮剑》《历史的天空》。这批小说大都写了主人公的一生,时间跨度很长。这批小说的主人公,后来大都有出将入相的人生辉煌阶段。如按“风雅颂”来划分,怕也是“雅”的成分占比多一些。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静静的顿河》这个种类的。因为这样一个偏好,我当然更想把《钱塘两岸》写成一部独特的“风”。这部书中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
柳建伟
对题材的史诗性情有独钟
上观新闻:《钱塘两岸》是否意味着您完成了从“军旅作家”到“社会书记员”的转型?
柳建伟:其实,我早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军旅作家了。把我划入军旅作家的行列,可能是因为我当了45年兵。从我过去创作、出版的小说来看,纯军旅题材的长篇小说只有《突出重围》一部,发表在刊物上的十多部中篇小说中也只有三部算较纯正的军旅题材。所以,我现在写《钱塘两岸》这类小说,不能说是转型,只能说是在题材上开拓了新的领域。
但是,写《钱塘两岸》确实有很多新的感悟和体验。一是从现实题材转向了战争和社会大动荡题材,可展示的生活的广度和可开掘的人性深度完全不同。二是我退休以后写更厚重的长篇小说,心境更散淡了些,这有助于让作品更为纯粹。三是写作时少了一些功利心,可以让作品显得更加从容。
上观新闻:您的作品大都倾向于驾驭宏大的时代主题,可以看出您对“史诗性”叙事结构情有独钟。
柳建伟:中国的文学观念中,“载道”和“言志”一直是主流。曹丕说得更极端些,把文学拔高到了经国大业和不朽盛事的高度。这些传统和主张,塑造了我的基本文学观,奠定了我的文学创作基石。孔子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对此我也是极赞成的。巴尔扎克除了他的“社会书记员”的自我设定对我有影响之外,他讲的“小说是民族秘史”的观点,我也很赞成。
在我看来,中国的古典名著都是“言志”和“载道”的。遍读外国名著后,我又认定西方文学中19世纪的经典长篇要比20世纪的厉害。这样,我开始写长篇小说时,自然而然对题材的史诗性情有独钟了。
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还没有出现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多半还没被长篇小说史诗性地呈现过,那么,作为中国作家的后来者,为什么不去学学19世纪法国、俄国大师的方式方法,认认真真写写中国呢?《钱塘两岸》就是在这种理念和追求的引领下,开始构思创作的。
好好了解新时代吧
上观新闻:2005年,您凭借《英雄时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中国最高文学荣誉对您之后的创作心态和自我要求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柳建伟:获奖的时候,我的工作岗位是电影编剧,所以,这个文学奖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带来影响的是,获奖后我的创作心态变得平静了不少。
上观新闻:您曾说:“作家是一个孤独的职业,剧作家是半孤独半热闹的职业。我更喜欢更孤独一些。”似可理解为您内心更看重文学创作。
柳建伟:1998年,我参与了自己的长篇小说《突出重围》的影视化工作。2001年,我写了第一部后来拍成电影并获了奖的电影剧本《惊涛骇浪》。从这一时期起,我写了二十来个电影剧本,拍成、公映的有十四五个,另外还写了三百多集电视剧剧本,算是一个影视圈里的“老人”了。我担任编剧的影视作品也把影视奖项得了好几遍。可是,从内心来讲,我并不喜欢在中国当影视剧编剧。
前段时间,电视剧《繁花》爆出一些幕后,有心的人已经可以从中看出编剧在电视剧创作生产中地位有多低了。最近,一桩电影编剧状告电影海报不署编剧名字的案子,编剧败诉了。这两件事,让我有些后悔自己在影视圈待了太久。记得当初苏叔阳老先生知道我调到电影厂工作后,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进入了一个名利场,踏进了一块是非地,别太认真,别丢了自己的小说创作。”
上观新闻:作为精通影视创作与纯文学的作家,您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与影视改编之间的关系?
柳建伟:文学已经有几千岁了,电影才130岁,电视剧才90来岁。影视剧剧本是文学和戏剧杂交的产物。文学是母亲,影视剧剧本是儿子,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这应该算是个公理。
影视和文学完全不同,影视是视听的艺术,文学则需要通过眼睛去触摸,用心灵去感知、去重构。所以,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一定会损失一些东西,增加一些东西。如果改编后的影视呈现基本上保障了文学作品的完整性,那么这种改编就算成功了。
上观新闻:在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的过程中,是否有过为了影视效果而牺牲文学性的遗憾?
柳建伟:遗憾当然有很多,不提也罢,提了尽是些辛酸。
近几年,中国的影视水准有所下滑,我认为这与不尊重文学有直接关系。这方面,中国需要好好学学韩国。韩国的影视这些年佳作频出,主要是因为他们非常重视文学这个源头。
上观新闻:作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您认为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文学流派纷繁的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生命力和价值是什么?
柳建伟: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道路的正途。当然,我也十分欣赏其他创作方法,也很乐见文学创作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我以为还远远没有出现高峰。
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未来几十年的中国,都处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漫长进程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时代的蓬勃向上,永远能支撑伟大的文学艺术创造。同时,能完成这种伟大的文学艺术创造的必由之路,必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
爱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亿万人民,正面、全面、多层次研究中国这个时代的变化,努力提升现实主义创作的水平,中国文学艺术的伟大时刻,必能降临。
上观新闻:若用“重围”比喻当下的文学困境,您认为最需要突破的“合围点”是什么?
柳建伟:在当下,文学创作好像被众多无形的墙围在一隅了。这些墙大概有这么几种。一种是作家和现实之间隔着的墙。作家对现实不熟悉,是很可怕的。二是作家的“谜之自信”形成的墙。作家太过自信,也是相当危险的。三是作家长期重技法而轻内容形成的墙。重术而轻道,也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太着急,想走捷径的人越来越多。AI技术突破后,被揭露出来的抄袭丑闻越来越多,这让人痛心。
怎么突出重围,我真的没什么妙计。还是先想办法好好了解新时代吧。用直面现实的方法,好好看清这个时代的主潮,也许能找到突破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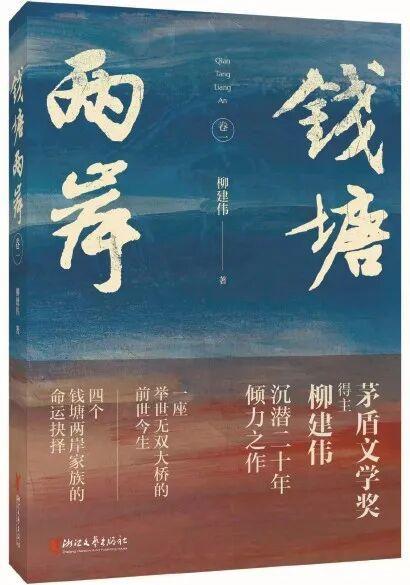
《钱塘两岸》柳建伟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原标题:《柳建伟:作家对现实不熟悉,是很可怕的》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黄玮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