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之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这种话也只有皇帝会说 | 李荣

我家小李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他临睡前我们都会朗声读会儿书,一者助眠,二者大家在睡意朦胧中多少会记得一点所读书的模糊印象,以后与书“再打照面”时能够说一句“倒像在哪里见过”,也就可以了。后来小李长大了,没太多机会全家再凑一起读书了。但这个习惯我们夫妻俩倒保留了下来,如今临睡前依然要读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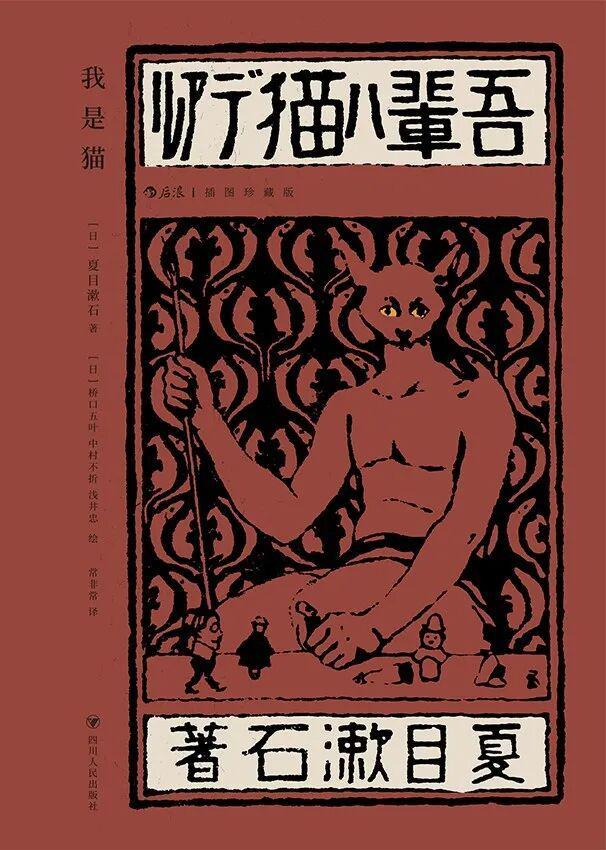
目下手头在读的是夏目漱石有名的小说《我是猫》,到了收尾的第十一章,述及在苦沙弥的家里,他的两位好友独仙和迷亭,边下围棋边闲扯,一位指对手一着棋是死路一条;对手不以为然,横下一条心,非走这一着不可;那一位就给他接上一子儿,随口就吟出了一句唐人的诗句:“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看到这一句,我当然眼熟。两年前我出版了一本自己的集子,取名《南风之薰》,还专门作了一篇序文,其中就引用了这一句。此次读到,如见故人。
《我是猫》的译本在这一句下加了一个译注:语出《旧唐书·柳公权传》。唐文宗夏日与众学士联句作诗。文宗的首联是:“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作:“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一读之下,马上发觉与我当初序文里的引用有出入:一是“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与“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这两句,我序文里都用上了,但分在了两处,因为我以前的阅读里,这两句是从两个来源而来。“薰风自南来,殿角生微凉”,由阅读王船山的文章而来;“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是由方回的《瀛奎律髓·夏日类》中而来,却不知道这两句其实是同时同地“一唱一和”的联句,旧唐书是最初的出处。二是“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之句,旧唐书里是唐文宗之咏,而我的序文因方回《瀛奎律髓》中的“唐太宗之咏也”,带出一句“历史上亦算明君的唐太宗,有时候不恤民情有如此”。
有出入,当然立即细细查究;一查之下,只恨自己读书少。文宗与柳公权的这两句君臣“联句”,其实是历史上广为人知的“熟典”,不知其出处,应该是有点惭愧的。而那个因照抄方回之误而误的“唐太宗之咏”,也早就有人详详细细地指出过,明清的冯舒、查慎行、李光垣等好多位,都曾在评点中特别提到:文宗,原讹作太宗。我的序文曾经在文汇笔会上以《“南风吹来清凉”》为题刊登过。笔会有个好传统,只要它所刊载的文章里有差错或可商榷的地方,便专门辟出“回音壁”的栏目,作为切磋交流的园地。只是一般的回音,都是别人指出作者的错误,这回我却是来“自首”,应该算壁上第一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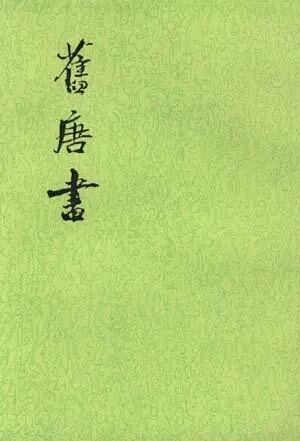
文宗与柳公权的那个“熟典”,出自《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的列传第一百一十五,原文是这样的:
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时丁、袁五学士皆属继,帝独讽公权两句,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于殿壁,字方圆五寸,帝视之,叹曰:“钟、王复生,无以加焉!”
它在历史上有名,是因为大家觉得柳公权在文宗身边,没有像宋玉给楚襄王来上一篇《风赋》那样,让文宗也明白,普通的百姓庶民哪有你这样的条件,觉得炎热的夏天也自有夏天的微凉舒畅。比如东坡,就作过一诗《戏足柳公权联句》,诗前的小引就说到了宋玉:“宋玉对楚王,此独大王之雄风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讥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权小子与文宗联句,有美而无箴,故为足成其篇。”足成的后四句曰:“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意思是同为炎夏,居所不同,苦乐也不同,而且让人感叹的是,不仅苦乐不同,苦乐更是难以相通。所以,如有炎热里的“清阴”,能够“均此施、分四方”就好了。
不过,细细品读旧唐书里的那段文字,也难说柳公权的言下没有“微讽”之意——他特意拈出“殿阁”两字,或许意谓微凉只应“殿阁有”,庶人的茅屋“安得而共之”。只是文宗又是点赞其辞,又是点赞其字,赞不绝口,即便柳公权实有讽谏之意,也早被文宗的赞叹之声转化成一片和和美美的气氛。也有后代文士看出柳公权的言外之意,但还是怪他没有如宋玉对楚王那样“随事纳诲,以启主心,而达下情”。所以东坡的“足句”依然有续成的必要,不作“隐跃含糊之语,冀幸一悟者”。
另外,方回在《瀛奎律髓·夏日类》的卷首小序中,虽然讹文宗为太宗,把唐代皇帝也搞错了,但整个小序的意思,与东坡是一致的:“南风之薰,以解民愠,以阜民财,舜之咏也;人皆畏炎热,我爱夏日长,唐太宗之咏也。所处之时同,而所感之怀不同。故宋玉有雌雄风之对焉。”可怪的是,清朝有名的大学问家、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纪晓岚以及他的大弟子,指出了文宗太宗的讹误,却说此序“殊无谓”。
这个评语加得有点重,我读了觉得很是惊讶,不知如何来评点这么一个“点评”。纪昀是高人,不至于读不懂或读不通方回这么的一小段话。即使纪昀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却也没必要下一个“无谓”的判语,这本身亦甚无谓。纪昀似乎对方回特别没有好感,曾经说:“文人无行,至方虚谷(方回,号虚谷)而极矣,周草窗之所记,不忍卒读之。”周草窗即周密,宋末元初有名的学者、词人,与方回是同时代人。周密的《癸辛杂识》,在《汴梁杂事》篇中有《方回》一则,记录了时人对于方回的“十一可斩”之说。这“十一可斩”的说法,也是由方回的一则丑行而来。当年贾似道当道时,方回“昵于”贾,贾势败,就上书言贾“十可斩”。时人取笑他,贾“十可斩”,你方回“十一可斩”,比贾还多可恨的地方。纪昀由其为人而及于其诗评,大体上没有好印象,认为他的《瀛奎律髓》,“非尽无可取,而骋其私意,率臆成篇,其选诗之弊有三:一曰矫语古淡;一曰标题句眼;一曰好尚生新”。
不过,今人看古人,还是尽量人归人、文归文、诗归诗、选归选、评归评。方回的《瀛奎律髓》能够流传至今,自有他的价值。他选诗的只眼独具,他论诗的高见卓识,都不应该轻易地抹煞。虽然其中也有纪昀所指出的强调枯瘦古淡、雕句琢眼和新奇生硬的弊病,但同时他也知道要修正和补偏,认为“诗先看格高而意又到、语又工为上;意到、语工而格不高次之;无格、无意又无语下矣”,格高易流于粗犷生硬和枯涩,须济以细润圆熟和丰腴。这样的诗评理论应该是比较完整的。
方回这样的人物,在生活行事上庸俗甚至可耻的地方很多,但同时“傲倪自高,不修边幅”,肆意挥洒。写“夏日类”小序那一小段时,不在意“是文宗还是太宗”这样的细小处,完全能够想象。甚至,很有可能是他想传达出“伟大如太宗,尚且如此”的意味,欲抑先扬,潜意识作祟,直把文宗作太宗。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想,更不是我因为“照抄不误”而因错出错的借口。
【南风之薰】是李荣在笔会的专栏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