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作家辽京的生活开始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意外接踵而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一张安稳的书桌,以及写作的稳定节奏。
慢慢地,潜藏在脑海里的深层记忆浮现出来,辽京回忆起一段段成长的往事,她以自己在大家庭成长的经历为基底,一段段地编织出一部名为《白露春分》的长篇小说。
如果说,过去的小说创作往往是“无中生有”,《白露春分》则是从个人经验裁剪出来的。对于辽京来说,书写这部小说最大的难度就是必须不断做出取舍,以及确保虚构的人事依然可以传达自己的感情。
辽京坦陈,这部小说一定有自己家庭的影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家庭的理解在改变,家庭对她的影响也在改变。她说:“也许再过十年,我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再来看这个故事,再来翻腾自己的记忆和经验,我对它们的态度也会变,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是和时间有关系的。”
《白露春分》涉及一个普通北京家庭的三代人生活景况,重点聚焦在奶奶秀梅和两个孙女佳圆和佳月身上。他们各有各的挣扎,也各有各的无奈,尤其让人慨叹的是小说的后半段,秀梅的生命一点点流逝的过程。从议题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说《白露春分》是一部关注“老龄化社会”的作品,但归根到底,辽京关心的始终是个体的人。
她关心的是,一个家庭是如何走到“老无所依,幼无所养”的状态;他们原本可能是一个旺盛的家族,怎么沦落到没有人获得幸福,每一个人都心怀怨恨的地步?
因此,这是一部有勇气的作品,辽京想要了解我们的祖辈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觉得家庭故事与其说是一个题材的目标,不如说是一个触角,或者是一个途径、一个工具,它可以让我们透过上代人去深入历史和时间的深处,让小说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这是2025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作者访谈第二期,对谈嘉宾是入围作品《白露春分》的作者辽京,欢迎持续关注后续更多作家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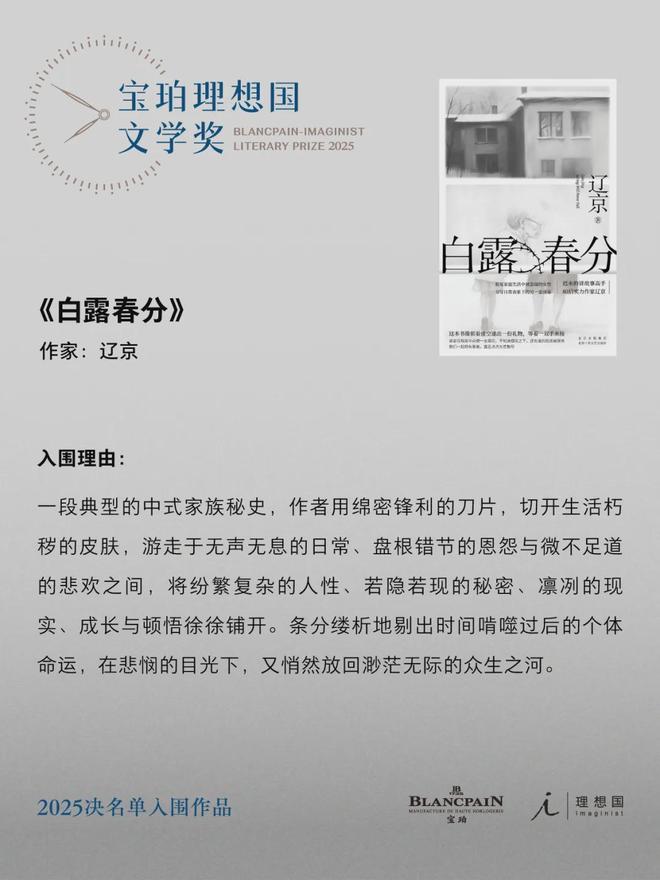
写作者的一种宿命
文学奖: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写作《白露春分》的过程?为什么会想要写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创作中,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辽京:大概是2021年到2022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在疫情期间,有很多事情都不确定,只有写小说这件事情是确定的,可控的,需要的资源也很少,大概只需要桌子、电脑和一些时间,这几样我都有。那段时间我会觉得长篇小说的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压舱石,让我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节奏,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
在开始写《白露春分》之前,我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严格来说,《晚婚》的结构更像一个中篇故事。我不想说这些作品都是练习,或者练笔,它们也是完整的故事,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和生活,但是,从这些写作中得到的一些经验、技巧,以及更重要的勇气,是开始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的必要准备。
坦白来说,这次的写作我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我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我自己也是在一个大家庭成长起来的,我对这样的家庭和其中的人情世故在写作之前是混沌的,但是一旦开始写作,我才发现自己原来认识这么多人,还记得那么多事情。
所以写作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对自身经验的一种挖掘,也是记忆的一种重新显现,同时也帮助我去思考自己当下的生活。如今我也有自己的家庭,也到了中年的年纪,我会开始想问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又该如何去过未来的生活。
在此之前,我写过无中生有的故事,但是《白露春分》是从经验中裁剪出来的,它是一次又一次减法的结果,我得不停地做出取舍,如果说有困难,这大概就是困难——确保它不要变成一部流水账,确保它是一部小说,确保虚构的那些情节和人物,依然能够传达我的真实感受。
可能每个写作者到某个阶段都会想要写长篇小说,都想要去挖掘自己从前的记忆、从前的生活,去重新发现自己记忆中的那些人,这可能是写作者的一种宿命吧。
文学奖:这是你的第二部长篇,和上一部作品《晚婚》相比较,有了一些很大的区别,在这两部长篇小说的间隙,你在做什么?你如何理解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的区别?
辽京:我觉得短篇小说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所以短篇小说的写作不是填补间隙,对我来说,长篇小说反而是个意外,不一定常有,但是短篇小说可以经常写,可以更贴近当下的生活状态。
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宽容,更能容纳那些旁逸斜出的东西,像一场漫长的徒步,当然有个目的地,要朝着它走去,但是在这个旅程中,我们可以东看西看,到处逛逛,走走小路,看看风景,再回到原来的路线上去;短篇小说则像跳水,只有这点时间,这点距离,要完成漂亮的动作,且结尾一定要好,好的结尾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这一点也像跳水。
通常我写短篇不会拖太久,也不喜欢被打断,长篇小说好像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在写《白露春分》的时候,我穿插写了几个短故事,换换脑子,因为《白露春分》的故事其实是有点压抑的,我写的时候,也感觉到这一点,我也需要偶尔抽离一下。
家庭关系并不特殊
文学奖:你的很多作品都聚焦在家庭,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个主题?
辽京:以家庭为主题,或者说写“家庭故事”,有一种特别的便利,即很容易进入过去的时间里。想象一下,写一个职场故事,或者校园故事,通常我们就在当下的时间里,很难从同事或者同学身上看到历史。
但是写一个家庭,很容易就通向过去,通向人们的来处,血缘关系是纵向的,是从时间深处来到我们身边的,无论怎么样深入地了解一个朋友,一个同学,一个同事,都在当下。但是我们一旦开始对自己的长辈发生兴趣,他们是怎么走到现在的,他们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小说的空间就打开了。
他们不是别人,而是另一个时空的我们。有句诗说“至亲至疏夫妻”,其实父母子女也是如此,生来就处在如此亲密的关系里,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反而阻碍了相互之间的了解。
文学奖:《白露春分》其实也是你自己对家庭的回望,里面有一些你早年生活的影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家庭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辽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家庭关系也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并不特殊,一样需要相互理解,缺少诚实和理解的“爱”是很恐怖的,会走向“爱”的反面。
在《白露春分》里,这个家庭表面上的问题是老无所养,这是最突出、最显明的矛盾,但它只是一个结果,至于原因,可以说是人性的、时代的、命运的,都有。任何一个悲剧都不是单独一个原因造成的,最致命的问题并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是生老病死,无力回天,而是当裂缝开始爬行的时候,人们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假装无事发生。自然规律是无法对抗的,但是人总是可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至少面对现实,好好告个别,在这个家庭里,这些都没发生,就像书里写的,他们从来没有过上一种真正的生活,没有真实地对待别人和自己。
文学奖:衰老和死亡,也是你这本小说触及的议题,读起来让人心痛,你是如何想到要用小说去处理养老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进入老龄化的今天,你对这个主题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辽京:我自己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大,见过许多人、许多事,是个人经验和记忆的一部分,不是我要用小说去处理某个社会问题,而是这些人物来找我,有的面目模糊,有的则很鲜明,有的人不在了,有的人则完全变了。时间会改变一切,甚至会改变记忆,我自己也到了中年,对许多往事的理解跟年轻时也不一样了,好像过去的事情也会继续变化,其实不是记忆变了,是我变了,我的视角不同了,我有了新的生活经验,带着这些经验再去处理记忆,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
我如今已经进入中年,有时候写着写着也会很感慨,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过了十年呢?我自己好像一直都过着很平顺的生活,受了教育,找了工作,然后组建了家庭,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想到我认识的许多人,他们没能过上我现在的生活,有的人去世很早,有的人身体不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这些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还没去体验到这个滋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天失去行动能力的,必须面对从衰老到死亡的阶段。
“养老问题”这个说法,带有某种“公共性”,对我来说,还是私人的感情居多,这部小说不是朝向公共议题的写作,哪怕它最终呈现了这个问题,讲的依然是具体的人的故事。如果说小说也有“公共性”,那应该是在读者心里引起的唏嘘共鸣,是情感上而非理智上的。理智上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当代“养老问题”的小说,情感上,我们知道那就是自己家的老人。
作者要相信自己的人物
文学奖:这部小说也是一部女性的成长史,主人公佳圆和佳月是堂姐妹,从小一起长大,但人生轨迹却有一些不同,她们有过疏离,也有彼此的理解,这样的女性关系让人动容,你是怎么理解她俩的这种复杂关系的?
辽京:其实当我塑造一个人物,用她(他)的视角去看、去想、去感受的时候,他们都会有我的影子,就像我自己有许多的分身一样,我觉得人没有办法在写作中完全地抹掉自己的想法。比如佳圆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我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去想,如果我是她,我会如何?我会做得更好吗?我会比她更勇敢,更聪明吗?
我觉得这两个人物,无法代表当代的女性生活,她们不是典型人物,只是在这部小说里,我需要佳圆和佳月成为一组相互对照的人物,有各自的特点,她们不是面对面照镜子,是背靠背,朝向不同的方向。表面上看,佳圆更外向,活泼,有主见,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她总有强烈的内心冲突和挣扎,导致她对外界的关注其实比佳月少;而佳月看起来是较为不起眼的那一个,她的目光反而更多地放在别人身上,她对佳圆的关注比佳圆对她的要更多。我最早用的就是佳月的视角,一开始我写的就是佳月带着奶奶秀梅出去旅游,我也是这样开始引出佳圆的。佳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外界,内心的挣扎和纠结比佳圆要少一点,她将注意力放在奶奶身上,也放在大家庭的其他人身上,她在这个小说里是我观察外部世界的一个视角。
在小说里,两姐妹形成了人物性格上的对比,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比较”,归根到底她们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只是凑巧在一个大家庭里相遇,亲人就像小学生分配同桌那样,是随机的相遇。许多童年时光,她们一起度过,两个人的小家庭都破裂了,父母关系不和,在奶奶这里,她们能找到安宁,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光,虽然也有磕碰与不快,还有奶奶的偏爱横亘其间,依然构成了她们童年回忆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佳圆和佳月的姐妹关系中,温暖是主色调。
文学奖:你又是如何理解奶奶秀梅这个人物的?她身上有很多旧的,令人不悦的东西,你并不讳言将它们展现出来,写作的时候有过犹豫吗?
辽京:塑造一个人物,前提是作者首先要相信他(她)。秀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很难想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人,拥有我们现在常说的“进步”观念,她只是她自己,不是任何观念的集合,她的人生平平淡淡地度过了,没有验证任何真理,除了生死。在她身上,甚至看不到因果的力量,她是一个平凡的人,结局却比平凡更惨。
尽可能地把一个人物写得复杂,关照到性格的各个方面,是长篇小说的应有之义。我没有犹豫过,因为没有要写一个完美形象的预设,小说里的人物无所谓完美,只需要完整,让读者也能相信她是真的,活的,她的存在是符合现实逻辑的,就够了。
文学奖:小说对林慧文、立秋等第二代女性的描写相对较少,但她们的形象依然很鲜明,你是如何理解小说中这个家庭承上启下的第二代女性的?你在这本小说中处理了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中的三代女性的不同景况,这是有意识的吗?
辽京:在小说里,她们是“中年女人”,出场不多,对她们来说,当下的生存更重要,秀梅面对的是养老问题,佳圆和佳月还有漫长的未来,而对立秋等人来说,生活正对她们变得越来越严酷,人到中年,有的选择离婚,有的在市场中浮沉挣扎,没有一个人过得容易,各有各的问题。
我没有意识去处理宏观上的女性问题,她们只是一些散碎的浪花,折射了什么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她们本身是成立的,是出场不多但是依然有形象的,就可以了。
讲好一个故事总归没错
文学奖:你开始写作的时间已经将近20年,但早年主要是在网络上写作,这段经历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些年,你的创作似乎越来越回归到一个传统的文学场域,比如在期刊发表,出版纸质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网络小说和传统小说对你来说有区别吗?
辽京:我大约是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是一个新人栏目,还放了一张我的照片,那个照片现在看起来好年轻啊,是我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写的是一个乡土故事,虽然当时也没有太多的生活经验,我也就写了这一篇小说。后来,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可能,就放下了。直到又过了差不多十年,我才开始在豆瓣阅读发表了一些小说,那个阶段的小说还是以讲故事为主,写了一些近乎悬疑小说的作品。
在豆瓣阅读上发表小说的那段时间,很轻松,也很自由,很有讲故事的乐趣,我始终是一个愿意讲故事的人,不管小说发展到哪个阶段,我觉得讲好一个故事,总归是没错的。
至于发表渠道的变化,一开始是偶然的契机,第一本书得到了不少回应,后面就继续出版,我觉得大致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不管在哪里写,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觉得小说不分传统的和网络的,而是分好看的和不好看的。我不是文学研究者和批评者,缺少更宏观的视角。在我看来,只要是同一个人写的作品,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气息或者质地,而不会因为在不同的媒介上发表而迥然不同。
文学奖:这几年,你的创作很旺盛,接连出版了好几本小说,我很好奇背后支持你持续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辽京:谈不上有什么巨大的动力,我只是还没开始衰竭,衰竭是必然的。目前的生活状态比较稳定,能写就多写写,难免也有偷懒的时候。
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生活中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与其说珍惜,不如说是担忧吧,所以尽量不浪费时间。对于写作,我没有太多的计划,好像也没有期待。也许有一天积攒的话就突然不想说了。在现在这个活跃的状态里,我还是希望尽量不要完全停下来。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由瑞士高级制表品牌宝珀BLANCPAIN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共同发起。公正、权威、专业是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诞生时确立,并将一以贯之的原则。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是华语文学领域首个为发掘和鼓励4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作家,由商业品牌与出版品牌联合创立的奖项。这一奖项的设立,也是为了让大众真正感受到“读书,让时间更有价值”。
2025 年第八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主题为“时间永远分岔”。本届评委团的五位成员黄子平、黎紫书、陆庆屹、施战军、孙甘露,围绕语言、结构、感受力、原创性、完成度等恒定的文学标准,共同提出五部决名单作品:
更多奖项进展,请关注“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网站、宝珀官方账号 (微博:@BLANCPAIN瑞士宝珀腕表,微信公众号:宝珀BLANCPAIN,小红书、抖音:BLANCPAIN宝珀) 、理想国官方账号 (微博:@理想国imaginist,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理想国imaginist,抖音:理想选书) 。欢迎加入新浪微博、小红书、抖音话题#参与讨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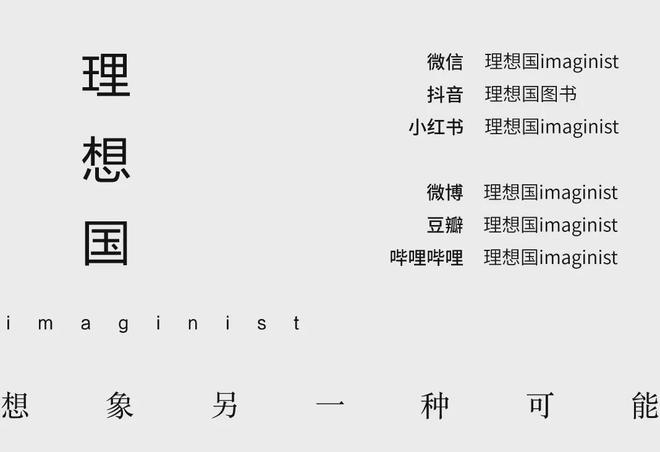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