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或许你可以读一读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是一句很适合最近秋日将近的节候的诗。这首名为《山居秋暝》的唐诗,入选了中学课本,也因其清新空灵的气质、简单流利的语感,留在了我们内心深处,成为基本的文字记忆和情感资源。
而它的作者,王维,写过类似的深入人心又举重若轻的诗很是不少: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这些精妙的诗句,人人熟能成诵,甚至熟悉到不再去思考,这些早早便被我们默默选择并融入身心的诗句到底好在哪里,怎么个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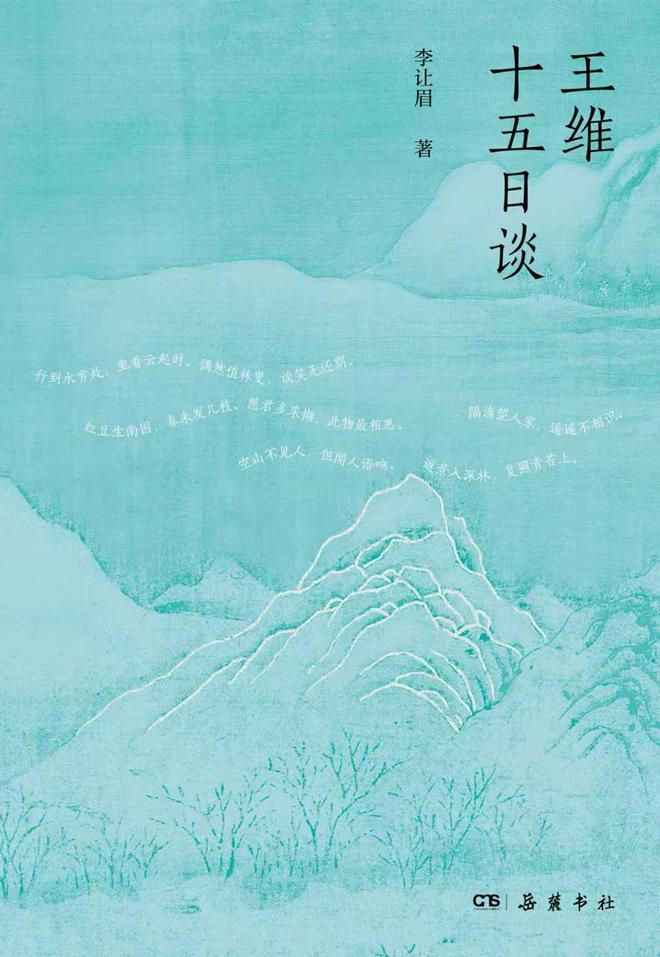
近日,青年诗人、作家李让眉就带着这样的疑惑,开启了一场追寻王维的十五日漫谈,写成这本《王维十五日谈》细解王维的生平、时代、亲交、情感、宗教、音乐、绘画、诗艺,以研究者深厚的学养与诗人独具的灵心,去描摹王维的神影,将世家公子、诗佛、音乐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单薄干枯的标签重新浸入历史的河流中去看见内中的脉络,灵光洞见,俯拾皆是。
在群星熠熠的唐代诗人中,王维是一个并不算特别突出的名字——当然我们也不会忘掉他。不同于李白的豪迈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也相异于杜牧的清健俊爽、李商隐的华美朦胧,王维的诗是一种不容易被贴上鲜明标签的存在。
他出身于五姓七望的世家大族太原王氏,非常符合当下流行的“世家公子”男主人设,又精通书画,弹得一手好琵琶,一身清才卓绝,还精通佛理,更兼“妙年洁白”的姿容,从这种种buff叠满的开局来看,似乎他会顺理成章地拥有一份荣耀光明的前途和美满顺遂的人生,然而他的人生轨迹却是微波而平顺,在不咸不淡的官职上终老一生,既没有李白、杜甫那样大喜大悲的跌宕,也没有高适那样晚年发迹、登上高位的得意。
后世观王维,其人其诗,皆似一颗玲珑温润的明珠,恰到好处地悦目,如同从天而降,无迹可寻。然而,一颗明珠自山中璞玉磨出,所受的斧凿是真实存在过的,宽袍之下遮蔽的始终是累累伤痕。
“读诗的时候我们始终要记得,王维是个擅长自我疗愈的诗人,这同时正意味着他本身很容易受到伤害”,这是李让眉在细读了《王右丞集》、走过了王维的一生之后,在《王维十五日谈》中所写下的感受。
作为家中长子,他九岁时父亲去世,便一身承担起家族的重担,十几岁便孤身前往长安谋求仕进,那首我们熟悉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其实还有一个注脚——“年十七”,所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十七岁的少年已经在繁华却陌生的异乡客居了不止一年,在本该合家团聚的重阳佳节,只能在心里遥念兄弟,但也因明白“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另一端有独属于他的惦念,因此一步都不能退却。
随着让眉将千年之后的焦距不断调近,我们才能发现,少年成名的天才诗人王维在二十岁出头的开元九年(721)进士及第后担任太乐丞,甫一入仕,便在同一年因“黄狮子舞”案坐罪,被贬到了济州做个司仓参军的小官。随后的几十年岁月里,他在贬官、去职、闲居、遇冷等困境中苦苦挣扎,鸭子凫水般保持着淡泊的姿态,也始终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姿态来接纳这种困闷的境遇。
我们读到的那些看似纯出天然、毫无机心的诗句,就来源于这样的人生。如果不能读懂王维的痛苦,也便不能真正理解他的宁静是什么质地,是如何化生。
潇湘晨报记者周诗浩
爆料、维权通道:应用市场下载“晨视频”客户端,搜索“报料”一键直达“晨意帮忙”平台;或拨打热线0731-85571188。政企内容服务专席19176699651。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