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正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史记》的七十列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写先秦诸子的几篇,很明显是就着当时能看到的各家子书来写的,所以《左传》虽有不少诸子故事,《史记》列传却很少引用,徐建委教授称之为“因书立传”。这一现象,结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太史令的事实,引发我们的一点推测,就是不光是先秦诸子的那几篇传,也许七十列传的大部分,都是“因书立传”,只是这其中的“书”,不一定都是后世理解的比较狭隘的已成一部书的“书”,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用文字书写的个人或特定群体的文献,包括之前的家族谱录、个人传记、官员档案等等。
太史令的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但西汉前期的文献收藏现实,是“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所以担任过西汉前期太史令的周史后代司马谈,一定有文献分类整理的经验。司马迁承乃父司马谈的遗愿,“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虽然最后的成果是撰写了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但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对于职掌文献的分类整理意识,一定也会渗透其中。因此,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是否有一种可能,将各类有关个人和群体的历史文献和现实档案,都能较好地安放在合适位置的分类法,在那个时代,就是《史记》的五体,尤其是其中直接涉及人的史料的三体:本纪、世家、列传。表是《史记》的骨架,可能是司马迁最先编写成的。而书,从目前留存的实况看,那是太史公最具雄心的创制——书写人类活动的制度史。
司马迁应该是看到了秦火和楚汉相争等一系列大的严酷的战争对于文献尤其是个人文献的系统性摧毁,才把《史记》130篇里超过一半的篇幅,都给了以写个人和群体为主的列传。具体而言,每一篇列传涉及的内容,背后都有一个、一组或一群的相应文献在支撑着它们。司马迁是用这个方法,使得经过秦火之后非常难得的中国的各类名人史料,得以有一个富于逻辑和历史时间序列的安排。此外,虽然七十列传的数字决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而应该与秦汉时代多以“七十”表示“极限的多”有关,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存在如下的情形,即司马迁当时能看到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个人和特定群体的文本,可能是最多的。
太初元年(前104)颁布《太初历》之前,精通天文学的太史令司马迁曾一度被边缘化。那段时间他应该没有闲着,兼管图书档案,令他把本职工作跟私家著述逐步结合到了一起。分分合合之际,客观上为中国未来的文献学做了虽极为初步却十分重要的开拓工作。可以说,西汉后期的兰台秘府收藏格局,其实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打下基础的;刘向刘歆父子的古典目录学名著《别录》《七略》,追溯上去,恐怕不能说毫无太史公的功劳。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史记》最初恐怕并不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史记》130篇文字与其背后所支撑的文献组群,两者的结合和有序的排次,才是当年的太史公最值得骄傲的名山事业。
那么,《史记》是何时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的呢?
这就要提到人所共知的李陵事件。一方面,司马迁因此下狱受腐刑后,“含粪土之中而不辞”,背负屈辱依然要从事的,应该主要不再是论次金匮石室之书那么表面事务性工作了,追求不朽的名山事业,那样坚毅的目标,此时被一种巨大的激情推到了最前台。另一方面,李陵事件后司马迁被提拔为中书令,职责范围的变化,客观上也使他可以对个人著述有一种更为纯粹的期待。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的那句“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就有了特别的意味。“副在京师”的“副”,表面上是跟“藏之名山”的正本相对的副本,但同时也隐含着另一个层次上的“副”:那个副本,是跟京师太史令职守的档案图书密切关联着的,客观上可以为经过排比的文献组群作提要式的指引。所以反过来,脱离了京师文献指引功能,具有独立意识的“藏之名山”的正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之作。
令人十分惋惜的是,那个“藏之名山”之本,具体的继承者,是闻名后世的司马迁外孙杨恽。一如其外祖的聪慧、耿直,杨恽最后也没有逃脱帝制皇权的魔掌。虽然《史记》在杨恽生前已经“宣布”,基本的架构和大部分内容都流传至今,但随着杨恽的被腰斩,藏之名山的那部《史记》里保留的一些重要篇章(比如《今上本纪》原稿),以及司马迁晚年可能对《史记》所作的增饰,已永远地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夜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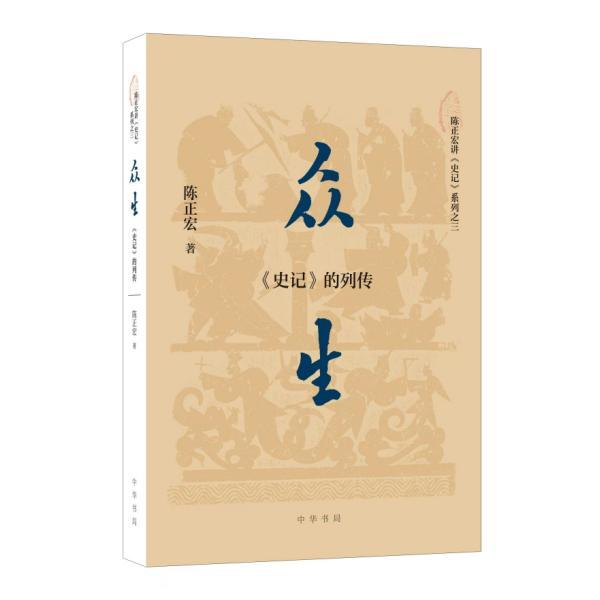
《众生:〈史记〉的列传》,陈正宏 著,中华书局2025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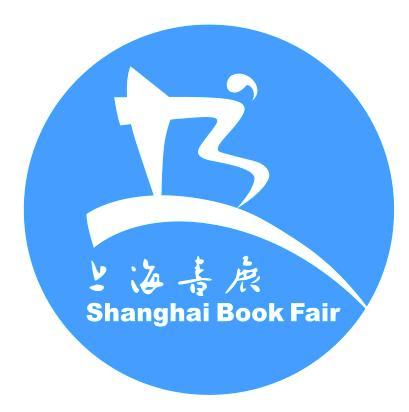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