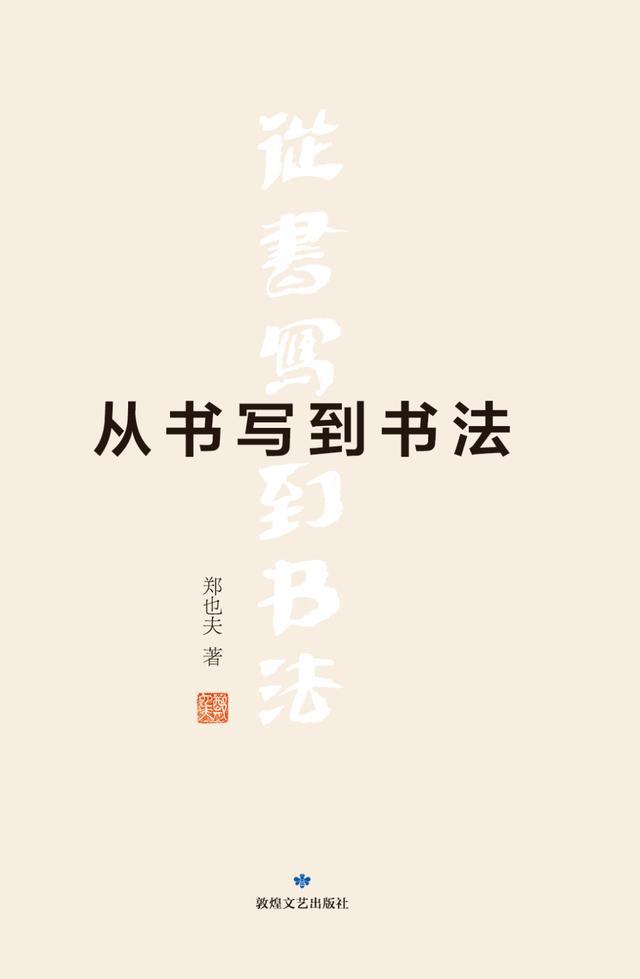
《从书写到书法》,郑也夫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
一,一个书法素人写作此书的动机
“如果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为什么一定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这是钱锺书对一位读过《围城》的美国读者请求见面的回复。”此说让笔者想到庄子的知鱼乐: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与钱层次不同,一个是古代智者认知上的前沿思考,一个是现代作家婉拒粉丝时的抖机灵。但或智慧,或机智,共同点都是逻辑不通。人鱼不可置换,大概率地说,人能知人,人不能知鱼,此物种之异同所使然。书蛋不可置换,鲜有吃了某蛋寻母鸡的人,读了某书想见著者的人却多的是,不荒诞。笔者做央视“东方之子”主持人时采访汪曾祺,问他:“您女儿问您《受戒》这样的作品还能写出来吗,您答不能。敢问为什么不能?”看得出来老爷子不想回答。看着摄像机迟疑片刻才说:《受戒》的情节是虚构的,小和尚的心情却是我的初恋,不会做第二遍。能说了解作者对理解作品是没有意义的吗?有,且在多个维度上。
敝人反钱锺书之道行之。先向读者交代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写这本书?
我是书法素人。2020年元月才开始写毛笔字。之前绝少阅读关于书法的书籍。如此就更要向读者交代其人,其写作动因。
我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领工资的教师,这么说是想表达,我不是典型的社会学家,长期的知识摄取和全部著作,都可见证我是个拒绝画地为牢的杂家。但身为学者当不存疑。从1978年(七七级)进入大学迄今46年,从1982硕士研究生毕业算42年。治学四十余年了。我以为合格的学者一定是研究者。而研究者的特质是好奇心。这既有先天的原因,也是学术训练和长期钻研的结果。作个学者我及格。文史哲三个方面,我比较平衡,智力特质上稍稍偏向哲理,即穷根问底的劲头更足。哲学史的第一章常常讨论哲学的定义。这是寻常人不视为问题,实则难度极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总是以哲学思考的尺子测量和定义其他事物,要定义尺子本身会不知所措。我本来就喜欢这样的思考,又受到如此训练。故一发不止,四十余年来不遗余力地解答着自己赋予自己的大小问题。
学写毛笔字不久开始阅读书法史。字写好了?有余力了?都不是,是要安顿自己的好奇心,是想搞明白自己手里干的是一桩什么样的技艺,它自何时开始,如何演变至今。不读书法史也罢,一读麻烦来了:不满油然而生,质疑一个接一个,几至不吐不快。能写吗?我是书法素人,但这似乎不全是负资产。书法技能上缺少幼功,但在书法史的认知上未被洗脑,没有僵化的成见。虽然也痴迷几个人的书法作品,但古代大师于我并无不可置喙的神圣。我是书法菜鸟,却是社会学、史学的老狐狸,一个不乏斩获的怀疑论者。见到问题不深究,能颠覆成见却不敢写出来,岂不是辜负了一个怀疑论者四十年的功夫。于是下述的一个个观点在批判性的阅读中次第成形。
最早的文字不是甲骨文,不是金文,是毛笔写于竹木上的文字。王国维说:“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笔者更进一步,且整合了更多的论据:甲骨上墨写的字;甲骨文中有“聿”(毛笔)“册”(连缀的竹简);汉字在其一切载体上一以贯之的书写顺序:字从上到下,行从右往左,在世界书写史上独一无二。最后这个论据是笔者独家见解。
秦汉简牍中的主打文字是秦隶、汉隶,从来不是小篆。小篆地位的拔高,是许慎《说文解字》造就的中国书法史上的最大错误。且小篆也不是李斯的发明。李斯书写秦代石刻也属杜撰。
东汉之前只有书写,没有书法。笔者从四个方面为书法定义:目的,被承认,署名,水准。
楷书之祖钟繇的作品是他手下的文吏书写。这不是想当然吗?对此事最有发言权的陈寿、裴松之均不认可钟繇的书法。钟繇书写的证据在哪里?
草书受道教扶乩的启发,很可能王献之亦在其列。
王羲之至尊的书法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李世民。最好的楷书属于唐人。
中国顶级书法家中半数被遗忘。部分作品被后人发现,其中极少数书写者的姓名重见天日,多数湮没无闻。
馆阁体及雕版中“宋体字”的流行是必然的,因为帝国的“文书行政”决定了规范化的书写是大事体,与之相比书法是小游戏。
上述观点辐辏一稿之时,笔者意识到拙作的颠覆性。为什么大多数书法史作者与笔者立场、观点殊为不同,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笔者以为,他们或意识或潜意识地,是带着自赋的使命来的:要拔高书法的地位。拔高不外几个手法。其一,把祖宗追溯得越老越好,这是悠久的尚古传统所使然。说出的越古老越有学问,发掘得越古老越有贡献。如此就极大地混淆了书写与书法。其二,造神。这是人类每一桩浩大活动中都必然发生的事情,是心性使然。没有超级巨星,焉能显示这活动的伟大,不展示这活动的伟大,焉能表现参与者的崇高。其三,赞美。古代书法大师评价优秀作品多是以比拟的手法来赞美。笔者不以为赞美是对待心仪事物的最好方式,比拟必往高走,故引领夸张,一浪高过一浪。“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蔡邕《笔论》)“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蝌蚪;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王羲之《书论》)“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袁昂《古今书评》)古人的比拟式赞美,极大地影响了以康有为首的一大批现代书评家。赞美是赞美者的抒情,背离认知,求真务实的读者不知所云。笔者认同一位古诗词教师的说法。他向学生显示一首诗词之好的方式,就是再三地朗读,让同学们沉浸其中去体会。他还讲述诗人的生平遭遇、写作此诗的场景,唯独不去赞美诗作。能体会其美的同学,在反复朗读中自会感动。鲜有一种美能感动所有人。体会不到的人,听到赞歌就体会到了吗?对一个厌吃某食物的人赞美该食物他就爱吃了?中国书法是伟大的,但没有伟大到造神和赞美者所说的那个程度。从古到今,中国书法从来没有覆盖中国书写人口的三分之一,遑论一半。
笔者是地道书法素人,不带任何使命进入书法史的阅读与写作。比比皆是的数典认祖、造神赞美,刺激敝人反其道行之。反动取向之一是疑古,此呈现于上述观点中。取向之二是认知,认识书写到书法的演变,认识书法所需条件与其演变的一个个环节。
做个真实却未必恰当的比拟。敝人去过无数寺庙,从未烧过一炷香,即使僧人善意劝我。进入书法的殿堂我依旧是不“烧香”的来客,但绝不是拆庙的。我痴迷且执著书法,但造神和赞美远离我的人生哲学。我以为,我找到了更有意义的投身书法的方式。
二、想象在史学研究中的合法性
做事无不带方法者。差异在于,其一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其二说明还是不做说明。颠覆成见,推导史册不曾记载的事情,讲述前人没有说过的道理,最好还是明示自己所持方法。敝人方法有二。其一疑古,对其方法论上的辩护已在拙作《五代九章》(2023)前言中条分缕析,恕不赘述。其二想象,论说如下。
事实、逻辑、想象,是本节讨论中的三大要素。搞清事实是史学的首要工作。逻辑无疑是历史学解析事实的主要方法。“想象”也是要素,且地位并不居于事实与逻辑之下。
历史学应对事实的主要工作,一是判定真伪,二是解决短缺。
因为史书中真伪并存,判定真伪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手法是摆脱孤证,利益不一致的两个人说出同一事实,即为证实。但这常常做不到,于是逻辑派上了用场。即判断一个缺乏第二证据的说法是否合乎逻辑。若合乎逻辑,大致可以认可。比如东汉学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是个孤证。可是笔者以为,它合乎逻辑。《报任安书》2870余字,是连缀250余片的一大捆简书。送到死囚犯任安手中,狱卒焉敢不上报,刘彻焉能不知晓。当年听到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刘彻罚以宫刑;《报任安书》老调重弹,他岂能容忍。从《报任安书》的内容看,司马迁完成了伟业,受够了屈辱,此时唯求死得其所。一个“孤证”加上坚实的逻辑,够了。而单一来源的事实与逻辑不符合时,则较难判定。社会历史中确乎存在不合逻辑的真实行为,因为人类有很多行为是荒诞的、非理性的,特别是昏君。但判断是否合乎逻辑是需要的,毕竟人类的多数行为是功利的、理性的。且不乏一些场合,逻辑在其中的权重竟然比“事实”更大,因为当事人们都在故意弯曲事实,乃至莫衷一是。所以在侦破案情时,犯罪动机备受重视,犯罪动机不是某人的说法,而是逻辑推定。故逻辑常常是怀疑的起点、分析的工具。
事实短缺,是历史学家每每遇到的问题。近现代史尚且如此,何况远古史。怎么办?必须诉诸想象。笔者愿意将这种想象称为“逻辑可能性”。即这想象不是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而是在有限事实和严格逻辑推理之双重约束下的想象。
哲学家和人类学家为人类下过无数定义。其中笔者最欣赏“人类是具有可能性的动物”。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理性能力与想象能力之合一。二者缺一不可。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且施展于方方面面,它在面对事实欠缺的历史时不可能缺席。民间历史从古至今充斥着想象。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希罗多德的著作是考据和想象的合一。他们毫不犹豫地以“逻辑可能性”填补无法获得的事实。现代史学的进步,应该是妥善地处理想象,而不是拒斥。混同史实与想象是前现代的历史学,拒斥想象、拘泥史书则是可怜的现代侏儒。所谓妥善处理,就是分析前充分掌握已有的史实,陈述时说清楚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想象,是逻辑的可能性。
“逻辑的可能性”是被人类广泛实施的智力活动。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刘慈欣的《三体》是 “逻辑的可能性”在科幻上的展开。昆德拉说:小说的价值是探索生活的可能性,探讨人性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可能性。历史学研究中的“逻辑的可能性”与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史实限定之下的“逻辑的可能性”。
拥有历史学想象力的学者,其实对史料上的微观的发现更珍惜和重视。因为他深知史料与想象的关系,深知一个微小的新史料很可能会颠覆或拓宽他此前的想象和推理。
本书讨论的是材料短缺的时代和领域,要极大地诉诸想象。故首先给出对想象的解释和辩护。
来源:郑也夫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