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带着这片土地上100多年的沉重,飞了起来
《本巴》之后,刘亮程在60岁那年完成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长命》。《一个人的村庄》明亮如白昼,《长命》是无边的长夜。
《长命》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家族整个被灭族,只有一个母亲带着五岁的孩子,一路从关内逃难到新疆落户。百年后,又繁衍出今日的一个大家族。
“我们家也有一段兴衰史,我也有黑夜‘见鬼’的恐惧童年,也回老家祭祖,在那里找回幼年丢失的父亲。”正是在这样的生命经验里,《长命》生长出来:一个村庄从“有神”走向“无神”,一个人理解了自己的“浅命”与“长命”。
刘亮程“拽着现实往未发生苦难的那个时间中走”。他还是想用文字把梦与现实连接在一起,让它变成一个梦与醒不分的更辽阔的世界。用他的话说,这些努力最终都不过是为了“更深地理解那个时代,穿过那个时代,放下那个时代”。
近日,在《长命》新书首发分享会上,刘亮程与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长命》责任编辑、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展开对谈,播客“文化有限”主播张超担任主持。从《长命》说起,聊死与生,聊恐惧,也聊我们心中养成的无数的鬼。下文为本次活动的对谈整理。
从《长命》说起:刘亮程写了一个爱情故事?
张超:《长命》是一个关于什么的故事?
刘亮程:我现在想介绍的,《长命》讲的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
张超:很意外。
刘亮程:因为我不想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是关于死和生的。最早我获得它的时候是在七八年前吧,在村里听说有一户人家祖坟被水冲,从棺材中冲出一本家谱来。他们看完家谱才知道,自己的家族在一百多年前被灭族,一个5岁的孩子和母亲逃难出来,一路逃到新疆,又用了130多年的时间繁衍成一个大家族。
这样的故事很重,十年前我可能也很难拿动这样的故事。我生活在新疆村庄,这样的故事遍布村子,每个村庄的许多人家可能都有一部家族兴亡史。这些故事天生就是被用来被遗忘的。家族兴亡的故事太多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是写不完的,这个故事就在内心一直放着。
直到有一天魏姑这个人物出现的时候,这个故事睁开了眼睛。一个作家要从这些必然被遗忘的故事中拯救出一个故事来,让它从历史中走出来,让它从已经消失的或未消失的人群中走出来。魏姑这个人物的出现,让我知道该怎么讲这个故事了。
一百年的岁月中,许多人已经亡故,变成了尘埃,许多人还活着,这个故事本身就分成了能够看得见的人世,和看不见的已经过去的那个祖宗的生活。在我的叙述中这两层人都活着,已经死亡的也在活,死亡也有其生命。所以魏姑的出现让我找到故事的另外一双眼睛,就是可以看见死亡的那双眼睛。当然魏姑这个人物包含了一个漫长的爱情故事,她爱着一个没有身体的人,这具身体早已被水冲走,早已在泥土中化成了尘埃,但是他的魂占据了魏姑的心灵,她要养着他。就像我在心中养一个故事,魏姑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她在心中养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鬼”。
张超:为什么起名叫《长命》?
刘亮程:“长命”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我在这么多年或者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中,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短命,也看到了悠长的人的命和万物的命。我生活在一个全是老人的村庄,那些老人都活得很长久,有些七十多岁,有些八九十岁,也都在院子里面干活,干着干着,从地里面回来提着一把镰刀,刚割完麦子,说回家午休,结果躺在床上就没有起来。有些去给牛羊喂草,把草堆在圈里面,靠在草垛上睡一觉就再也起不来了。对一个人来说可能多长的命都是短的,我没见过有人说自己活得太长了,都是短的,人生总有终结时。
另外,我在村里面的院子,每天看到的都是短命的那些东西,虫子每时每刻都在死,树每年叶子都落,我们家养的鸡活不过一年,狗命会长一些。相对于这些自然界的万千生命,我们人有足够长的命,但是这足够长的命在我们看来又如此之短,再长的命也仅仅是从生到死这样一个生命期限。
那么在此可能就很容易让一个人去思考,我们何以获得一个更长的命?其实这个更长的命,在我们文化中已经被我们的祖先所修成,这就是《长命》中所写的,每个人的短浅的此生都连接着祖先的千秋万代和子孙的万代千秋,我们个体的短命连接着祖先的长命和子孙的长命,我们的命因此而长。这也是《长命》这本书的书名,它的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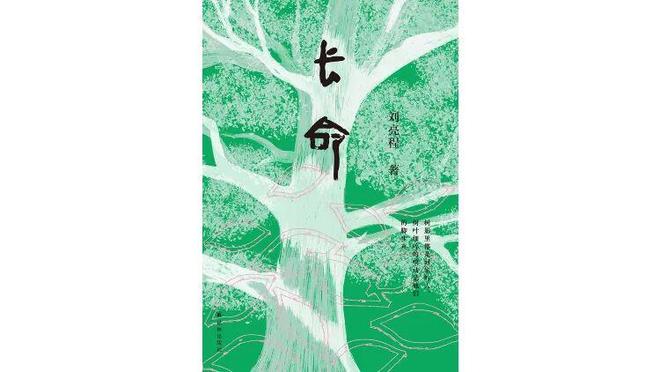
《长命》
作者:刘亮程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25年9月
张超:接下来一个问题想请教王德威教授。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您第一次读到《长命》这部作品,您印象特别深的那个部分是什么?
王德威:在一个很有幸的机会里,我成了先睹为快的读者。这个故事一开始让我着迷的似乎是在一个意外的状态里,主人翁魏姑后来成为一个通灵者,在她的回想中开始展开这个故事。其实作为一个读者,我一开始是有点困惑的。但在这个故事线索的推展里,我逐渐了解到这个故事那种悠长的不同层次的堆叠、交缠。在进行大概到了50页之后,当这个村庄的形象出现了,当我们的主人公长命作为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故事的线索才逐渐合拢。
刘老师刚才介绍这个魏姑和长命,这两位男女主角的邂逅,他们一起去追寻家庭的根脉这样一个艰难的历程里,这个故事就豁然开朗了。所以我觉得作为第一次阅读《长命》的读者,可能在前面50页要稍微耐心一点,它给出了许多谜一样的线索,而这些线索正是一位像是通灵者的小说作者所埋伏下的各种各样的伏笔。一旦你进入那个阅读的状态,这个故事就豁然开朗。
张超:陆老师,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因为我知道刘亮程老师的很多部作品,都是在您这里出版的。您第一次读到刘亮程老师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吸引您和打动您的部分是什么?
陆志宙:那我要回忆一下第一次读刘老师《捎话》时的情景。我记得是2018年6月底的一个傍晚,我收到《捎话》这部稿子,在电脑上打开第一页,几行字就让我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地,时空都变了,更觉得自己是在世界的另一端。这种体验是非常独特的,那个晚上我通宵把《捎话》看了一大半,第二天就跟领导说这本书我们一定要做,就是这样。
张超:从《捎话》到《长命》,有一种连续性,好像又有很多创新在里面。《长命》作为一个故事,这次来到您面前的时候,您有没有哪些惊喜,或者它让您感觉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陆志宙:太大的不一样了。我第一次听刘老师讲他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023年1月,在平遥。当时故事的基本元素都已经有了。2024年10月,我第一次看到了《长命》的文本,故事的开头给我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因为我们都知道,刘老师的小说一般都不会根植在完全的现实里面,时空是架空的。但是《长命》有明确的时间,一开头他就说是1982年,人物有现实中的职业,甚至一开始刘老师还给了一张人物表,非常确凿。而且,刘老师竟然写到了爱情。在刘老师作品里面,当然是有男女之情,但是开篇这样的一个少女之爱是第一次读到,魏姑对逝去的连生一声一声的呼唤,他写得那么温柔。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张超:说到少女心的部分,刘老师发生这个改变是为什么?您作为一个比较年长的男性作家,在写魏姑的时候是怎么贴近她的?
刘亮程:首先魏姑这样的人物我并不陌生,迎生和送生也都需要这样的人物。文学本来就是神鬼共通的,一个作家本来就是能跟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对话的。我在《本巴》这本书中写了哈日王长着一只大人的世故之眼和一个孩子的天真之眼,《本巴》可能是用这两种眼光写下来的。包括刚才志宙提到的《捎话》,其实它的叙述方式跟《长命》也差不多。
张超:用驴的视角。
刘亮程:对,一人一驴在穿过一千年前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在我的设置中,捎话人库只是一个人的世界,但是他所牵的那头毛驴能听到鬼说话,能看到鬼,甚至能看到声音的颜色,一千年前人鬼并存的世界。
到了《长命》这本书的时候,我仍然需要那只眼睛看见我想看见的,就是魏姑的那只眼,所以《长命》就是多了一只眼睛而已。长命看到的是现实的阴影部分,魏姑那只少女之眼看见的更多,看见的更长,所以魏姑可能也是我内心中养育多年的一个少女的形象。她显然已经在往事中,我知道她也已经老了,但是她少女时能看见我所不能看见的世界的那只眼睛还在我的心中,这个人物就出现了。
魏姑是一个文学人物,她也是文学本身。文学就应该是长着一只可以看见这个世界阴影部分的眼睛。我此生或者半生的梦、恐惧,可能都在这个人物中,都被她看见了。
张超: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对分别没有那么恐惧和害怕了。
刘亮程:我写作的时候也内心充满温暖,尤其是我写魏姑看到那些鬼魂的时候,我觉得那些鬼是多么温暖,我们的文化给我们创建了“鬼”这样一种温暖的存在,当我们的生命逐渐冰凉,常有余温,突然地就被接住了,生命又有了另外一种活法。这是我们的文化创造出来的。
中元节,我们看着纸灰一点一点烧完,内心多么的温暖,那一瞬间随着火光在黑夜中一闪一闪,天上也是闪烁的星星,你会觉得跟祖先真的是在一块的,那一刻你就知道那两个世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连接在一起的。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故事与文学的边界
张超:说到文学部分,想请教一下王德威教授,这个活动叫“故事睁开眼睛”,就我浅显的理解,我觉得故事睁开了眼睛,它就是从一个故事走向文学的那个过程。到底故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变成了文学,这个边界在哪里?
王德威:刚才刘老师讲得特别令我感动,他自己就示范了一个最好的说故事的人。我们如果用英文来讲“storyteller”,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者我们用中文是“说书人”的这样一个本色。这是一个古老的技术和一个古老的艺术,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刚才讲到了,我们文明的起源其实是一个说故事的过程,从开天辟地开始,从人类太古洪荒的情境地,怎么让我们生活的周遭能够产生意义,能够相互延传接续我们关心的事物,这个行动其实就是一个说故事的方法或者是一个说故事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故事”,与我们在教科书或是课堂里定义文学的最基本的元素,两者之间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分野的。
我们今天把故事当作一种文学创作的原生材料,或者文学创造起始的元素,我觉得这个分别可能是没有必要的,一个好的动听的故事,它如果能够世世代代一直引着我们不断地想要再听一遍,或者转头来再向其他没有听过故事的人叙说的时候,那个过程里所做的加工,所灌注的感情,所传递的各种相互吸引的这种方式,那就是文学的一个过程。
我们都记得鲁迅的《祝福》中祥林嫂的故事。祥林嫂经过这么多的磨难,当她第一次把她的故事和她的遭遇向村中的各种听者来叙述的时候,我们是感动的,当她反复叙说以后,大家觉得怎么又来了。这个就牵涉我们刚才说的文学和故事之间最微妙的,有时候也是最反讽的连接。祥林嫂的故事永远是真诚的,永远是让我们辛酸而打动我们的一个好的元素或者是材料,但是在讲述的过程里,祥林嫂显然不是一个一流的文学制造者。在这个过程里,可能她的故事遭遇到了一个阻碍。而鲁迅作为一个文学的写作者,他似乎看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又相似但是又相违背的一些艺术上的冲撞,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说故事者,他其实就是一个文学的创造者。而文学在这个地方,也许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界面,它的确能够用更细致的方法,引领我们所谓的情感的表达。
但是最后我想要讲的是,不论文学的创作千变万化,这个故事的本质必须是动人的,必须是真诚的。刘老师在《长命》里面所讲述的故事,其实很复杂的,我们刚才只集中在爱情的部分,其实我可以补充一句,我作为一个阅读文学者或者听故事的人来讲,我觉得魏姑不只是一个情种,她是一个多情的人。这个情当然不只是爱情的情了,她对人生,对世界有纯粹的爱,这是令我感动的部分。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刘老师是一个史诗的讲述者,是一个民间神话的塑造者,又是一个不同群体之间的捎话人。我想在那个层次上,说故事的人所给予我们的,所谓的叙事的公共性或者是情感连接的公共性,不需要太多文学名词或者文学批判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学来再多加解释,故事就是那个最让我们感动的事物的本质。

电影《吉祥如意》剧照。
谈死与生:“我们的文化早就给死亡做了准备”
张超: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刘亮程老师。《长命》讲了人和人关系之间的联系或者家庭脉络之间的传承,但是好像这样的故事在我们今天年轻的语境之下有一些错位,因为今天很多年轻人谈的可能都是原子化的生活。您在写这样一个这么不一样故事的当中,有没有考虑过跟大家离得有一点点远?
刘亮程:一个写作者完全地忠实于自己,对得起自己就足矣。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这部小说离我的生活和我的生命有多远,其实我是信任年轻读者的,我知道他们会长大,他们会从20岁长到30岁,长到50岁,长到跟他们的父亲一样年长。在这样的过程中,那种生命的感觉会不一样,你20岁的生命和50岁的生命完全不一样。
前段时间我给学生讲自然,我说作为一个自然生命,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生命过程到了秋天。我以为自然界的一个秋天到了,其实我的整个生命过程已经到了秋天,我面对最大的自然其实是我的老年,而不是一棵树落叶子了,而不是大地黄了,不是自然界的一个冬天到了。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他的那一块自然,青春,充满活力,有无数的远方。但是我想他们到了60岁,50岁或者40岁的时候,他们就会越来越长得像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没有一个孩子最后长得不像他们的父母,而像了别人,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年长的人,无须担心年轻人会想什么做什么,你只需在老年待着,以一个爷爷的身份,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待着,看着那些跟来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在某一个生命阶段突然不像你了,他们有了另外的生活、另外的想法,对世界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和看法。但是你知道他慢慢会朝你走来。这个完全不用担心,一代又一代人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我也是年轻的时候不认为,后来我跟我的母亲回了一趟老家,才完全颠覆了我的想法。那年我40多岁,陪着我的母亲去甘肃老家。我母亲1961年逃荒到新疆,40年之后才回家,过来时还是20岁的青春少女,回去时已经60多岁,一个老人回到了她的老家,那个老家不是我的,我是在新疆出生的。我以为那个老家跟我没有关系,回到老家的时候先回到叔叔家,叔叔把我们带到四合院中的那个堂屋,德威的老家也有堂屋是吧?
王德威:其实我的父母是东北人,在台湾我们没有亲戚,只有一代。您刚才说的回到老家,我们叫作返乡探亲。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东北,突然说多了一些哥哥,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那一下子一大屋子人令人震撼,突然了解到原来是有另外一个生命联系的脉络,在历史的机缘里面就发生了。

电影《吉祥如意》剧照。
刘亮程:我带着母亲回到那个村子里面也是,那个村子有半村人姓刘,全是我们家的亲戚,一波一波人就过来了。我的父亲叫刘彪,说刘彪的儿子回来了。我就跟着叫,但是叫不过来,全姓刘,叫不过来。你一下子觉得你这个刘姓下面竟然有一群人,半个村庄的人,还有更震撼的是挂在墙上的都是一个又一个牌位,这个都写在《长命》里面去了。
王德威:很令人感动。
刘亮程:我突然觉得我们刘姓人在地上活的一层,墙上挂的还有一层,然后就挨个儿烧香磕头,感觉最震撼的是我叔叔带我们去坟地,那个也写到了《长命》里面。
王德威:是的,我猜想那是您个人的经验,那个特别感动,因为很真实。
刘亮程:对,尤其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的叔叔拉着我的手说亮程你要多来,说你下次来我不在家就在地里。我知道他说的“地里”就是回到祖先中了。这样一说我就知道,我以后是不是也要回到那儿去。如此温暖的归宿,不像天堂那样缥缈,那个地方就在厚土中,在村庄边,老乡不远,坟头和屋顶遥相相望。庄稼扎根的声音,走路的脚步声,时时都会传到那个世界中。
这种感受无时无刻不在。我父亲是我8岁的时候去世的,我一直想写他,一个8岁的孩子肯定是把父亲遗忘的,8岁之前的记忆是模糊的。但是回到老家以后,我突然看到父亲的名字就在家谱中躺着。他死在了新疆,埋在了新疆,但他的名字在家谱中,我看到他那一眼,我就知道我父亲回来了。他在家谱中,他本来就在家谱中活着,所以我回来就开始写《先父》这篇文章。我就开始向他诉说,我知道他活着,我才向他诉说,他有耳朵可以听,他有心灵可以感受,他有眼睛偶尔也会流泪。他会看着一个他8岁就抛下的儿子,长得跟他一样大了,甚至都比他大1岁了,再长下去都比他大了。这样一个儿子还在世间,还在活着,他也没有管过他,8岁就走远,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这个儿子都快长老了,来找到他了。就这样的叙述,就这样的诉说,父亲和儿子叙述、诉说,成就了一篇文章叫《先父》。回了一趟老家,我又找到了父亲,找到童年丢失的父亲,我在我的内心中把他找到了。
王德威:我多加几句话,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个经验,我听了很感动,但是我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去真正感受。其实我们的故事是一个离散的故事,在台湾重新开始一个家族的一个过程。
刘亮程:家里面还有堂屋吗?没有了?
王德威:因为我们的家族原来是闯关东的,山东的背景。今年夏天我才到了山东莱阳,父辈口耳相传是从莱阳迁居到东北。您刚才讲的让我很感动,这样祖祖辈辈家族血脉绵延不绝的深切的感受,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投射。但是东北的情况又不一样,因为它又是一个经过了很多历史的不同事件的地方,所以家族的离散,那个反而是我的一个核心的感受。
张超:您刚才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我的奶奶,我当时我奶奶还健在的时候,她就每天用缝纫机给自己缝寿衣。我当时很年轻,不太理解,我说这好吓人。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了解中,我就觉得你活得好好的,在准备故去的衣服,是不是不吉利,但是她很平和。我当时很不理解。但是读完您这本书的时候,我好像一下子理解了。
刘亮程:我们的文化其实都已经早早就给死亡做了准备,我们现代人就是这种文化的一员。我们的人就如此匆忙,我们见到很多离开这个世界的人都有如此多的不甘、恐惧,他觉得不该这个时候走,他还没有准备好,这是我们的文化早就在给我们准备,你在多大年纪该考虑这个事情了,你得想这个事情,你不想这个事情,人生这趟旅途另外一条路迟早就得开始,那条路是迟早要走的。
我们古人的经历都是这样,他会把以后的事先做好,做得让自己如意,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当你的奶奶在缝她的寿衣的时候,当那些聪明的老人把他自己的寿屋准备好摆到那儿,摆到阴凉处的时候,当他把儿子叫到身边安排后事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和死已经在一起,连为一体了。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多好,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一点不惧。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谈文学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好的世界级作家必须写出复杂度
张超:王老师我接着想问您一个问题,关于文学和我们现实生活对话的问题。您平时也会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文学,也会看东亚文学。去年的时候,我们的邻国韩国女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笔下的故事和当下关联非常紧密。我想请问,像刘亮程老师写的这种非常中国这些文学,如果站在世界文学的谱系来看,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呼应和映照,它和世界文学的对话性存在吗?
王德威:这是一个大话题,但是我也很乐意来回应关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无论是对话或者是交锋关系上的一种个人的看法,或者是一个观察。我觉得第一,东亚的文学或者是任何其他世界地区的文学,在整个文学版图里是所谓打上括号的“那个世界”的一部分,当然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当我们标明说这个是中国文学,我们突出了某一类特色。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好的说故事者,不论是他是来自哪个时代,来自哪个区域或者是文明,总有一些东西是和世界的读者或是听众来分享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刘老师的作品,用我大胆的话来讲,其实是并不那么中国的,我觉得他的确是有某种世界性。刘老师的这个作品所思考的问题,它不必用一个简单的地区或地域的标签来作为唯一识别的方法。刘亮程作为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在中国与世界文学版图上占据一个很特殊的位置。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作品,可能反而赋予中国文学很大很深的一个能量。
刘亮程老师的作品,你可以说他是非常有中国特色,尤其是《长命》这本书。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刘老师的作品对于我来讲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反而恰恰是他不那么中国的那个部分。他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体验,他问了一些特别严肃深邃的问题,什么是生命,以及大的时空状态里面人如何挣扎着求生存,怎么恋爱,怎么死亡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永恒吸引力的,而真正的关键点还是你是不是能够把那个故事说得好,说得动人,这一点是真正竞争的一个场域。
从我个人来看,《捎话》讲西域的故事,讲千年以前的一个故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特别亲切?这个亲切的原因当然是他用了中国的语言,而且用特别优美的甚至有点诗意的、空灵的语言来传达。而他传达的主题却是传达的不可传达性,对沟通的绝望,对声音传达各种的阻挠,居然写了一本这么动人的沟通不可能的小说,我想这里面透露的张力,那种让读者在阅读里面不那么把一个我们所熟知的话题或者一个地域,或者是一个国籍,或者是一个文明,视为当然,那个张力是刘老师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非常特殊的一个能量。在这次获诺奖的韩江的作品,也有这一类的面向。作家必须写出那样的复杂度,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世界级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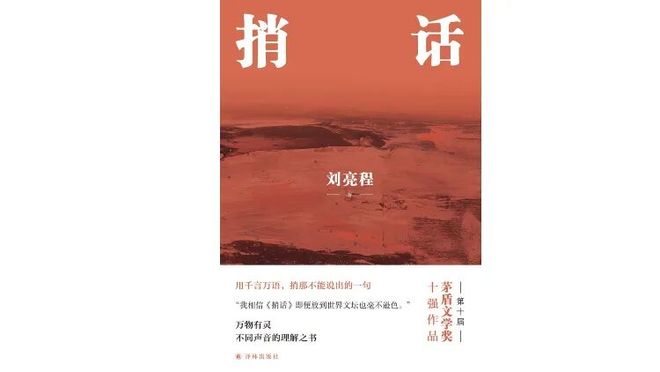
《捎话》
作者:刘亮程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22年4月
陆志宙:刚才王老师也说,我们都是从《捎话》进入刘老师的作品,刘老师关注永恒,关注永恒的时间里面人类最根本的存在和困境,他关注我们古老心灵里面不变的那个东西。刘老师有一本书就叫《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其实可以看到刘老师的目光是向上的,穿越了身边的瞬息万变,他看到的是人类心中最根本的困境。其实我们讲托尔斯泰、讲加缪、卡夫卡,他们表达的也是人类在孤独中怎么选择,在命运关头如何面对,这些根本上是具有世界性,是相通的。但是刘老师的故事,无论是《捎话》、《本巴》,还是现在的《长命》,都是来源于中国的故事,他是从中国的故事里面发展出来的一种世界性。而且刘老师给我的一种印象,虽然他最终是写的人的命运,但是他总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在我们具体人的生老病死中,在我们大地万物的花开花落中,将宏大的命题通过具体的日常的琐事体现出来,在永恒和人间日常之间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谈内心的复杂:30岁谅解的,60岁又回来了
张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刘老师,因为我看到这本《长命》其实有很多非常沉重的、对撞性的故事,比如说郭家的家谱,整个族被灭族的故事,后面还有一个乡村的村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被搬迁或者迁移,被迫被消亡,这些都是很激烈的东西。但是好像在您的篇幅里面,没有展开写,把它略去了,化为了一个非常轻盈的部分。为什么不愿意写这些沉重的故事?
刘亮程:在我的文学作品中我有自己的大与小、轻与重,在《长命》的故事里,我把那些大的、重的社会事件,用文学叙述中让它变小了。就像我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我30岁,我写的是我的童年。《一个人的村庄》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我,大家知道那个时代中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长命》中写的那个兽医被批斗,也是我先父的经历,只是我的先父没有经受住那样的批斗。包括写的铸钟师傅最后死在那个钟里面。
所有残酷的现实其实都发生在身边,甚至发生在我们家中。我觉得我母亲对我这种生活态度或者写作态度影响很大,因为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大哥总是见到仇人就要追打,我们在一个村子里面,迫害我父亲的人还都活着,但是我母亲教导我们说,都是一个时代的事儿,每家都是这样,过去就过去了,你们要好好生活,你们不能再跟仇人的儿子结仇去打。我是一个心中无仇的人,我见到我父亲的仇人,我觉得他跟我没有仇。可能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吧,我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我觉得我把我们家的那些东西都放下了,我父亲不在的那个早晨,我都没去写他,反而写了大地上的虫子怎么生怎么死,写了树叶怎么落下来。我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我已经全然理解或者释然了,我的生活中、我的家庭中所发生的那些苦难,那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是一块土地上的苦难,每家都是那样。
《一个人的村庄》写了比一个家庭更大的万物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我们家去世了一个父亲,树上掉下来一只麻雀,旁边蚂蚁的家庭中可能死了一个爷爷。它就是这样,我30岁的时候就是这样理解世界的,所以《一个人的村庄》是一个万物竞相生长的村庄,自己家庭的苦难和自己生活的社会背景太小了,我那时候确实认为它是小,一场一场的人世间的喧哗,它不会大于风吹动树叶的声音,一个时代不会比一场黄昏落日更盛大。我要用我文学中的“大”去相对减弱这个时代对于一个家庭的重压,我要让我认为的那个“大”顶天立地,我要让大家认为的“大”变成尘埃。这就是写作者的一种权利吧,文学给了写作这一种权利,由它来辨别这个世界什么是大。
我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了许多的黄昏落日,这样的黄昏,太阳一遍遍落下去的时候,每一次落日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没有比它更大的。但是到了《长命》这本书中,其实我原来不想写的那些东西又回来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到了老年之后,他突然开始跟这个世界不谅解了。
张超:30岁的时候谅解,60岁又不想谅解了。
刘亮程:我30岁的时候是如此的释然,我用一声又一声的风声覆盖了那一个又一个的痛。写《长命》时可能我真的老了,人一老就开始计较了。
王德威:刘老师,对不起,我打断您,因为您讲这个我也特别感动,就是这种很细致的生活上的曲折的遭遇。这个和您在前一本《本巴》里的历程是不一样的,会不会因为有《本巴》的那样一个童话式的超然的史诗、大的视野的一种极致之处,您把这个问题又翻个个儿,重新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个世界的另外一面。这个反而让您的这个世界其实更复杂了?
刘亮程:谈到一个人心灵的复杂性,其实我们不了解自己长着一颗怎么样的心灵,因为这颗心灵长成的过程太过复杂。我们有一颗醒来时的心灵和一颗做梦的心灵,这两个心灵就完全不一样,梦中的你跟现实中的你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我一直都在写梦,一直想用文字把梦与现实连接在一起,让它变成一个梦与醒不分的辽阔的世界。我们把梦搁到黑夜中,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小的世界。它必不辽阔,因为它没有梦。一旦我们不承认梦,慢慢我们也只有半条命,因为另外半条命是在梦中度过的。
像德威老师刚刚提的《本巴》。《本巴》其实我写的是语言,《本巴》是被语言托管的一个世界,或者是被语言接管的世界。《本巴》的开端在最后就是东归路上部族面临灭族,那个孩子固执地想用人类幼年童话故事,去接管那个发生在眼前的残酷现实,《本巴》就是这样开始的。那个孩子固执地背靠着喊杀声不断的现实,在创生自己的语言故事,最后三场游戏接管了那个现实。语言当然可以接管,《长命》中有一个片段,其实我写的时候我自己都非常感动,就是出车祸的那一家。一家三口出车祸,死了就死了,他们在世界上已经不再会有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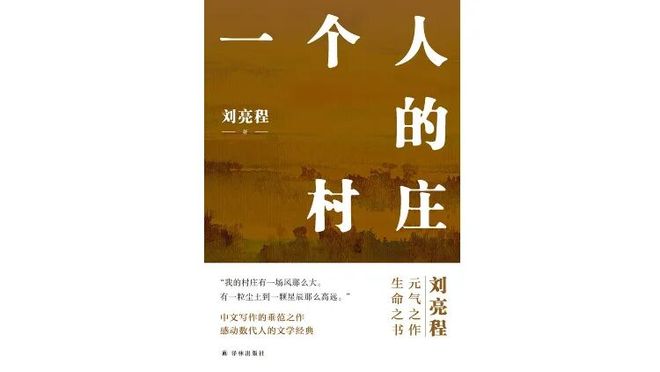
《一个人的村庄》
作者:刘亮程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22年1月
王德威:什么都没有。
刘亮程:但是在文学中的世界还有,一旦文学把他接管过来,文学就要给他续命。在我的故事中,那个女孩因为要父亲在开车的过程中给她讲故事,她的父亲出车祸了,她的魂就老不甘,每天带着她的父亲拉着她的母亲往回走,固执地往回走,她要回到未发生车祸之前的时间。文学也是这样,我觉得我所有的文学都在拽着现实往未发生苦难的那个时间中走,往那个含有完整的早晨的时间中走,我所有的小说中写到的孩子都在8岁之前。
张超:《本巴》的人都不长大。
刘亮程:我还有一个学生叫喻雪玲,她写了我的《年谱》。她写完《年谱》之后,我才发现为什么我的《虚土》中写到那个孩子是5岁,《本巴》中的那个孩子也是几岁,反正没长到8岁。
为什么是这样?我自己是没有清晰认知的,最后直到我看完了我的年谱,看到我父亲去世那一年我8岁的时候,我才知道在我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那些孩子都没有长到8岁,都没有长到父亲要走的那一年。
一个人的潜意识是自己无法完全了解的,你不知道你的生命中埋了什么,因为很大一部分生命记忆埋在你所不知道的童年,童年是被我们所遗忘的。但是你在文学写作的时候,无意识中童年又在操控着你的写作。还有《年谱》中写到我1到8岁期间生活在地窝子中,我几乎把这段生活忘了,也很少去写它。我看《年谱》以后,我发现我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地洞,《虚土》中有地洞,《凿空》中有地洞,整个是挖洞。
我记得我写挖洞的时候,发现我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动物,我太熟悉地下了,挖着挖着突然停下来,耳朵听土里面的动静,那就是我早年的生活。我早年就生活在地窝子中,一个地洞,地上的声音传到地下惊心动魄,还有土里的声音,老鼠打洞的声音,一只老鼠突然打着打着,打到我们家。所以一个作家所有作品都可以在他的童年找到源头,或者说一个作家一辈子都在写他的童年,被他忘掉的童年,他在童年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惊恐,以及看到的亲历的这个世界中他的家人和村人的生与死,都在童年,文学就是在写被我们遗忘的那些东西。
陆志宙:刘老师的《年谱》我也是看得很感动。《年谱》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刘老师的母亲有超强的记忆力,非常细节,把刘老师的1岁、2岁、3岁发生的、差点要沉入遗忘之海的故事,还有那个时代的事情,都还原了出来,也能够让我们明白刘老师的这些文学的底色到底是怎样的。
2023年听刘老师讲《长命》中的故事时,我说刘老师您小时候的那些苦难并没有过去呀,因为刘老师在《一个人的村庄》里,他把所有的苦难都过滤了,是一个少年的明亮,是他把东西都轻轻地放下,给我们呈现的明亮而温暖的世界。但是到了《长命》,刘老师给我们讲铸钟人的遭遇等等。今天听刘老师这么讲,我也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确实是要把那段经历拿出来,要正面地来面对它一次,然后才能放下。
刘亮程:那是属于我们的共同时代,对它释然也好,遗忘也好,以这种方式书写它,都是为了更深地理解那个时代,穿过那个时代,放下那个时代。
“我要写一种飞翔的文字从这个世间惊恐中孤独地飞起来”
张超:说起描写那个时代,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不知道准确不准确,想跟各位老师聊一下。我们书写那个时代,过去一些比较严肃的,或者比较创痛的事件的时候,很多人选择去直面它,把这个痛苦写大,写的颗粒度很细。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沈从文先生或者汪曾祺先生,就会把这些东西处理得很轻。但是我会发现,读者在阅读的审美偏好中,好像很多人都觉得那些重的部分或者写重的人更真实。好像这种写轻的人,我自己感觉价值好像被低估了。
王德威:《长命》的开始是一个相当浪漫的场景,悲哀,但是浪漫。当时我就想,因为刘老师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好,你始终在他那样的一个所谓的明亮的、包容的陈述里,有一个底色其实是阴暗的。这个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即使在看《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也感觉有一些不安,但是这个东西在后来小说的叙事里呈现出来了,因为小说的叙事需要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故事来承载来推进。
回到沈从文的例子,沈从文最优美动人的小说其实是最沉重最悲伤的。我们都记得《边城》的故事,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少女恋爱的故事,这个就对应《长命》也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但是你只要看看《边城》前面两三页,你可以看到有多少所谓时代的苦难,多少这个人世上不由己意的意外的创伤。但是从头到尾,《边城》为什么到今天还是我们在中国文学里面,尤其是青年读者都会觉得好好看,好感动,好浪漫,那个里面所蕴藏的这种悲伤,我觉得可能是沈从文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遗产。
我们怎么去面对生命各种各样的创伤和不圆满,我们有各种的方式,对不对?我们有所谓的涕泪飘零的伤痕,各种各样的姿态,但是也可能经过了刚才刘老师一再强调的,经过一个叙事者、文学人、通灵的媒介,转化成为另外一种仪式性,或者叙事性的,或者只是一个浅浅姿态的表述上,承载着各种各样过去记忆的一种转化。
我觉得轻和重是要看读者怎么样判断自己情感和伦理的位置,而作者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体会到那个点,随便地略过去了,你就觉得这好轻啊。其实你只要在阅读的过程里稍微停顿一下,你可以体会到那个作者在叙事时的那种斟酌,那种拉锯,有的时候是过了一点,有的时候不足,但是那个过程其实反而是最让人感动的。
我觉得后来刘老师写的几本小说里都有这个痕迹,他一直在处理相当黑暗的东西,就是他对生命的看法,他对死亡,他对命运的各种各样的波动,对基本的人类沟通的一种永远的怀疑,转而去承载、去拥抱一个更宽阔自然的世界,或者一个灵异的世界,其实这何尝不是在回应对人生不圆满的创伤的一种写法呢?
我们刚才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但是只要稍微再多看看,连生的名字,其实对应的是两个人,一下子就突然了解到,这个爱情是故事里有故事。所以在那个层次上,我觉得这个小说就让我超过了原始的那个浪漫的预期,你突然感受到它有某一种深得不可言说的内容向度,所以我反而想听听刘老师怎么诠释轻和重。

电影《吉祥如意》剧照。
刘亮程:谢谢德威老师。我年轻的时候经常会做飞的梦,就是梦中看到自己因为恐惧从地上飞了起来,总是被人追赶,追着追着别人就追不上我了,因为我飞起来了。而且我还发现追我的人不会飞,我就非常庆幸这个梦的设置,梦中充满了恐惧,但是最终当厄运真实要降临到头顶的时候,突然获得一种飞的能力,所以在我写我所有文字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写一种飞翔的文字,从这个世间惊恐中孤独地飞起来,把所有一切都扔在地上,所以我说我的文字每一个句子都是头朝上的。
看过我文章的人,看仔细一点会知道,我的句子或者第一句就飞了起来,或者三句之内必有一句是飞起来的。如果句子有句态的话,我所有的句子都是展开了翅膀在天上飞。我希望用我的轻盈的文字带着这块土地的沉重,带着苦难,带着悲伤,也带着幸福,拖尘带土朝着天空去。我不想把沉重的生活写得更加沉重,我不想把苦难写得更苦难,我只想带着它飞。因为只有在我的文字中它们才能获得这样一种飞翔的力量,就像梦中的我从惊恐中飞起来,把那些苦难丢到地上一样。
《虚土》是这样,《捎话》是这样,《本巴》是这样,甚至《长命》这本小说中所写的魏姑也是这样。那个魏姑的叙述就是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一只翅膀,另外一只翅膀在《长命》,他不会飞,整个小说就像扇动着一只翅膀在天空飞翔的鸟。我们知道,一只翅膀是不能飞翔的,但是在文学中,它确实飞了起来。魏姑带着这片土地上100多年的沉重,100多年的死亡飞了起来。所以《长命》是一部生机勃勃的小说。我写了无数的死生,我一般不会在我的文章中用“生死”这个词,我会用“死生”,所有死亡的后面都是生,这是文学能够给予这个世界的。
张超:陆老师,我最后这个问题想问问您。刚才刘老师讲了他的文字都是向上和飞扬的,作为一个编辑,不仅仅负责一个作品的出现,还可能要负责它的销量,更实际的部分。您听到一个作家写一个飞的部分,您会不会担心?
陆志宙:还是像王老师说的,其实还是故事本身是不是足够真诚,足够好看,足够有吸引力,还有给人有不同的层次感。其实我们每个人去体验轻和重都有自己的方式,刘老师的《本巴》是以三个孩子三个游戏这样一种轻盈的方式去讲述,但是它的背后其实是东归这样特别重的一段历史,那么多的战役,那么多的杀戮。但是刘老师是用三个孩子三个游戏去接管了这段很沉重的历史。包括在《长命》里面也是,对魏姑与长命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收敛着写的。你看长命陪着魏姑一路,或者魏姑陪着长命一路回到钟塔县,去寻找祖先。其实魏姑常常会和连生在讲话。但是长命一直在默默地看着她,他也知道她在跟她心中的连生讲话,只是他的目光永远会落在魏姑耳朵后面不被岁月改变的那块白皙的皮肤。
到后面魏姑出狱回来,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我,就是长命给她买了一部手机,把魏姑接回到她自己的老房子,临走前长命把手机交给魏姑,轻轻说了一句——你要找我,电话号码都已经存到手机里面了。其实这时候你就能看到长命是多么的体贴,又是想得多么周到,但是一切都没有说,一个眼神就够了。他们这样的也不能说是爱情,应该是有点亲情和爱情相交织的感情,既有边界感,又相通,一个眼神就能懂。刘老师在处理轻和重之间是非常有他自己原则的。
讲到轻和重,我还要讲到我们对封面的设计也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这本书里面一个中心意象就是钟,钟声在空中连起来一条道路,它迎接着亡灵回家,也连接着我们的思念。但做出来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钟这个形象太重了,我们就想着还是要表现生命,有那么多的死,但是死的间隙还是可以有生的,生可以生机勃勃,可以连接天地,生生不息。最后我们和设计师决定采用生命树的意象,一代又一代的生,最后死也是一种生。
刘亮程:对,这个封面我很喜欢,一个连天接地的生生不息的树,树上好像还有一些眼睛,粉色的眼睛。
陆志宙:对,书的内封也有很多眼睛,就是“故事睁开了眼睛”的那个眼睛。
张超:刚才聊了很多天上的事儿,最后再聊一下非常地上的事儿,先请教王老师,假如今天,现在可能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在波士顿,在哈佛的女孩跑到您面前,说王老师,我应该怀有什么样的预期打开这本书,这本书能给到我什么,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王德威:我可能会问这个学生,你听过《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吗?《一千零一夜》的主人公在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必须讲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必须跟前面讲得不一样,故事讲得不好是没有明天的。这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古老的童话,一个传奇。如果面对一个完全没有当代中国文学阅读背景的学生,我会说,你想看一个中国的,我们当代如何由故事向死而生,延续着我们对生命期待的,一个说故事人的最新的作品吗?那就是《一千零一夜》之后的中国的《长命》的故事。
张超:换一个视角问刘老师。您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外孙女,她现在很小,当她长到20多岁,也许会向她身边的好朋友介绍,说我的外公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但是20年后,那个世界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您期待那时她能从这本书里读到什么?
刘亮程:可能她会聊她自己的恐惧,可能会聊藏在她心中的鬼,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鬼,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有自己共有的鬼,这个鬼叫“中国鬼”,是我们的文化通过千万年的祖先崇拜,而在我们心中养成的无数的鬼。它代表了我们的黑暗,代表了我们的恐惧,代表了我们无尽的思念,代表了我们对此生的不甘和对永生的追求,这就是我们的“鬼”。
我在这本书签手写了一句话“我在心里藏了一个鬼,就是你,我想你时,这个鬼会动”。
这就是我对《长命》这本书的介绍。《长命》没有虚构鬼,《长命》虚构了很多人,但唯独没有虚构鬼,《长命》里面的鬼就是我们的不安,我们的恐惧,我们看不见的黑暗,他们在沙沙作响的树叶中,他们没有身体了我们给他们身体,他们没有耳朵了我们借一只耳朵给他们听,他们没有眼睛了我们还有两只眼睛借一只给他们看,他们没有嘴了我们借他舌头说出。整个《长命》就是我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把自己有的全部借给那些没有的生命,让他们呼吸,让他们说话,让他们活过来,我们在这样的活过来中看到作为一个生命我们的命有多长。
张超:最后的收尾交给陆老师了,陆老师,我知道您作为一个编辑,肯定希望所有人都喜欢这本书,都来读这本书。如果给您一个假想,您可以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一个特别重要的人,您最想把这本书送给谁?您为什么想送给他。
陆志宙:我想接着刘老师的话,这本书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的不安,接住我们所有的害怕。我们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困难的时候,但是《长命》这本书能接住你的困难,能接住你的不安,能接住你的恐惧,能够给你最深的安慰,能给你最好的安顿。
整理/申璐
编辑/刘亚光
校对/刘军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