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论剑|赵德发新作《大海风》:文化交融的精神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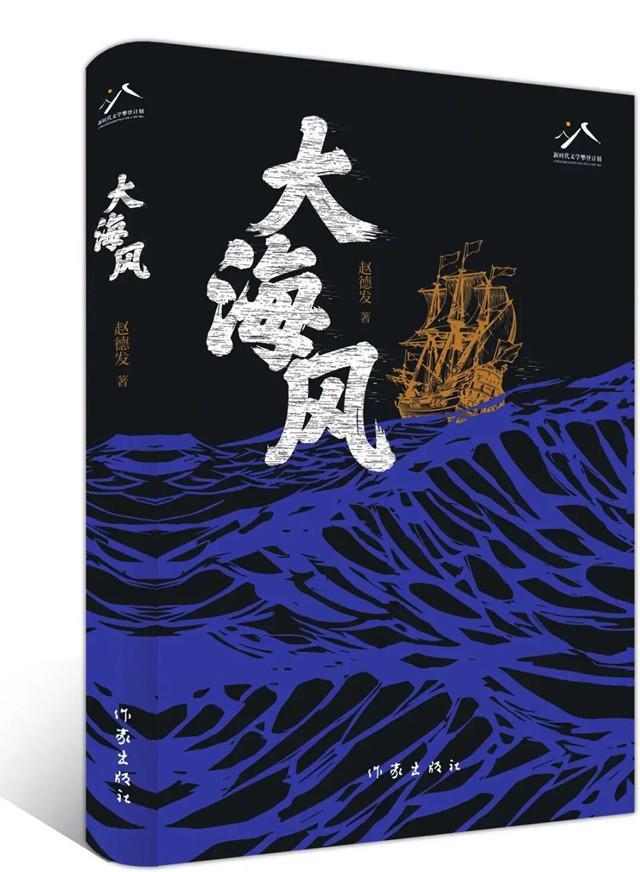
作家赵德发推出的长篇新作《大海风》,以黄海之滨的马蹄所为缩影,通过邢氏三代人的蜕变,展现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小说以"大海风"为意象,勾勒出一幅人海共生、文化交融的精神图景。
人海共生关系的精神镜像
文|王敏
作家赵德发历时四年推出的长篇新作《大海风》,以胶东地区民族航运发展史为叙事支点,选择了“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以“为历史保存细节”的地方志式书写方式,将历史的风云变幻凝聚于地方的小人物、小故事、小世界之中。通过“地方——整体”的辩证关系,铺就一条通往总体性的道路。
大历史的小切口
《大海风》的“地方性”首先体现在对地理空间的具象化书写上。故事以黄海之滨的马蹄所(村)为叙事中心,辐射海暾城、青岛、济南、上海、大连、天津等城市以及广阔的海洋,为读者勾勒出精准的地理坐标,仿佛置身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沿海现场。写到青岛时,中山路、南京路、崂山、小青岛、沙子口、太清宫、明霞洞等真实的地理场景再现,更让人有种阅读地方志的幻觉。
马蹄所就像一个探照风云变幻大历史的小切口。从历史渊源看,它曾是明代海防重镇,是倭寇不敢靠近的“海防铁蹄”;到了近代,却沦为列强争夺的战场,经历着前途莫测的海防危机。这种古今对照的地域书写,使地理空间成为历史变迁的见证者。作者更将虚构的小说故事与真实的历史人物杂糅交织,真实大历史与虚构小故事交融,使宏大叙事扎根于地方肌理和人物命运变迁,最终以地方性来映射并彰显总体性,从而抵达历史本质。
“大海风”既是标题,又在文本中循环复沓,成为贯穿全文的多重意象。最浅层的表意就是人与大海之间既共生又充满张力的美学关系。开篇邢家商船遭遇“大海风”,船老大和风船皆葬身于大海,人在大海中谋生,又在大海中丧生,表达的正是这层意象。“大海风”的第二层表意是“西风东渐”和“东风西渐”的文化交融之风。失去科考机会的邢昭衍、翟良、翟蕙等人,在礼贤书院接受的正是这种中西文化交融共生形成的新风尚的洗礼。
从“小我”到“大我”
《大海风》的家族叙事并非简单的血缘延续和代际传承,而是通过邢泰稔、邢昭衍、邢为海三代人观念的嬗变以及人生选择的差异,勾勒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多元化探索历程,以及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轨迹。
父亲邢泰稔代表着传统海洋文明,本质上是一种沿海的农耕文化。他虽然以风船捕捞和短途运输为业,开商号,送儿子去青岛念洋学,看起来比在家门口打鱼的同辈兄弟更“先进”,但人生主要目标并没有本质区别,仍是攒钱“置地”,本质上还是保守的乡土观念占主导。
主人公邢昭衍则更具“走向深蓝”的开拓进取精神,在时代浪潮的淘洗中不断超越自我,逐渐成长为推动民族航运业发展、探索实业救国道路的时代新人。亲历船毁人亡的海难,九死一生捡回性命的邢昭衍,并没有因此而远离大海,反而不惜分家“卖地”也要造大船、开商号——从父辈“置地”到自己“卖地”,邢昭衍完成了对传统乡土观念的超越。邢昭衍从“无船”到“有船”,是“小我”艰难奋斗的创业史;从风船到轮船的发展壮大,实现的是从个人创业到实业救国的升华;最终“沉船”抗日,预示着他最终走向革命救国的抗战洪流。
家族中最年轻的邢为海,则是坚定走革命道路的践行者。邢氏三代人以“农业立身、实业兴国、革命救国”的人生实践,共同照见了近代中国艰难求索的大历史。
变与不变的新美学
《大海风》将海洋纳入主体叙事,以扎实的在地经验书写人与大海的张力关系,实现了对传统乡土文学的美学超越,开辟了海陆并蓄的美学新境。
这种新美学首先体现为空间与生活的“海陆交融”。小说以广阔的海洋以及胶东港口城市及渔村为故事发生地,空间场景丰富多样,既展现了海洋的辽阔与神秘,又呈现了陆地的繁华与变迁,海陆之间紧密联系又相互影响,形成了海陆并蓄的空间美学。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渔民,也是农民,既耕种土地,也经营渔业,生动呈现了近代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交叉融合的生活图景,一定意义上也是海陆并蓄的生活美学。
更深层的是文化与人格的“海陆共生”。作品中既有细致深描的海洋民俗文化,又有以礼贤书院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同时将传说与历史、现实与虚构多种元素融入其中,充分展现了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马蹄所作为陆地与海洋的交汇点,更是一个复合型的文化空间,既保留着邢泰稔式深度依赖土地的传统乡土精神,又孕育着邢昭衍式勇于开拓冒险的现代海洋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海陆并蓄的文化美学。
邢昭衍则是人格美学的集中体现。他既属于海洋,也属于乡土,他身上有开拓冒险精神,也保留着传统文化中仁义质朴的生命底色,这正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动荡的历史大潮中看似微不足道却能乘风破浪的道义根基。
《大海风》里的女人们
文|慈云祥
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大海风》,既展现了中国海洋企业家邢昭衍的个人成长史,也再现了中国海洋企业发展的兴衰史。成功的人物塑造、严谨的叙事逻辑、生动的故事画面,激荡起20世纪上半叶山东沿海一带的社会和海上风云。
《大海风》既有大格局、大情怀,也接地气,围绕着邢昭衍的事业、亲情和爱情出现的几位女子,在这部书中虽然是配角,却是让这部书更接地气、更有看头的亮笔,也值得一叙。
邢昭衍的母亲吴氏,是一个连自己名字也没有的妇女。书中有这样一段与吴氏有关的介绍:“当年,邢昭衍的父亲(邢泰稔)为了省钱不请女觅汉,母亲(吴氏)白天晒鱼干、干杂活,夜间还要看星星,看香火,恐怕误了做早饭。有一回,她实在困得不行,误了点儿,让父亲(邢泰稔)揍了一顿,后来她就在晴天的夜间坐在院中的树下,把自己的头发拴一根麻绳挂在树杈上,头一耷拉就被麻绳扯醒。早来的伙计见到这个情景,给她起了个诨名‘挂树杈’。这个诨名被人背后叫了多年,直到后来成了‘东家奶奶’,才很少被人提及。”寥寥数语,把那个年代妇女的地位很清楚地摆在了读者眼前。
到了邢昭衍这一辈,他的妻子梭子、妻妹篣子、妹妹石榴,以及翟蕙,在生活中各有各的不同。
梭子和篣子是亲姐妹,都有想主宰自己幸福的意识。但是命运却让她们的感情和生活有了天壤之别。梭子看中了邢昭衍,主动出击圆了自己的爱情梦。篣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爱上了自己的姐夫,情愿做小妾不成,就把命运交付到所爱之人手里。当邢昭衍让她嫁给邢昭光时,她虽然不情愿,依然是嫁了。小说最后,篣子在极度痛苦中回到了老家的破房子里度日。篣子这个人物的塑造,总让我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琳娜》。不同的是,“安娜”的爱情梦想破灭后,用卧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篣子在看似绝路面前,却能直面命运的不公,坚强地活了下来。
邢昭衍的妹妹石榴的言行,是那个年代多数女人的精神写照。她从小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对于越出规则敢于追求自己爱情的女人,本能就有一种敌对情绪。当梭子成了她的嫂子之后,她用语言、用行动对其进行侮辱以表达她的蔑视。直至后来梭子重病缠身,她都没有一点善言善语,表现出了极端不友好。
翟蕙是知识女性,她会外语、懂管理,待人接物礼貌周全,与邢昭衍相识后,成了他事业上的助手、生活中的帮手。这样一个完美女性,命运没有对她网开一面。在作者的笔下,她既熠熠生辉,又朦朦胧胧,多了一层神秘色彩。生动的行为描写和细腻的心理解析,让这个人物鲜活且真实。她爱邢昭衍,她的爱深沉且自尊,和邢昭衍的感情水到渠成,但最终却还是为了自己认同的道德规范,忍痛割舍了那份爱。
说《大海风》中的女人,就不能不说邢昭衍的女儿杏花。杏花本是邢家骄傲的公主,后因爱上了马蹄所的灯塔看守尹戈尔,做出了违反未婚女子规矩的事而命运翻转。她在姨妈篣子的帮助下,雇小船走水路去寻不辞而别的尹戈尔,途中因海水结冰船搁浅,跟随大马古去了大马古家,和他结为夫妻并开始了新的生活。她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文中并没有过多着墨。杏花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邢昭衍沉船返回马蹄所的途中,听到了她的歌声。这一留白,拓宽了作品的外延。
在《大海风》中,这些作为配角的女人们的故事,让整部作品更加灵动,生命力更加鲜活。在有的章节里,还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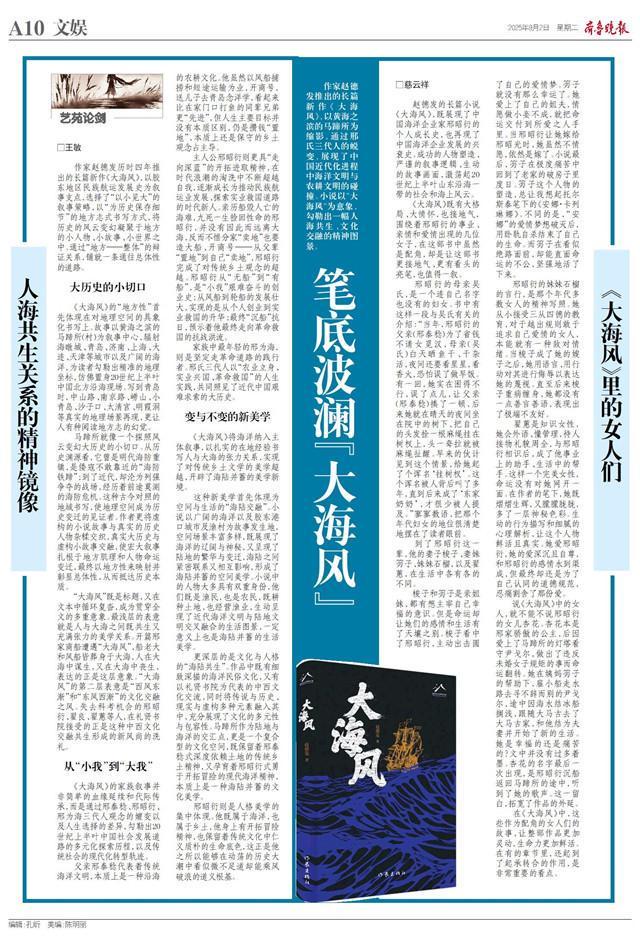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