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拾穗者——读冯秋红纪实散文集《墨海拾珍》
●李风宇
当数字洪流不断冲刷记忆的堤岸,冯秋红的《墨海拾珍》恰似一位执着的拾穗者,在收割后的文化田野上,弯腰捡拾那些被时代快车遗落的精神麦穗。这部跨越二十载的访谈集,以三十余位艺术大家的生命故事为经纬,编织出一幅兼具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的精神图谱。目光掠过目录上那些熟悉的名字——文怀沙、廖静文、高马得、常国武,仿佛能听见文化记忆在书页间沙沙作响。这些名人大家当中有多位是我的师长、好友、老熟人,高马得、陈汝勤夫妇是父执辈,尤记得在高云岭高马得老师家改稿,有缘多次承教于两位老师;曾在北京海淀西苑宾馆与文怀沙老师畅聊文坛旧闻,并蒙老先生指正关于在下写作俞平伯先生的书稿,作为晚辈读书如见故人,感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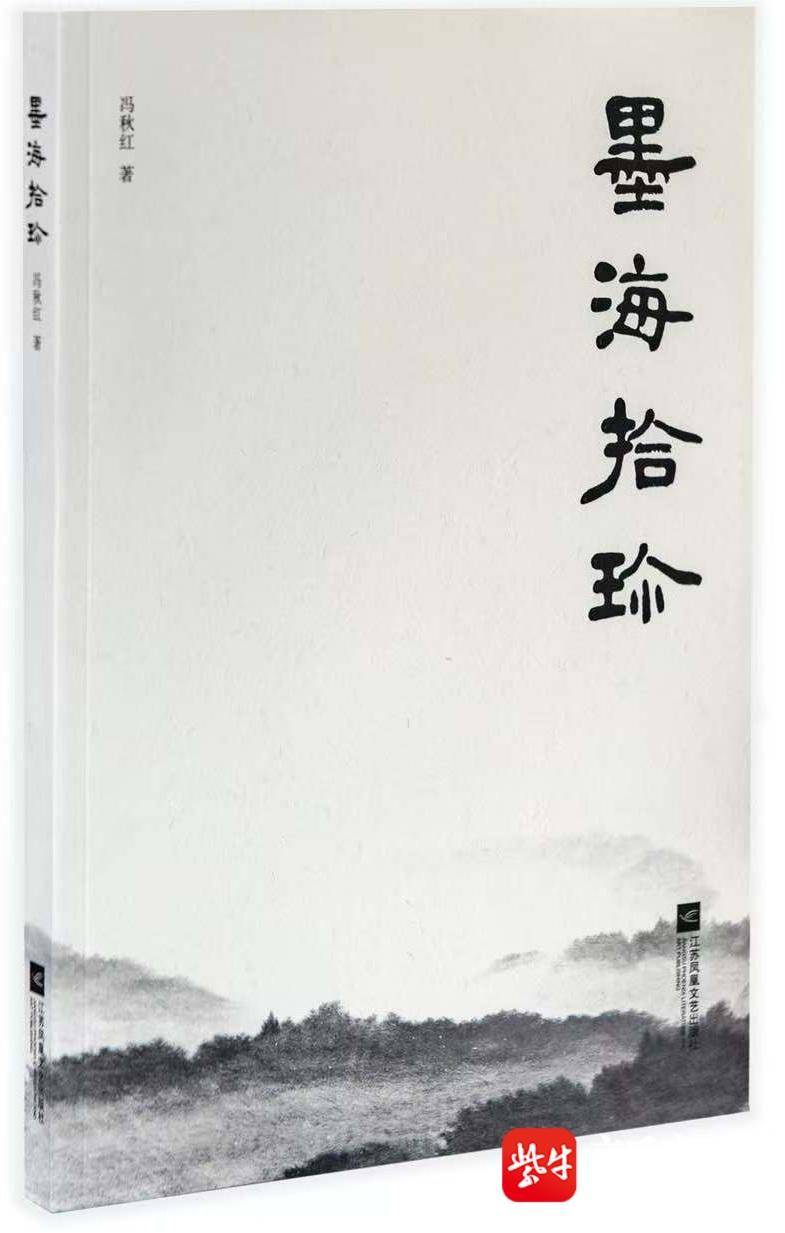
作为资深文化记者,冯秋红始终保有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洞察。她在书中附录的创作谈里强调:“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必须扎根时代的土壤。”这一理念贯穿全书,让这部访谈录超越了简单的史料汇编,成为记录时代精神变迁的文学文本。从文怀沙的傲骨到廖静文的坚韧,从高马得的诙谐到常国武的执着,三十余位艺术家的生命故事构成一幅流动的文化星图;翻阅这些泛黄的记录,宛如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考古。
《墨海拾珍》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逆时序编排的巧思。从2024年的言恭达回溯至世纪初的冯骥才,这种“倒放人生”的叙事策略,构建出独特的时间诗学。就像考古学家清理文化地层,读者在逆向阅读中不断撞见被日常掩埋的精神矿脉,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光泽由此显影。萧平在序言里说此书是“时间倒流”,恰恰点出这种编排对线性时间的反抗:当高马得夫妇的“绘事唱随”与年轻艺术家的创新实验在书页间隔空对话,不同世代的艺术精神便完成了超越时空的共振。 访谈对象的选择本身,就是对文化价值的一次重估。书中既有被冠以“国学大师”的文怀沙,也有自嘲“祥林嫂”的普通艺术家;既有享誉画坛的徐悲鸿遗孀廖静文,也有默默耕耘的版画家程勉。这种不按等级的书写,打破了艺术史叙事的宏大框架,让那些被正统话语遮蔽的微光得以显现。尤其对高马得、陈汝勤夫妇近六十载创作生涯的记录,冯秋红用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细致,捕捉他们从《新华日报》美术编辑到插队宝应,从艺术探索到《连理集》出版的每个关键节点,让个体生命史成为观察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发展的微观窗口。
从记录到文学叙事,突显出作者描写细节的不俗功力。《墨海拾珍》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将新闻访谈淬炼成了文学化的历史叙事。作者不满足于简单记录言语,而是通过场景还原、细节捕捉与心理描摹,搭建出立体的历史现场。作为资深文化记者,她太懂“细节是文学的血肉”——描述常国武先生的书房时,不仅记下书架上的线装书,更留意到砚台里未干的墨汁、窗台上半枯的兰草,这些看似随意的细节,恰恰是老学者生活状态的诗意呈现;写范曾作画,“笔尖在宣纸上行走的声音像春蚕啃食桑叶”;记余光中吟诵,“眼镜片后的目光随着韵脚起伏”,精准地捕捉让平面访谈升华为立体的历史再现。这种文学化处理在触及敏感历史话题时更显珍贵。当一位老作家谈及反右经历,冯秋红没有停留在苦难控诉,而是细腻描摹对方摩挲茶杯的动作:“青花瓷杯沿被磨出细密的纹路,像极了那些无法抹平的岁月伤痕。”意象化的表达既避开了直白叙事的生硬,又给历史记忆注入了更持久的艺术张力。 高马得病榻创作的《乘风破浪20年》的篇章尤其动人。冯秋红敏锐抓住两个细节:老人要求夫人回家取颜料时的坚决,输液时仍反复修改画作的执着。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实则是艺术家用生命最后能量完成的文化仪式。她没有停留在事件表象,而是深挖行为背后的精神逻辑——对高马得而言,为扬子晚报作画不仅是职业习惯,更是将个人艺术生命融入文化传播体系的自觉。这种深入的细节速记,让新闻报道变成了文化记忆的珍贵档案。
冯秋红在访谈中展现的“对话智慧”,重构了交流中的深度。她深知访谈不是简单的问答游戏,而是通过语言搭建的临时性精神共同体。正如巴赫金所说,真正的对话是“众多独立声音的复调”,《墨海拾珍》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 文怀沙怒斥“国学大师”头衔时,冯秋红没有急于追问,而是以沉默的尊重给予表达空间,这种“留白”让访谈对象得以展露思想本真。更难得的是她“在场者的清醒”:当市场化浪潮席卷文坛,她向格非尖锐发问:“当文学成为消费符号,作家是否还需要坚守精神高地?”这个问题不仅指向受访者,更成为对时代的叩问,让访谈录超越了记录功能,成为充满思想锋芒的文化评论。
对高马得夫妇的描写堪称该书“双重叙事”的典范。交替引述两人的回忆,让同一段历史有了两种既不同又互证的视角:高马得眼中的陈汝勤永远是“小丫头”,陈汝勤记忆里的他则从“老夫子”变成“幽默风趣”。多声部叙事消解了单一视角的权威,更在话语缝隙中泄露艺术伴侣的情感密码。当陈汝勤说起两人“同时说出同样一句话”的默契,冯秋红巧妙插入高马的戏画中的心有灵犀,让文字与图像互文,共同诠释艺术婚姻的精神本质。处理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时,她举重若轻:不直接评述历史风云,而是以个体生命片段折射时代光影。常国武在动荡年代坚持治学的背影,版画家程勉三十年专注“南京大屠杀”主题的执着,这些具体而微的叙述避开了概念化表述,让读者在情感共鸣中自行拼凑完整的历史图景——这正是文化记者区别于历史学者的独特视角。
《墨海拾珍》的独特价值,在于模糊了新闻与文学的边界,以新闻写作为记忆载体,创造出“诗性纪实”的文体。冯秋红将新闻的即时性与文学的永恒性熔于一炉,让报纸访谈获得了超越时效的生命力。记录高马得夫妇向香港城市大学捐赠画作时,陈汝勤一句“因为他懂”,经她语境营造,成为诠释艺术家精神追求的经典瞬间——这种将新闻“瞬间”转化为文化“永恒”的能力,源自对语言诗性的深刻把握。书中对艺术创作的描写尤其体现这种诗性:写高马得戏画“用极少笔墨表达生动意境”时,冯秋红的文字也呈现出相似的审美追求——简洁精准的笔触,留白处的丰富意味,甚至句式节奏都与所描述的艺术风格呼应。这种“形式即内容”的自觉,让访谈集超越了信息功能,具备了独立的美学价值。 作为扬子晚报文化记者的长期积累,冯秋红在书中构建了独特的“媒体与记忆的联结”。高马得连续二十年为晚报创作新年贺画的史实,不仅记录了艺术家与媒体的共生,更折射出传统报纸在文化传播中的历史地位。当她细致描写高老每年接受晚报“考试”的趣事,媒体人与艺术家超越功利的精神对话跃然纸上——这种关系在流量至上的今天更显珍贵。
书中还藏着一条温暖的暗线:冯秋红对文学后辈的提携。收录的创作辅导讲座实录,与其说是技巧传授,不如说是文学精神的传承。她反复强调的“细节是文学的血肉”,在访谈实践中得到完美印证,那些精准的细节捕捉本身就是最好的示范。作为江苏艺术评论学会常务理事,她始终搭建学术与大众的桥梁:既深入探讨“新金陵画派”的技法创新,又用“书法如舞者,中锋是立身之本”的比喻普及专业概念,让高深艺术走出象牙塔,成为滋养大众的精神养分。
在文化记忆面临流失的今天,《墨海拾珍》的出版具有特殊警示意义。读到93岁陈汝勤颤抖着打开《连理集》,或高马得在病床上坚持作画的细节,不禁让人叩问:算法主导的注意力经济时代,还有多少文化记忆正在消失?冯秋红用二十年记录的片段,恰如散落在记忆天幕上的星辰,标记出永恒的精神坐标。书中反复出现的“离去”意象构成深沉隐喻:文怀沙、廖静文、高马得等大家的离世,不仅是生命的消逝,更意味着特定文化传统的断层。冯秋红记录高马得将“画画手艺”视为唯一遗产的价值观,陈汝勤对水印木刻技法的坚守,实则是为濒危文化基因建立档案——这种抢救性记录在传统文化加速流失的背景下,彰显出超越文学的社会价值。《墨海拾珍》最终指向记忆与遗忘的永恒博弈。冯秋红像一位执着的文化守夜人,在时光潮水退去前,拾起那些被冲至遗忘边缘的精神贝壳。当读者跟随她的文字重访消逝的艺术现场——高马得夫妇看戏后一人画水墨、一人刻木刻的夜晚,文怀沙拒绝“国学大师”头衔时的激愤,获得的不仅是文化知识,更是对抗集体失忆的精神力量。受访者多已暮年,有些甚至已离世,但翻开泛黄的记录,仍能感受到跃然纸上的精神力量:对艺术的执着,对真理的追求,对时代的担当。墨痕或许会褪色,精神却永远流传。从这个意义上说,《墨海拾珍》不仅是访谈录,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桥梁——让今天的我们与闪光的灵魂对话,在墨痕深处读懂民族的精神密码。而冯秋红这位忠实的记录者,早已成为这段文化记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合上这本厚重的访谈集,高马得笔下那艘承载着扬子晚报二十年历程的龙舟,依然在记忆的河面上破浪前行。冯秋红用文字建造的这座记忆宫殿,不仅安放着三十余位艺术家的灵魂,更珍藏着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狂奔途中不应丢弃的文化行囊。在这个意义上,《墨海拾珍》既是对过去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未来的殷切期许——那些被文字定格的墨海珍珠,终将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继续绽放永恒的光芒。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