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这不是一本书:书有什么要紧的!”丨诗人读诗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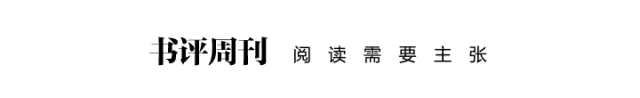
现代诗语言优美,情感丰盈,意象新鲜,但有时晦涩难解。从阅读角度看,“晦涩”是现代诗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然而,这晦涩无论是源于特定的表现方式,抑或对诗之新奇的追求,还是对“何以为诗”的定位,一首好诗不可能仅表现在晦涩,而必须值得深入阅读,让读者在认知与想象的主动参与中,发现晦涩中那复杂的诗意,充裕的内涵。
“诗人读诗”栏目邀请几位诗人,每周细读一首现代诗。这样的细读是一种演示,更是一种邀请,各位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品味现代诗的一些方法及其自由性,进而展开自己对现代诗的创造性阅读。
第二期,我们邀请诗人桑克,和我们一起赏析哲学家尼采的诗《这不是一本书》。
撰文 | 桑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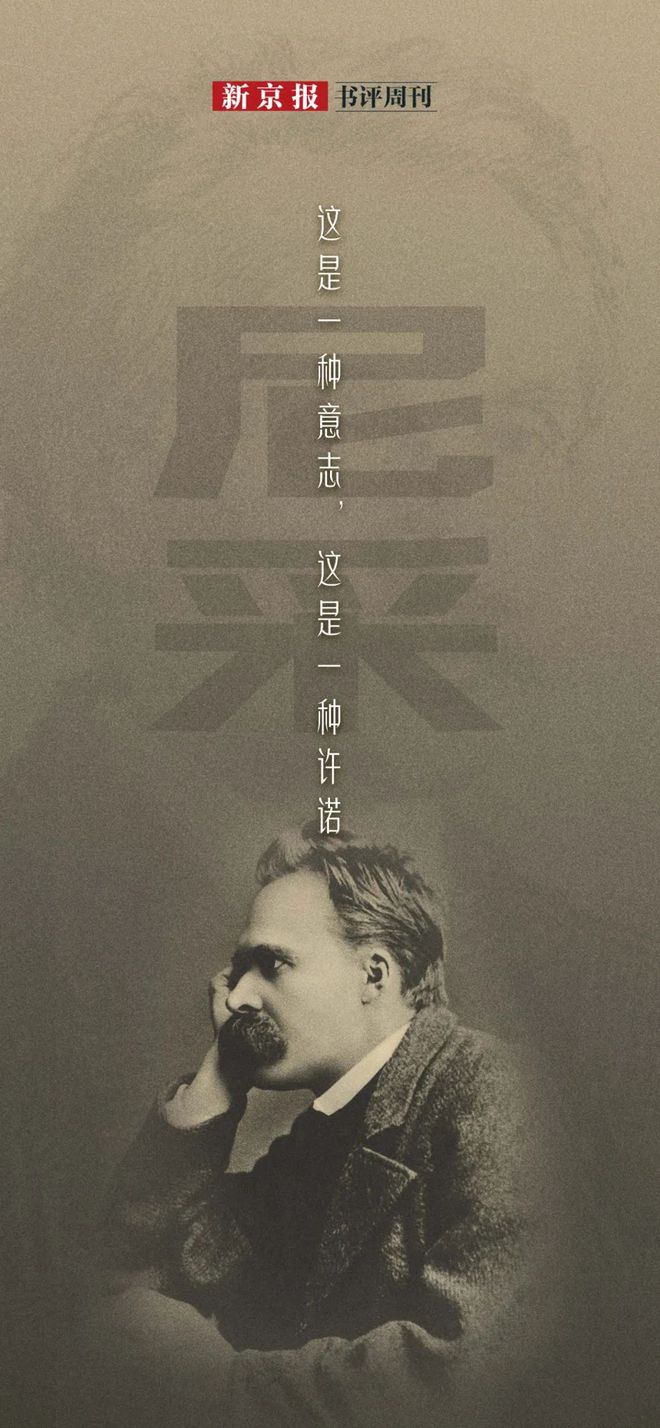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等。其诗歌在西方世界和汉语世界受到广泛关注,不仅是其哲学思想的延伸,其诗作所展现的文采和精神气质也非常独特,兼具哲人与诗人的双重特征。
本期诗歌
这不是一本书
作者:弗里德里希·尼采
译者:孙周兴
这不是一本书:书有什么要紧的!
棺材和裹尸布有什么要紧的!
这是一种意志,这是一种许诺,
这是一次最后的桥梁爆破,
这是一阵海风,一次起锚开航,
一阵齿轮滚滚,一次舵轮定向,
大炮在轰鸣,炮火冒白烟,
大海发出阵阵怪兽般的笑声——
诗歌细读
我没有能力把握尼采诗的全部或者大部,所以我在自己读过的孙周兴先生编译的《尼采诗歌新编》中挑选出一首短诗《这不是一本书》进行阐释就是为了扬长避短。但是我担心我仍旧逃脱不出接受美学之误读,以及自身不足之错读共同编织的罗网。聪明的读者想必已经看出,我这是在为自己即将酿造出来的酸酒或者咸醋制造一种借口,或者一口用以甩脱责任的铁锅。所以,作为一个没有德语阅读能力的人,我的阅读或阐释绝对是表面化的,既不深刻,也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它只是一个写诗人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不为人道的心得而已。我姑且写之,您姑妄听之。
尼采这首诗的标题和第一行的前半句都是一样的,即“这不是一本书”。明眼人一眼就瞧出来,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一个经典的诗歌定式,即“什么不是什么”,铺展开来就是——“甲不是乙”“牛不是马”“山不是水”“诗歌不是政治”“煤球不是元宵”。尼采(1844-1900)死后出生的美国诗人弗兰克·奥哈拉(1926-1966)也写过一句诗“我不是画家”,用的也是这个定式。屈指一算,两位诗人之间其实仅仅相差了二十六年,这便足以证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距并不遥远。
“什么不是什么”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否定性句式。众所周知,否定的目的就是为了拒绝和反抗,但是不可否认,其中存在着一种深层目的——就是为了确定。那么否定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否定其实也是一种确定方式。这话只是看起来绕,其实非常明确。只有否定了什么才能确定什么,即便不是彻底确定,至少可以确定一部分。尼采所谓“这不是一本书”的真正意思就是确定“这”(眼前事物)是“一本书”之外的某物。
疑问来了,难道“这”真的不是“一本书”吗?
尼采的这首诗是写在1882年7月至8月的笔记本里的,刊载在利科版《尼采著作全集》第十卷第35页。在同一页上,还有另外一首诗《快乐的科学》——
这不是一本书:书有什么要紧的!/这种棺材和裹尸布有什么要紧的!/书的猎物时代已成过去:/而在这里面,活着一个永恒的今天。(孙周兴译)
《快乐的科学》的第一句和《这不是一本书》的第一句一模一样,第二句主体相似而有所不同——《快乐的科学》的德语原文是An diesen Särgen und Leichentüchern!(这种棺材和裹尸布有什么要紧的!),《这不是一本书》的德语原文是Was liegt an Särgen und Leichentüchern!(棺材和裹尸布有什么要紧的!)。这种不同,视觉直观就可以发现。而第三句第四句完全不同,写得真好,此外就不必多言了。
当然,读者可以把这两首诗当作一首诗的两个版本或者两个组成部分。
现在尝试解读一下《这不是一首诗》。它的前两句是,“这不是一本书:书有什么要紧的!/棺材和裹尸布有什么要紧的!”
“这”不是一本书,仔细琢磨,这种表达实有欲盖弥彰之嫌。“这”很可能就是一本书,只不过尼采本人不愿意承认,其原因就是“书有什么要紧的”。书不重要。另外一个尼采中译者钱春绮先生把这个理由译成“书算得了什么!”英译者詹姆斯·卢切特(James Luchte)把这个理由译成“what matters books!”,书真的不重要。而且尼采进一步将“书”视为“棺材和裹尸布”——与死亡关联的腐朽事物,书“有什么要紧的”/“算得了什么”。
人人皆知,否定之后就是肯定。尼采连用四个“什么是什么”的经典诗歌定式来肯定“这”究竟是什么。

老彼得·勃鲁盖尔《有伊卡洛斯坠落的风景》
“这是一种意志,这是一种许诺,/这是一次最后的桥梁爆破,/这是一阵海风,一次起锚开航,/一阵齿轮滚滚,一次舵轮定向……”
“这”是意志(Wille)和许诺(Versprechen),意思相当明晰。从普通语义来说,“意志”就是人类自觉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倾向,从哲学概念来说,“意志”的内涵比较复杂,暂时将之理解为一种推动力吧。“许诺”就是提出可以兑现的约定,从哲学角度来看,“许诺”涉及社会契约论等讨论范畴。“最后的桥梁爆破”(letztes Brücken-Zerbrechen),钱春绮先生译为“最后的桥梁破坏”,詹姆斯·卢切特译为“a last breaking of bridges”(最后一座断桥),还有一个英译本译成“a last bridge to break”(最后一座要断的桥),我建议读者也许可以将之理解为最后的出路吧,在桥梁最后损毁之前赶紧通过,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海风”之后的两句其实不必引申,就把语义停留在词句表面也就行了。这种方法其实适合解读大多数词语镜像。词语构成画面,读者直觉可视。一个人吹着海风,起锚开船,齿轮转动,把船舵固定在航向上……此等画面,可谓其乐融融也。
与尼采形似的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他连用六个“什么是什么”来肯定或者定义“诗”是什么。“这是充满力量的尖利的哨声,/这是相互挤撞的冰块的咯吱,/这是让树叶结满冰霜的夜晚,/这是两只夜莺决斗的声息。//这是已经干缩的甜豌豆,/这是豆荚中的宇宙的泪水……”(吴笛译)其中含义之丰富,迫使读者必须安装至少两副想象力的翅膀,才能将物像与“诗”有机而精确地联系起来。
返身再看尼采《这不是一本书》的最后两句,“大炮在轰鸣,炮火冒白烟,/大海发出阵阵怪兽般的笑声——”至此读者才会突然醒悟,尼采的这艘航船原来并不是游艇,而是拥有大炮的军舰。之前阅读设想的美好画面必须依此纠正。而“大海发出阵阵怪兽般的笑声”(Es lacht das Meer, das Ungeheuer)又是什么意思?这是大海对军舰大炮轰鸣的正常反应还是助纣为虐?难道它的笑声是一种嘲笑?钱春绮先生将此句译为“大海、这庞然巨物,发出笑声!”意思相当明确,“大海”和“庞然巨物”(即孙周兴先生所译之“怪兽”)是同一事物。詹姆斯·卢切特将此句译为“The sea is laughing, the Monster!”他的翻译与钱春绮先生的理解基本一致。大海如此反应,军舰又当如何?“这不是一本书”的“这”又当如何?
最后两句把全诗的方向扭向让人不安的没有答案的境地。但是尼采也许正在享受这种意想不到,并把“不合时宜”的思想变成烟雾迷漫开来。与此同时尼采本人正像他1888年2月写给勃兰兑斯的信中所说的,“我像鸟一样飞翔于高高的天际,盼望着能以尽可能非现代化的眼睛考察现代世界的一切。”非现代化VS现代,变换或者错置一种方式,也许再看这首诗(暂时别提“一切”)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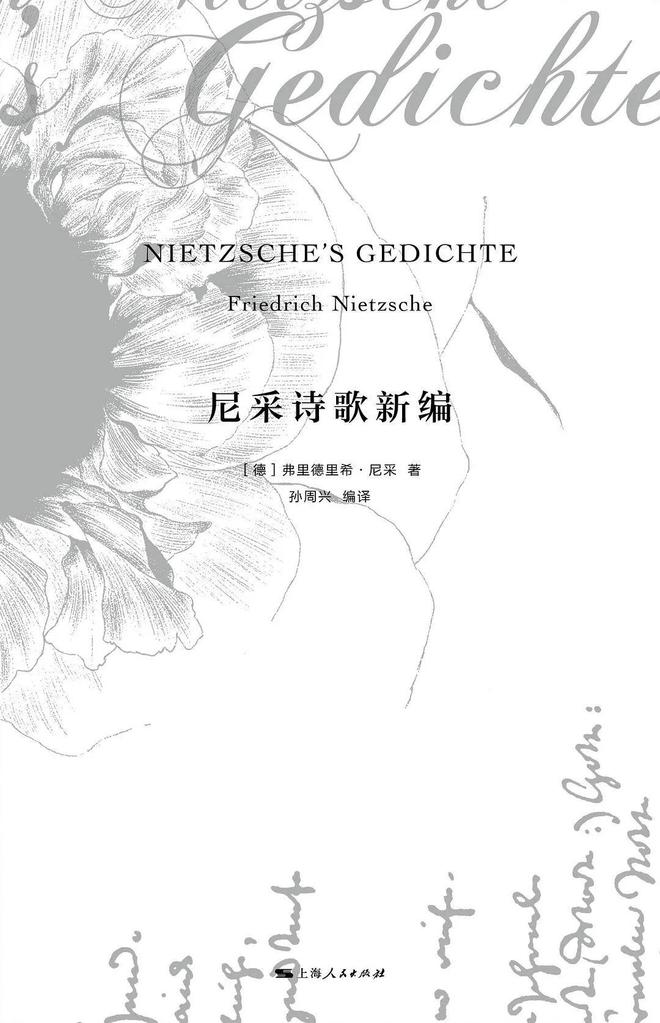
《尼采诗歌新编》
作者:弗里德里希·尼采
编译:孙周兴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8月
回顾上期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桑克;编辑:张进;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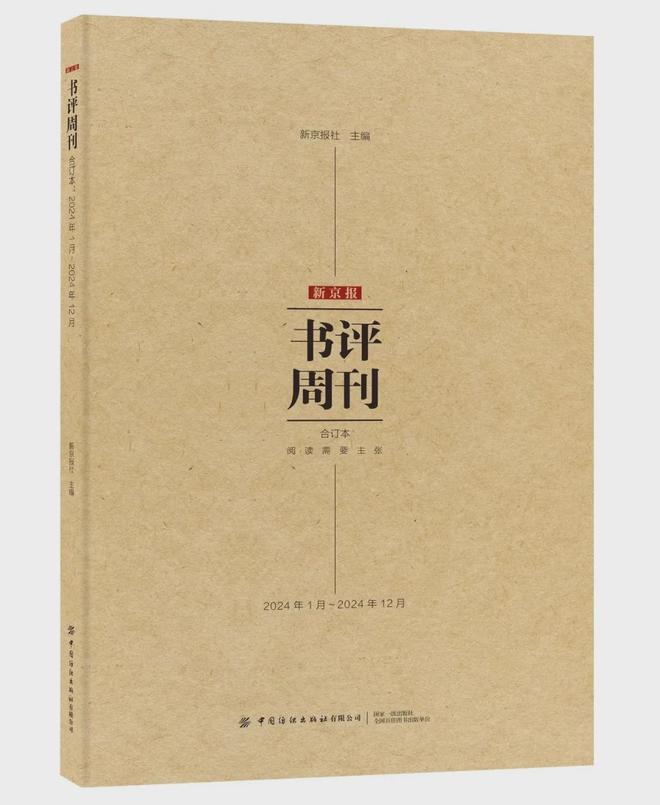
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