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淳读《法哲学基本原理》|马克·墨菲与当代自然法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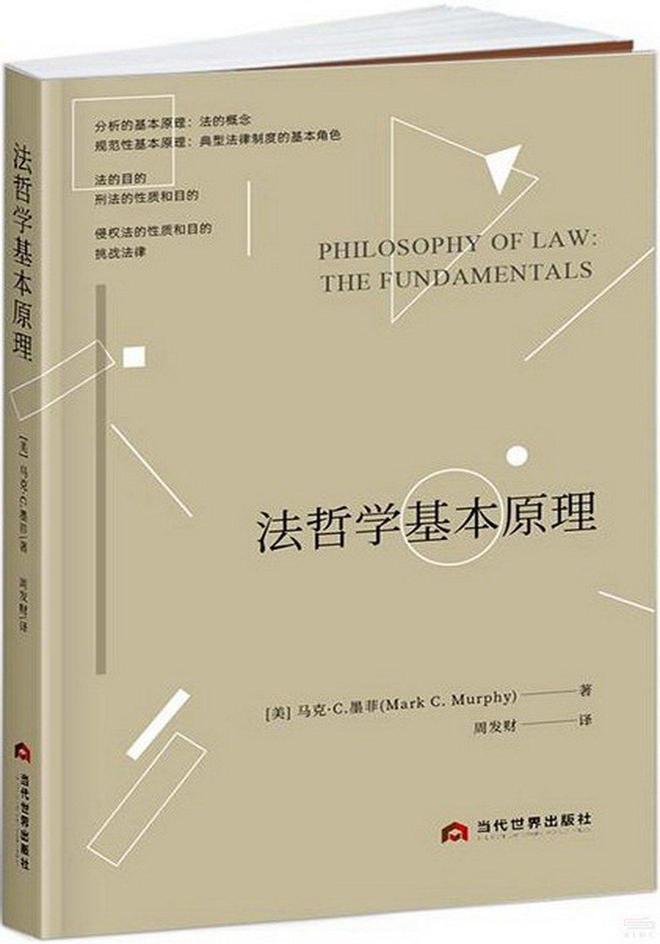
《法哲学基本原理》,[美]马克·C. 墨菲著,周发财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234页,7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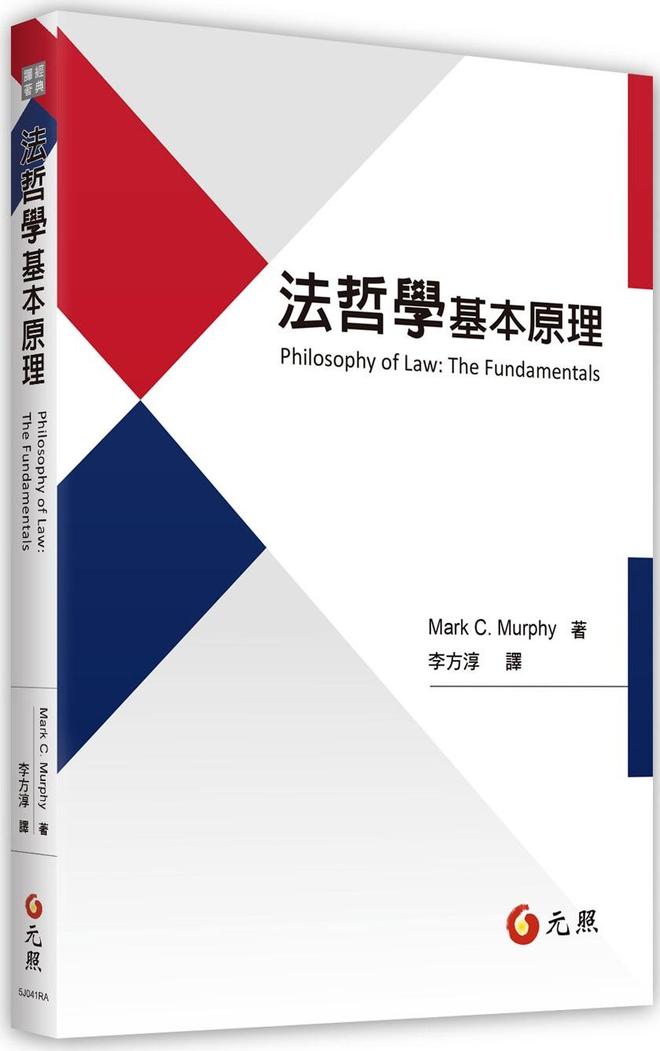
《法哲学基本原理》,[美]马克·C. 墨菲著,李方淳译,元照出版公司,2025年4月出版,256页
在今天的法学院课堂上,自然法理论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虽然大学教师都不得不讲授它的历史,却很少有人承认它对当代法理学的实际贡献。这种矛盾使自然法沦为法学课堂的装饰品,不可或缺却又无关紧要。在这种境地下,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教科书几乎都是出自法律实证主义者之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哈特(H. L. A. Hart)的《法律的概念》,任何持自然法立场的教科书都难以相媲美,他为法理学讨论设置的框架否定了自然法的一些基本立场,使得自然法进一步沦为一个没有价值的错误理论。
直到当代自然法理论的兴起,这个局面才有了些许好转,以菲尼斯(John Finnis)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承认实证主义对古典自然法的批判,但他转而运用哈特的框架来为自然法正名。虽然菲尼斯可被视为当代自然法理论的开创者,却远非其终点。自1980年《自然法与自然权利》问世以来,自然法理论在英美学界逐步受到关注并日趋成熟。新一代自然法学者的讨论远远超越了菲尼斯讨论的广度与深度,涉及伦理学、政治学与法哲学等各方面话题,且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有一部梳理自然法理论讨论的作品就显得尤为必要。
《法哲学基本原理》正诞生于这个背景之下。作者马克·墨菲(Mark Murphy)是刚逝世的伦理学、政治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但并未受到其师观点的直接影响。他在前期关注于自然法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哲学问题,而后转向宗教哲学研究。他有关法政领域的讨论多集中在《自然法与实践理性》与《法理学和政治学中的自然法》两部著作及几篇零散的论文中,而《法哲学基本原理》可以认为是对他同年出版的后书进行的梳理与提炼。墨菲在本书中意图用三个基本共识(commonplace)来统摄各类法律理论,以此为标尺检验它们的合理性。
三个基本共识
墨菲选取的三个基本共识分别是:法律是社会事实;法律具有权威性;法律要为了共同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基本共识只意味着这些信念得到大多人的认可,它既不能担保这些信念为真,也不能保证通过研究这些信念之间的重叠与矛盾,我们能够获致什么明确的结论。基本共识能够担保的只不过是,它们是恰适的研究起点。
这三个基本共识实际上是法理学领域讨论的重要话题。墨菲在书中着墨不多,我们需要进一步澄清。
法律是一个社会事实,这个命题是哈特以来的英美法理学家的共识。社会事实是一个描述性的,涉及多个主体存在及他们之间关系的事实。哈特借由这个命题构筑起当代法律实证主义的典范模式。哈特将法律义务看作我们的行动理由,它们由诸种社会规则所支撑,而这些社会规则只有在诸种实践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存在(Ronald Dworkin, “The Model of Rules II,”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46)。这些实践条件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外在面向,它是对诸种行动模式的描述,这种面向表达了描述性的社会规则。譬如,教室里大多数学生都坐在教室左侧。与之相关但有所不同的是社会规则所具有的内在面向:它是一个行动模式所涉的行动者对于其所保持的反思批判的态度。借用德沃金的举例方式:(a)每个学生都坐在教室左侧,(b)其中一个学生被问到他为何要坐在教室左侧并回答说是这样一条规则要求他如此去做,(c)某个学生因忘记坐在教室左侧而受到他人批评甚或惩罚——当这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时,就可以认为存在所有学生都要坐在教室左侧的法律义务。当代法律实证主义者通过社会实践来解释法律的性质,并主张法律的地位是由其来源而非其背后的价值所决定的,这种做法深刻地冲击了忽视这一点的古典自然法理论。但像菲尼斯和墨菲这样的当代自然法学者所做的不是退回到古典,而是在哈特圈定的框架内做文章,即在承认哈特所说的外在视角和内在视角分野的前提下,在哈特没有详加阐发的内在视角里重唤自然法的活力。因此可以说,在当代,无论是自然法学者还是实证主义者,大多都会同意社会事实属性是法律的(一个)性质。
法律具有权威性则意味着法律由绝对性的服从理由来支撑,这在墨菲看来是自然法法理学的核心主张([美]马克·墨菲:《法理学和政治学中的自然法》,王志勇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9页)。我们可将权威做两个层面的划分:理论权威与实践权威;正当权威与事实权威。理论权威是认识上的权威,这样一种权威以塑造其权威对象的认知为目的。理论权威的指示是一个人相信其主张正确的理由,譬如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汉代在唐代之前,而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是真的本身即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是真的的理由。与之相对,实践权威是行动上的权威,这样一种权威以规导其权威对象的行动为目的。实践权威的指示是一个人按照其主张行事的理由。譬如,家长命令他的孩子打扫房间,这个命令本身赋予孩子打扫房间的理由。第二个划分是正当权威与事实权威。前者是恰如其分的权威,譬如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后者则是被相信具有如此权威,而不论其实际配位与否,譬如一个信口雌黄,但被所有人奉为权威的骗子。正当权威与事实权威在逻辑上是交集关系,被信奉为具有权威的人当然也可以是个恰如其分的权威。
那么法律是怎样的权威?法律旨在规范人的行动而非塑造其认知,这意味着它是实践权威,但法律究竟是事实权威还是正当权威则是个不够明确的问题。在拉兹(Joseph Raz)那里,法律的本性在于主张自己是正当权威,而它至少要是一种事实权威。至少在实证主义者内部,法律是一个事实权威是可以得到辩护的。
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于,自然法学者要如何承认非真正权威的效力?一部恶法是由实践权威而非真正权威制定并颁布,实证主义者会认为,透过社会实践,我们会承认一部恶法依旧是法律,而不会因为其不道德性影响其地位。自然法学者可以对此给出三种反驳。一种认为,自然法不过是用来提示道德性对于法律的重要性,而我们服从的法律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实践合理性。墨菲对此的批判在于,这种观点将自然法理论转化成了一种极为无趣的道德哲学理论,而脱离了分析法理学的框架。正如上述所言,在墨菲看来,在那个时代捍卫自然法理论,不是要另起炉灶远离实证主义者的炮火,而是在分析法理学内部完成这项工作。而满足这个要求的自然法法理学又被墨菲进一步区分为强自然法理论与弱自然法理论。尽管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能用这一点来恰如其分地概括,但我们可以这么说,强自然法主张规范的正义性是法律占据其地位的必备要素,这个主张也可被称作恶法非法命题,这种立场必然会受到实证主义者的攻击,因为它仅承认真正权威的立法权威。另一方面,弱自然法理论则认为,法律就其本身而言存在法律性(legality)以及作为法律的内在标准,但违背这些标准的恶法不必丧失其作为法律的地位。这是因为墨菲引入了缺陷的概念,一部有问题的法律或者不是法律,或者仅仅就法律而言是有缺陷的(同上,25页)。在这样一种观点看来,经由承认规则引入的法律可能是恶法,但这仅仅是有缺陷的法律,并非不具备法律的地位,故而它可以承认事实权威的立法权威。这个观点看上去问题重重,但让我们暂且停在这里。
第三个基本共识是法律是为了共同善。共同善是一个对于所有共同体成员来说都是好的状况,这个基本共识强调法律要惠及社会各个阶级,它不能沦为某个阶级的权柄以用来压迫其他阶级。将此称作基本共识是相当奇怪的做法,对于自然法学家而言,这是个不必多言的真命题,但对于实证主义者而言,这至多也不过是一个非本质性的要素。在实证主义者那里,共同善的地位要么是不受认可的(奥斯丁[John Austin]的粗糙实证主义),要么是非常薄弱的(哈特的精致实证主义)。但德沃金对哈特的批判使得实证主义阵营内部依据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立场,又划分为刚性与柔性的实证主义。在墨菲看来,刚性实证主义认为道德必然不能够纳入法律当中,从而将共同善坚决地排除在外,而柔性实证主义则认为这是可能的,这最终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承认规则能否接纳道德。但即便实证主义者对共同善命题大多持否定态度,墨菲仍坚持他的弱自然法理论至少在表面上能够兼容实证主义的主张,这仍要回到他所提出的缺陷概念。
但在讨论缺陷概念之前,有必要回应墨菲对两个实证主义阵营的勾勒。墨菲在本书对两种立场的刻画过于语焉不详,很容易让我们误解实证主义者对于道德和法律关系的看法。实际上,无论是哪位重要的实证主义者都不会否定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关系。如加德纳(John Gardner)所说,法律实证主义关注的是法律规范的效力条件,并且可以与任何有关法律本质的命题相兼容。这个主张只是告诉我们,在识别法律的时候,我们是依据规则的来源而非价值(包括来源的价值)来识别它的。换言之,实证主义者只是主张,道德(必然或是可能)不能成为识别法律的判准。但从这个结论并不能够推出更强的法律与道德在方方面面都不存在联系的命题,也鲜有作者会这么提(John Gardner,“Legal Positivism: 5 1/2 Myths,”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2001]: Vol. 46:Iss. 1, Article 12)。
缺陷概念——衔接自然法与实证主义
我们立即就可以想到一个批判缺陷概念的说法,说任何东西在其目标落空的情况下是有缺陷的,只不过是换种表述来说它不是这样一种东西罢了,这种说法没有实际价值,我们可以将此称作诉诸琐碎性(triviality)的批判。
若要回应这种批判,就需要明晰墨菲赋予“缺陷”的意涵,墨菲对于这个概念的论述包含在他独特的功能主义进路中。我们可以将此拆分成两个命题:功能构成命题与包容性的功能归属命题。功能主义进路要求从一个事物整体的功能来理解其各部分拥有功能的状态。只有将一种功能归属给一个事物整体,我们才能够理解构成该事物的各部分的地位,换言之,部分之所以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个部分的功能对于整体的功能有所贡献(Mark C. Murphy, Natural Law and Practical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23)。譬如,蜂鸣片之所以是闹钟的一个部分,是因为其运作的特征构成了闹钟的一部分;一个玩具车并不属于人的一部分,也是因为他运作的特征并不构成人的一部分。墨菲将此称作功能构成原则:如果x由于x的功能f而是y的一部分,那么就存在一个功能g,它是y的功能且x发挥y的功能对之有所贡献。借由这个命题,墨菲将部分的功能与整体的功能勾连起来。
包容性的功能归属命题则源自于他对麦克·摩尔的功能归属命题的批判。在摩尔看来,除非我们寻得法律所服务的一些独特目标,否则我们就没办法确定法律是什么。而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目标,那么为了促成这一目标,法律就必须向人施加道德义务,而任何不能满足此条件的法律都不能称之为法(《法理学和政治学中的自然法》,65页)。通过将目标作为法律性的唯一来源,摩尔确保了法律的道德性。再以闹钟为例,蜂鸣片因为其独特的运作特征而属于闹钟,但如果蜂鸣片无法发出响声,从而使得闹钟无法发挥叫醒人的功能,那么根据摩尔的推断,这样的闹钟因为其功能的落空就不能再称作是闹钟。
墨菲对此的批判在于,摩尔过分强调目的作为法律性与守法的道德义务的唯一来源,而忽视其他可能的来源。在墨菲看来,我们守法的另外一个来源在于法律实现其目的所依赖的典型活动,或者说只有通过这样的活动,法律目的才有可能实现。譬如,蜂鸣片可能会拥有不同的质料与形式,而既然蜂鸣片的目的在于发声,那么就只有那些典型活动在于制造声音的物体才能被恰如其分地被称作蜂鸣片。这可以表述为:若要认为x属于某种功能类型F,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典型活动做φ就是要实现某些特殊的目标状态S(同上,66页)。由此,墨菲让手段也成为了法律性与守法义务的来源,从而使得缺陷概念的存在得以可能。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保证这个命题不会是无意义的,即假如目的的落空也会使得手段落空,那么包容性的功能归属命题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墨菲的办法是为手段提出不同于目的的判准,对于手段要适用在常态性背景(background of normalcy)下的优先判断。这就是说,做φ是x的典型活动并不意味着x永远都能够做φ,而是说x是做φ的那类事物,即便在x没能做φ的时候也是如此。再回到闹钟的例子,墨菲会认为,蜂鸣片因其在常态下的发声功能而属于闹钟,那么在异常状态下,虽然发声所要促成的叫醒人的目的落空,但是由其优先性判断所确保的手段并没有落空,那么即便是在异常状态下,其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属性也能够得到确认,而蜂鸣片坏掉的闹钟并不会仅凭其目的的落空而不被称之为闹钟,而只是有“缺陷”的闹钟。当将此套用在法律上面,就可以说,当法律依照充分理由来指示人类行动时,人们便能够适当地发挥功能并保障法律所欲以达致的目标得到实现,但没有如此做的法律作为法律而言就是有缺陷的。
在理解“缺陷”概念的意涵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墨菲如何用这个概念勾连自然法与实证主义。比克斯(Brian Bix)曾指出,一部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某种社会事实,而非其是否符合道德。现实中可能有许多我们认为不道德的法律,但尽管如此,它仍旧是一个社会通行的标准,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部恶法,但不会因此就认为否定它的法律地位。总之,实证主义者会主张,法律的道德性是一回事,其是否有效是另一回事。
墨菲则反过来将这点作为攻击实证主义者的手段,说一个社会的法律是由那个社会的事实所决定的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成员不可能犯错,或者说,“比克斯在根本上低估了概念使用者在使用这些概念的过程中的可谬性”(同上,41页)。一个社会的成员对于法律的认识不一定会符合社会事实,因为错将不该承认为法律的规则承认为法律亦或反之都是社会中常见的事情,所以比克斯过分夸大了社会事实命题的作用,并忽视在实践中犯错并制定出一套有缺陷的法律的可能性。由此,弱自然法与实证主义在缺陷的法律上产生交合,两者都会承认法律可能是有缺陷的,不过弱自然法的旨趣并不在于研究有缺陷的法律,而是要“发展更充分的没有缺陷的法律性理念分析”([美]马克·墨菲:《法哲学基本原理》,李方淳译,元照出版社,2025年,55页),二者可以共享同一个基础,并沿着这个基础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方向。
不过,更确切地说,两者的关系是貌合神离的。虽然两者都会承认“不义的法律仍是法律”这个命题,也承认法律可以依据纯粹描述性的标准来识别,但是它们的出发点以及精神则是背道而驰的。实证主义者无需再为描述性添加任何条件,但是自然法学者则会认为,这种标准的确立必须要诉诸实践合理性(不同学者可能会用不同的词来表达这一概念,菲尼斯使用practical reasonableness,墨菲则使用practical rationality,但他们表达的意思几乎是相同的,亦即人类合理地安排自身事物所达致的良好状态)。由此,自然法学者可以主张存在一些属于法律本性的规范性条件。
如此分歧也使得自然法学者关注的侧重点与实证主义者不同。虽然自然法学者承认缺陷法律的存在,但他们关注的重心在于无缺陷的法律是怎样的,它需要哪些准备条件以及由此可以发展出怎样的讨论。这使得自然法发展出与实证主义不同的研究进路。自然法学者在道德哲学领域主要关注于实践理性与基本善问题,而经由在法哲学领域所确立起来的法的目标,他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过渡到对共同善的政治哲学话题。
立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的义务
在结束自然法与实证主义之争后,作者开始着手讨论典范法律体系的角色及其义务问题。墨菲指出,每个法律体系必须要具备三个基本角色:守法者、立法者以及法官。尽管这些角色各自有别,但它们都要回答两个相同问题:构成性问题,即担任该角色需具备的条件,和实质性问题,即该角色应当如何履行职责的政治义务问题。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三个角色构成性理由都是一样的:他们具备如此角色是由社会实践所确定的。
而尽管每个角色所遇到的实质性问题都有所不同,但墨菲最终给出的回答是让他们置于这样一幅图景之下。对于每个具体的政治社会而言,都有着其独特的共同善,而其中一些共同善通过法律被公平地分担给每个社会成员,如此,每个成员就具有为着共同善而尽到其份额的义务,这是三个基本角色的义务来源。墨菲将此称为共同善原则。在这种观点下,共同善原则蕴含了守法义务以及其它内容,我们也可以说,遵守基本角色的要求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共同善原则。
这种粗糙的表述听起来难免有些乏味,我们不妨将它们和作者在尾章对这些角色的批判放在一起考虑。
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分别针对三个角色给出不同的批判理论,但我们可以将它们理解成对于不同视角对于共同善原则的批判。哲学无政府主义认为我们无需借助权威和法律便可认识到如何行动是道德的并据之正确行动,故而权威不过是个不必要的介质。批判主义则主张社会中存在的共同善不过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从而反驳了对所有成员都是不偏不倚的共同善的可能性。法律现实主义则指出法官裁判过程中的开放性问题,主张法律本质上是政治,立法者与法官之间的界限并非截然二分的,相反,他们不过是在不同语境和社会约束下运作的法律制定者。这种观点主张法律具有不确定性,进而批评作为分配共同善的法律工具的地位。
针对第一个批评,墨菲指出权威所具有内容独立性的规范性力量,这意味着权威命令自身就是促使守法者遵守命令的理由。说每个社会都有着共同善并不能够使其适用于这个社会之中,而若要满足这个目的,就需要对共同善进行具体化。这项工作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完成:一方面是从共同善相关的道德原则出发进行演绎,另一方面则是对某些一般性事务的慎断(determination)。譬如,从杀人是不好的推演出不得杀人的一般性规则就属于前者。后者则指的是,我们要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之间确定其中一种作为我们社会的规则,譬如,酒驾应当受到禁止,但我们应依照何种标准来认定酒驾,却是有一定开放性的问题,通过摄入量、对身体机能的损伤程度亦或血液酒精含量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在这些开放性的选项之间只能有一套方案成为权威命令。就此而言,立法者订立法律的活动就如同建筑家在构筑房屋一般,道德诫命确立了房屋最低限度可接受的形式,而在这个限度内具体设计怎样的形式并采用怎样的质料全属立法者慎断的内容。但除非权威命令具有独特的规范性力量,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守法者为何要依据这套而非那套方案行事,就此而言,法律对共同善的具体化构成了每个人为着共同善尽其份额的必要内容。
针对第二个批评,墨菲认为,批判主义并不能够从各个阶级拥有不同的价值观推导出各个阶级的利益事实上是相对的。再者,批判主义只是在宣称每个人的价值观具有受到其所处阶级成员所分享的价值观的倾向,但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就是被如此决定的。最后,符合共同善原则的法律并不会沦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相反,它总是可能会选择性地削弱支配状况,或至少为更剧烈和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形式铺平道路。
针对第三个批评,墨菲的办法是从两个角度削弱这种批评的力量。首先,即便我们承认法律不确定性的存在,这也难以对法官角色造成有利的批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定分止争的职能从功利角度考虑,仍旧是在许多情形下都是值得保留的东西。再者,法律不确定性的范围也远比现实主义者强调的要小,在许多明显情形下,社会成员所持有的共同道德见解本身就足以作为规范性来源,法官在这些事务上的裁判也不会偏离这种见解。
为共同善立法
在明确共同善原则的基本主张及其与守法义务的关系后,墨菲开始着手处理法律目标的问题。基于上述确立起来的法律作为实现共同善之手段的论述,墨菲认为,法律的目标即在于“法律应该通过权威性规则来支持的那部分共同善”(同上,81页),他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就是哪部分共同善应当由法律加以规制,以及哪些应当排除在外。
在这里,墨菲将密尔的伤害原则奉为典范。密尔的理论是功利主义式的,这种观点承认善之于正当的优先性,以及它作为所有伦理问题的唯一终极诉诸的地位。根据这种观点,个体是对于自身的终极主宰,他是最能够理解自身幸福是什么的人,而既然所有人都以追求幸福最大化为目标,那么就可以推定个体是自身幸福的最佳决定者,且为了保护个体的自主性,法律就不能干预个人指涉自我的活动。另一方面,这也不意味着所有指涉他人的行动都是应当由法律干涉的,在密尔看来,法律对行为的约束只有在迫使主体尊重属于他人的东西时才是合理的。他举出三种应当受到规制的行为类型:1. 直接削弱他人福祉的行为;2. 没有对特定的对象履行义务;3. 没有实现过正派的共同生活所需满足的要求。尽管密尔的理论看上去为法律划定了清晰的边界,但他的理论仍旧受到外延不清晰的批判。有些滋扰性的冒犯行动似乎正处在这个边界上,而密尔并没有为此给出论证。此外,密尔也承认对一些特殊人群(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和有损自主性的例外干涉。这为家长主义进路的干涉理论留出了空间。家长主义的基本立场预设,在行动中存在一系列可比较的选项,而干预的选项是被干预者经过慎思后也会赞成的。那么,对自主性的干涉就可以通过保护更大的益品来得到证成。
另一条有前途的理论来自罗伯特·乔治对德富林主义的再阐发。德富林主义的出发点在于拒绝具有神学色彩的批判性道德与法律之间的联系,转而选择将具有非认知主义色彩的实定性道德作为法律背后的基础。这种道德“源自存在于共同体中的对错感”([英]帕特里克·德富林:《道德的法律强制》,马腾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29页),是一个社会中公正的成员所持的态度。此外,他也批判传统理论对于公共与私人领域的截然二分,在德富林看来,行动的不道德性本身就威胁着维系整个社会的道德纽带,这就足以证成对这些行动的禁止,无论它是“公共”或“私人”的(同上,32页)。
乔治反对德富林将批判性道德与神学知识捆绑在一起的做法。乔治认为,即便一些批判性道德可以通过宗教理论得到解释,但是它们同样可以凭借自然理性来得到充分认识,从而没有理由反对道德背后的认知基础。进一步,乔治指出只有凭借理性认识的道德才能够作为立法的适切基础。基于这些判断,乔治发展出他自己的多元主义至善论,这种理论承认人类善的多元性,并将各式各样的人类善纳入其中(Robert P. George, Making Men Moral: Civil Liberties and Public Mor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 228)。它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更广阔的图景:各式各样的个体透过交流彼此的内在思想和意志达成合作,并通过合作联系在了一起,由此形成了人际间的和谐与友谊关系,而这种友谊关系是人类福祉的一部分。过上这样一种社会生活属于人类福祉的一部分,而政府应当尊重、保护和促进这样的人类善。
上述两种理论都属于福祉主义的讨论范畴,墨菲还给出了另一个超越福祉主义的进路。这条进路的主张非常清晰直接:一个政治社群的共同善囊括了这个社群的所有成员的繁盛,这些繁盛要以这些成员享有那些真正使得人类生活运转良好的善为条件。这些善的范围远超出了福祉主义限定的框架,而可以囊括所有对人类有价值的目标。这种主张将保护一个美德盛行的道德共同体视为一种理想,并且实现这种理想的一种方式是限制某类不道德的行动,由此证成了为道德立法。
结语
回忆起作者在开头树立的目标,即便我们承认三个基本共识对于法理学研究的重要性,也很难肯定这三者能够成为各式理论的试金石。若非经过新分析法学的洗礼,人们或许很难承认法律的社会事实属性是一个基本共识。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讨论同样也并非所有理论的立论基础,即便是否定道德对于识别法律的重要性的刚性实证主义,也不会凭此就被视作是成功或是失败的,更准确地说,道德在这种理论里是不重要的。可以说,几个基本共识既不基本,也非共识,更难以用来验证各式理论。我们最好还是将它们看作墨菲为自然法理论设定的几点基础。
不过另一方面,这本书仍旧很流畅地总结与梳理了当代法理学与政治哲学的一些重要议题,它也是作者为自身立场辩护的一次尝试。在一些读者看来,墨菲直接从法理学话题没有任何铺垫地转向政治哲学讨论会显得有些诡异,但是在墨菲这般的自然法学家看来,即便自然法的法理论能够独立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讨论来得到证成,只要这种法理论能够得到证成,人们就会意识到一个丰富的法理学讨论是不能脱离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话题,这三者的讨论应当贯通的。这意味着,自然法学者与其老对手的问题域就是不重叠的。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