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晓薇|从《蟠虺》到《听漏》——刘醒龙“青铜”小说的代际

刘醒龙“青铜重器三部曲”系列长篇小说目前已有两部问世,分别是2014年出版的《蟠虺》和2024年出版的《听漏》。这两部作品以青铜重器为主角、以武汉为地域背景,与刘醒龙其他以鄂东故乡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放在一起,仿佛一棵大树上分出的两枝特别与众不同的枝桠。但撇开小说题材内容等层面,我们仍可以感受到小说内里的精神延续性,其中之一便是刘醒龙小说一以贯之的传统品格。本文从代际伦理、叙事空间层面进行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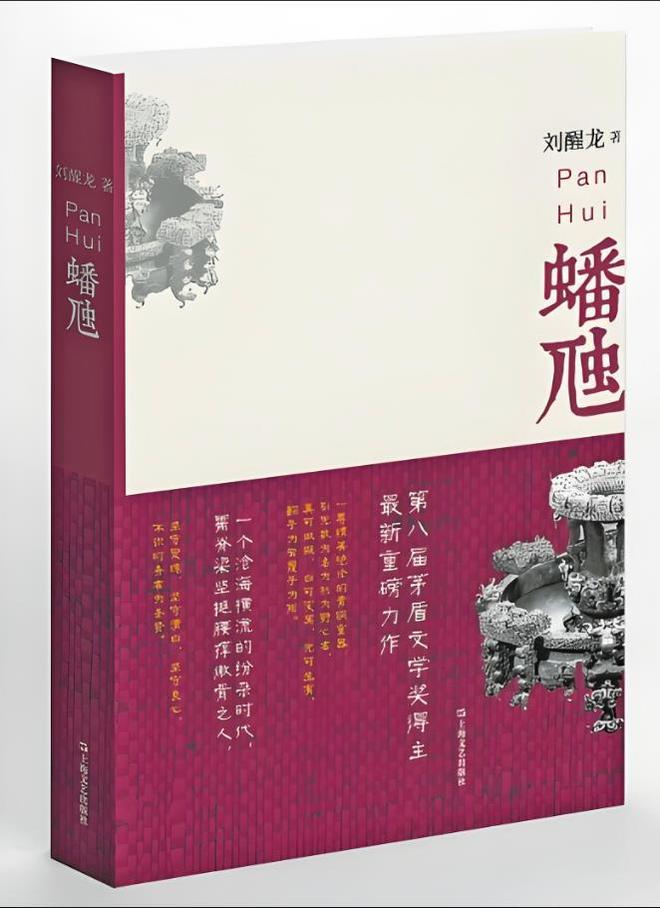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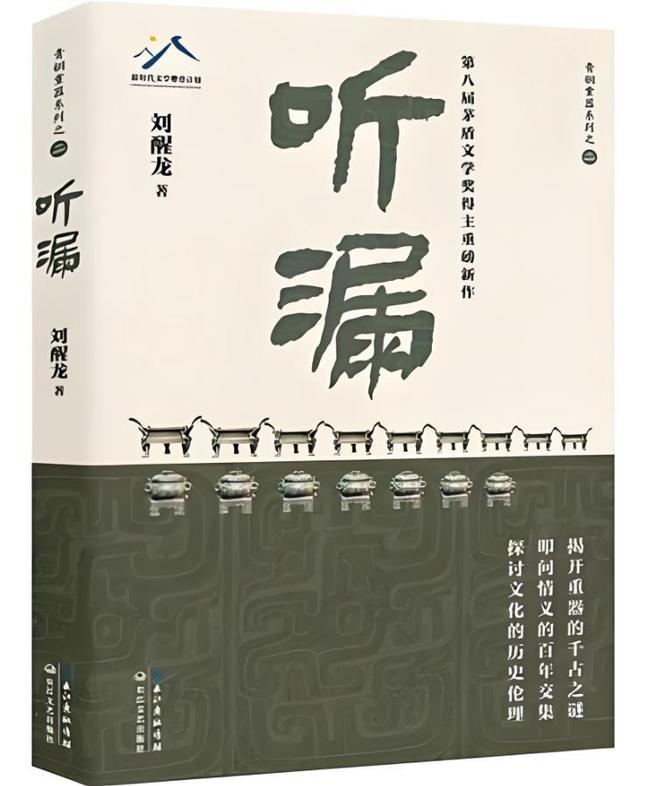
父业子承的代际伦理
父业子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很常见,在传统商业或手工业中,子辈通常会接手父辈经营的产业或传承父辈的技艺。父业子承的代际传承将职业或事业传承与家族传承联系起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在《蟠虺》《听漏》这两部小说中,父业子承的代际关系是十分显然的。
《蟠虺》最直接的父业子承发生在郝文章与郝嘉、曾本之之间。郝文章是楚学院号称“青铜重器研究上百年不遇的天才”郝嘉的私生子,从小在孤儿院长大,长大后考上武汉大学考古系,毕业后到楚学院工作,在从未接触父亲的情况下走上了和父亲相同的职业道路。这种职业道路的选择当然与传统的父业子承中父辈直接影响子辈作职业选择有区别,但是在后续的发展中,作为生父同事兼好友的曾本之弥补了郝嘉的缺位,成为传、帮、带的师傅,而后来郝文章与曾本子女儿曾小安恋爱并婚生楚楚,郝文章与曾本之从单纯的师徒关系转变为有姻亲关系加持的师徒关系,从“外人”变成“自己人”,这其实是传统父业子承的现代变体。郝、曾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但通过姻缘关系结成一家,将家族伦理编织进职业中,父业子承的传统并无实质变化。
有意思的是,小说还通过否定曾本之、郑雄这一对“父业子承”关系,凸显了郝文章、曾本之的父业子承的合理合法。曾本之与郑雄也不是血脉父子,但是通过与曾小安的婚姻,郑雄进入了曾本之的家庭。然而,在此后的学术事业中,翁婿二人的工作思路与学术理念发生分歧,最终曾本之通过对郑雄的双重否定——从学术层面将他定性为“伪器”,从姻亲关系层面将他定性为“伪娘”,将其逐出师门和家门。曾本之对郑雄双重否定的过程,同时也是他对郝文章双重肯定的过程:一方面他澄清了郝文章的过错(盗窃曾侯乙尊盘),另一方面,他默认了曾小安与郝文章重修旧好,从家庭关系层面接纳了郝文章。随着监狱生活的终结,郝文章最终实现了双重“归位”——学术关系成为曾本之的接班人,家庭关系成为曾本子的“半个儿子”。
到了《听漏》,主角换成了三大泰斗之一的马跃之,相对而言,那种浓稠的考古事业代际传递的关系和氛围也变得疏淡,但仍然盘旋萦绕着。马跃之本是青铜重器研究专家,但后来转向丝绸等杂项研究,三十多年后又重回青铜重器研究;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他与小玉老师的非婚所生之子陆少林诞生、成长并成为青铜重器收藏家的过程。至此,马跃之的青铜重器事业有三十多年的迂回,而陆少林也以青铜重器收藏的方式变相地传承了父业,这是传统父业子承现象的另一种现代变体。
父业子承的职业代际传递,在谋求物质生存的职业或寄托精神文化追求的事业中投射进了传统血缘伦理和部分婚姻伦理:一方面,在传统社会生产条件和生产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家族抱团,形成较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利于所承传的职业、事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这些代际传承的职业、事业也会反过来保障家族的生存与世代繁衍。父业子承其实是古代“人的依赖关系”时代的产物。因此,《蟠虺》《听漏》中或浓或淡的父业子承伦理现象实际正是小说所具有传统品格的一种折射。
叙事空间的公私叠合
从叙事空间角度看,《听漏》《蟠虺》所涉及的物理空间,大多存在较明显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重叠甚至是融合的特点。
私人空间也叫私人领域,是指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包括物质性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精神性的私人生活空间。公共空间是指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在这样的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聚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在传统社会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高度融合,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所谓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区分,因为,在古代“人的依赖关系”中,强调的是个体的共性以及据此形成的群体,影响群体关系的私人性往往遭到蔑视与打压。汉娜·阿仑特认为:“在隐私领域尚未被发现以前,私人性的特点之一是,人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作为动物种类的一个标本(即作为种的人类)而存在于这个领域中。这正是古人对私人性表示极大蔑视的终极原因”。
《听漏》《蟠虺》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都市武汉,总体属于现代社会、“物的依赖性”时代,但是仍带有并不稀薄的传统色彩。在叙事空间上,这种传统性的表现正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高度融合。以《听漏》为例,小说中所出现的主要物理空间有水务局收藏室、相忘湖茶吧、马跃之家、六十四路双层巴士、十三街坊等,这些空间均有较显著的公私融合的特点。以前三者为例。水务局收藏室本隶属水务局,是一个公共场域,但它又带有几分副局长陆少林的私人色彩,这里三分之一的藏品是陆少林的收藏,其中就有与陆少林身上的文身纹样一致的青铜残片;同时马跃之正是在这里将青铜残片拼合,找到了自己从未谋面的龙凤双胞胎儿女陆少林与梅玉帛。相湖忘茶吧是一个公共场所,楚学院和博物馆工作人员曾在这里茶叙,它也是柳琴与马跃之夫妇以及柳琴与曾小安这对忘年闺蜜闲聊的私人空间。马跃之张家湾小区的家是他与温柔贤妻柳琴的私人空间,同时马跃之也将自己的工作场所延伸到家中,比如每天下班回家他都要在书房中修补《楚湫时地记》,使得这个私人场域又楔入公共空间。
《蟠虺》中所涉及的众多空间同样表现出浓厚的私人性与公共性缠绕的特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楚学院与曾本之的家。楚学院作为从事文物研究的事业单位,毫无疑问是一个公共空间。但在这个空间中,重要人物曾本之、郝嘉、郑雄、郝文章都并不以单纯的“公家人”身份呈现。曾本之与郑雄、郝文章是师徒,还是翁婿,郑雄与郝文章是同事,更是情敌,郝嘉与郝文章是前后同事,还是有血缘关系的父子,以上关系(尤其是翁婿、情敌、父子关系)都表现了他们在楚学院这个公共空间中无法摆脱的私人性存在。因此,小说中所呈现的楚学院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同体共在。更能说明楚学院作为公共空间的私人性的事例,是曾小安与郝文章在此相恋,并在郝文章的办公室孕育了爱情结晶。曾本之的家本是一个私人空间,但这里又有挥之不去的与考古事业相关的公共性。除了曾本之将青铜研究从单位延伸到家中的书房的公共空间,他的前后女婿郑雄、郝文章也曾在这里居留,这就更加加重了这个私人空间中以考古事业面目呈现的公共性。
《蟠虺》《听漏》所书写的主要地域是21世纪初的武汉,是现代都市空间,现代社会空间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分离,而两部作品所呈现的诸多具体空间却恰好相反,表现为公、私空间的叠合、融合,这表明作家在此更为关注这个现代都市空间的传统性的一面,同时作家的这种书写也验证了总体上呈现为现代性的空间中无法磨灭的传统性。
关注传统的正向书写
无论是代际层面的父业子承也好,还是空间层面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重叠、融合也好,《蟠虺》《听漏》都呈现出浓重的传统品格,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作家刘醒龙对自己所居住的武汉这座城市的一种体验与认知,这恰好与诸多武汉作家笔下的武汉叙事形成了区分,造就出刘醒龙小说中武汉城市形象的独特性。
另一方面,将刘醒龙的这种传统书写置于当下文坛中,也可以发现其独到性,即《蟠虺》《听漏》所书写的传统多以美、善、雅的面目呈现,是典型的对传统的正向书写。这令人联想到的同样来自乡村、眷念传统的贾平凹。贾平凹小说中所书写的西安也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但那种传统多以破败、残缺、丑陋的面目呈现。刘醒龙与迟子建较为接近,倾向于书写以美善面目呈现的传统,但迟子建的传统书写是针对大兴安岭和北极村故乡而言,在城市书写中并不突显。

(喻晓薇,武汉轻工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
(来源:极目新闻)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