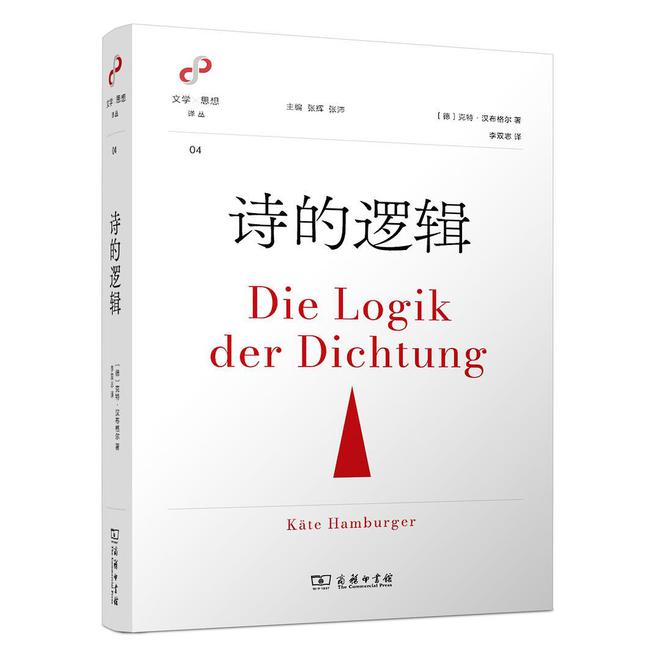
《诗的逻辑》
作者:(德)克特·汉布格尔
译者:李双志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5年4月
大约十年前,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德语系做博士后研究,每天都要去德语系所在的一幢淡黄色四层小楼。途中会经过树荫笼罩的大片草地,各式或新潮或古朴的院系楼宇点缀其间。在某个岔路口,抬头可见一块白底黑字的路牌,上面写着“克特·汉布格尔路”(Käte-Hamburger-Weg)。
在这座拥有近三百年历史,四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校友的德国顶尖学府里,能获得一条道路的冠名权的,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其实,不只是哥廷根大学以这种方式向这位学者致敬。德国教育科研部在2007年启动了人文学科的国家级特别资助计划,就以克特·汉布格尔为之命名,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6个克特·汉布格尔研究所。德国的思想天空群星闪耀,一代代名家大师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当代的国家重大人文建设项目,偏偏选了如此一位似乎少有人知的学者作为标签。这位克特·汉布格尔到底是谁?她有何成就能让今天的德国学术界和政界如此推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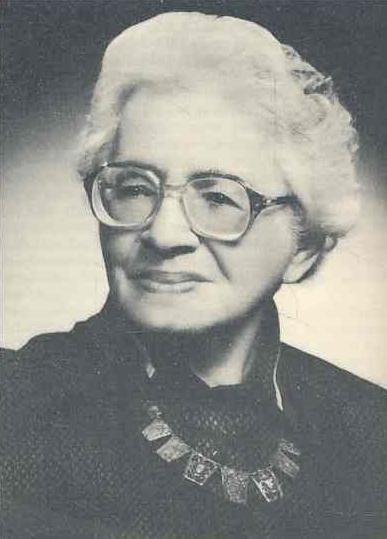
克特·汉布格尔(Käte Hamburger,1896—1992),德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哲学家,斯图加特大学的教授,对托马斯·曼、里尔克等作家有精深研究。代表作《诗的逻辑》奠定了其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声誉。
克特·汉布格尔是谁?
1896年9月21日,克特·汉布格尔出生在汉堡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中。但她和瓦尔特·本雅明等众多德国犹太中产阶级的后代一样,对本家族的商业营生毫无兴趣,而是热心于文学阅读和文学研究。1917年完成中学学业之后,她先后在柏林和慕尼黑学习了哲学、艺术史和文学史。1922年,她以一篇关于席勒的哲学论文获得了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作为犹太女性,她在当时的德国高校难以觅得教职,所以她先在汉堡经营书店,之后迁至柏林,以自由学者的身份继续从事文学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在1932年结识了著名作家托马斯·曼,从此以后与他保持了终生通信。她也成为德国最早研究托马斯·曼的专家之一,在漫长的学者生涯里为这位作家的伟大作品写下了多篇丰富、细致、深刻的专业解读。
1933年希特勒掌权德国,建立纳粹极权统治。1934年,汉布格尔流亡法国,随后又移居瑞典的哥德堡。她在瑞典一边从事语言教师和文化记者的工作,一边继续撰写文学研究的文章。1956年,她才回到联邦德国,在斯图加特落脚。1957年,她以《诗的逻辑》这本专著通过了教授资格评定的考试。但遗憾的是,直到1976年退休,她都没有得到正式的教授席位,而是一直作为编外教授在斯图加特理工大学比较文学系教书、写作。她对德语文学的经典作家如歌德、海涅、里尔克和其他欧洲文学名家如安徒生、易卜生都有精深的研究和著述。同时,她继续在文学理论领域笔耕不辍,贡献了许多颇具原创性的思考。1966年,她以其杰出的文化成就获得了联邦德国的大十字勋章。1989年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给她颁发了席勒纪念奖。1992年4月8日,她在斯图加特走完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之路,与世长辞。斯图加特大学在她过世后,专门设立了研究工作室,收集汉布格尔发表过的所有作品并在线上出版,让这位伟大学者的学术财富能继续泽被后代学人。
克特·汉布格尔在文学研究上的卓越功绩和国际盛誉,都奠基于她在1957年发表的这部文学理论名作《诗的逻辑》。1968年汉布格尔自己对首版进行了较大修订,推出了第二版。随后该书两次再版。1973年这部著作被译为英语,1993年再版,1986年被译为法语,在国际文学研究界引起了广泛反响,之后还被译入西班牙语、斯洛文尼亚语、韩语等众多语言,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国际学术经典。汉布格尔也凭借此书成为了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德国文学理论新潮中的关键人物,与叙事学理论家艾尔伯特·莱姆特(Eberhardt Lämmert)和弗兰茨·卡尔·施坦策尔并列为德语版“新批评”派的核心代表。这部著作以当时整个西方文学理论界的文学本体论转向为背景,富于独特的理论创见和细密的文本分析,为 20 世纪的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学术路径,尤其对蓄势待发的叙事学和文学虚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了解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不可绕过的一座学术里程碑。
从语言理论切入文学本体论
关于“何为文学”这一基础性问题,从古至今,论述纷争不断。在现代学术版图上,20世纪初的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率先拉开了一场文学本体论研究的序幕。他们反对以作者生平、社会背景、哲学或心理学等文学外部因素来研究文学作品,强调文学作品本身的独立性,要求文学研究者以作品内部的语言结构等形式特征为对象,着重考察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尤其是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认为与日常语言相比发生了变异的语言,才是文学性产生的关键所在。在英美两国发展出的“新批评”与之遥相呼应,同样关注作品本身,要求回归文学本体,倡导文本细读,尤其要求淡化作者意图而关注作品本身的语言现象,包括词义、语境、隐喻等。
“新批评”作为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流派,影响延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而在当时的德国文学研究界,正处于一个重新出发的零点时刻(Nullstunde)。20世纪30年代以来,纳粹德国所主导的学术意识形态化,让文学研究在十多年间丧失了独立地位而服务于政治宣传,渗透了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教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高度政治化的学界迅速转弯,走上了去政治化道路。文学研究回归文本本身,将文学作品从政治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文本内部的语言结构及形式特征开始成为研究重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的文学研究开启了自己的形式主义文学本体论时代,和“新批评”的学术主张多有相似,对俄罗斯及布拉格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也多有继承。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气候中,汉布格尔以《诗的逻辑》为这一场重大的研究范式转换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她同样是从语言的角度探究文学之为文学的根基所在,这里的逻辑指向的正是语言的逻辑。不过,她首先将自己的这种研究路径与传统的德国美学划清界限,她觉得黑格尔美学以来的文学界定都太过模糊,而且往往诉诸主观体验,或者陷入循环论证之中(“我觉得这种语言是文学的语言,因为我知道我是在阅读文学,而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是因为采用了文学的语言”)。她和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现象学文学研究的关系也很微妙。尤其是著名文学理论家罗曼·英伽登从胡塞尔现象学借来的意向性对象概念及准判断概念,在她看来依然无法彻底说清楚文学语言如何有别于日常语言,文学描述出的世界如何有别于现实世界。
汉布格尔自己则试图从根本上重建一套语言理论,然后再梳理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学是以语言为材料的艺术创作,它之所以如此难界定,正因为它所采用的语言材料也是日常言说的媒介。一旦作家开始采用这种语言媒介,势必要牵涉语言中已然包含的现实信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因而难解难分。虽然俄罗斯—布拉格学派已经用“陌生化”概念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进行了区分,但是汉布格尔显然并不满于这个仍显虚泛的概念工具,而希望打造一套更客观、更精细的测试装备,用来核定文学语言(她坚持使用“用于文学的语言”这个略显繁琐的表达,因为她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完全隔绝于日常语言的文学语言)的本质所在。
她首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将传统上翻译为“摹仿”的μίμησις /mimesis与ποίησις /poiesis联系起来,从而给这个西方诗学的核心概念一个新的解释:与“制造”相关的“演示”而非“再现”。于是她从根源上排除了文学摹仿论,但也着重指明了文学与现实存在一定的映射关系,文学以现实材料来创造非现实,演示的过程已经让现实材料脱离了现实世界。
然后她又为日常语言的表意功能找到了一个语言理论的锚点,这便是德语中的“表述”这个词。这是汉布格尔的一个极大的理论创新之处。她将大家习以为常的语言基本结构进行了细致的分类考辨,并推出了如下结论:语言就是一个表述系统,表述是一种主客体结构,一切表述都是现实表述。汉布格尔的语言理论并不是简单的语言学,更偏向于存在主义的语言思考。它所认定的表述不是陈述句,也即主谓结构中的“S是P”,而是包括了疑问句、祈使句的一种普遍性的语言模式:某人(表述主体)就某物(表述客体)说出了什么(被表述者)。如此一来,现实世界通过语言媒介,整个都进入了这样的主客结构。
汉布格尔之所以大费周章地阐述她独创的这套表述理论,是为了建立一个参照系,以展开她的“诗的逻辑”。她要说明的,正是文学叙事如何在沿用这种表述结构的同时又发生了偏离,从而产生了可以客观把握到的一些语言特征,以此为据才可判定文学之为文学。为此,她一方面从自己广博的阅读经验里取出了大量的现当代文学实例,另一方面沿着传统的文类范畴,也即史诗—戏剧—抒情诗的三分法,一步步推进她的文学观测。
从史诗到电影的虚构叙事法则
汉布格尔首先将包括小说在内的史诗和戏剧归于虚构类文体,而将抒情诗与前两者区分开来。她对史诗,也即包含小说在内的叙事文体的分析,显然最为用心。这也是因为这个文类尤其能体现文学不同于非文学体系的语言特征,用汉布格尔自己的话说,“只有在叙事文学这里才能表明,当语言制造一种虚构体验而非现实体验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
叙事文学中的虚构叙事,已经脱离了表述结构,不再是就某物说出了什么,而是直接制造了某物。这和文学的叙事结构直接相关。汉布格尔在此又制造了一个新术语,即“我”—原点。她借鉴了建立坐标系的数学方法,先确立原点,再从原点出发来观察叙事角度。虚构叙事之所以不是现实表述,恰恰因为前者的“我”—原点不再是现实中的表述主体,而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而与之相应,汉布格尔认为她发现了虚构叙事的三大语言标志:不再指示过去的史诗类过去时;体验直述也即后世叙事学讨论的自由间接文体;以虚构人物为原点的空间指示词。
汉布格尔的一个经常被后人引用的经典例子是用过去式所写的这句话:“明天就是圣诞节了。”(Morgen war Weihnachten.)指向未来的时间副词可以与过去时连用,这在现实表述中是不可能的。而这意味着,这里的过去时已经失去了现实语言中的时间标示功能。虚构叙事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也便制造了一种伪现实,引导读者去体验一种当下感,同时也让他清楚地知道这种当下感是虚构的。体验直述同样如此,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听到的他人心声,在文学虚构中却被直接写了出来。体验直述因而更鲜明地体现了文学叙事是在“演示”而不是在“表述”。空间指示则时刻提醒读者,叙事角度不是从作者或者读者端发出,而是从人物端发出的。最后,汉布格尔还指出,虚构叙事的功能是波动状的,也即不同的叙事模式如体验直述或对话,可以在叙事进程中自由切换,读者并不会感觉到异样。相反,这种切换是常态,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叙事的虚构性。
汉布格尔在此已经确立了一套建立在确凿的语言证据上的虚构论。对文学语言的缥缈悬浮的感悟式言说被清晰明朗的分析式观察所取代。因此后世往往认为汉布格尔这部《诗的逻辑》代表了一种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倾向。
从最明显的叙事文体出发,汉布格尔又先后对戏剧和电影中的虚构叙事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论述。戏剧让词化为人物构型,又让人物构型化为词。而虚构的语言特征就转移到了人物身上。虽然人物的演绎更让人产生摹仿现实的错觉,但是在现实表述中无法达成的时空指示,依然表明了戏剧的文学虚构本质。汉布格尔对电影的关注,可谓是后世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先驱。她认为电影兼有戏剧史诗化和史诗戏剧化的特征。摄影技术造就了活动的画面,而这活动的画面担负起了叙事功能,让我们从现实的体验域进入功能化的象征域。所以戏剧和电影虽然不如小说那么精准地展示了语言的演示功能,但它们也都是在创造非现实。
如果说对于叙事文体和表演艺术,汉布格尔贡献了极为精彩的语言理论分析,那么在抒情诗上,她就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虚构论,部分地返回了诗的传统解释中。她认为抒情诗不是虚构,而是现实表述,诗中之我也是一个现实的表述主体。恰恰是被人看作最具文学性的抒情诗,在此似乎回归了日常的表述体系,而与虚构叙事的文学特质泾渭分明。然而,汉布格尔随即杀了个回马枪,如此解释道,抒情诗的主体并没有制造任何非现实,但是它将表述客体的客观现实改造成了主体的体验现实,于是也让表述脱离了现实关联。这也符合她对自己的文学本体论的理解:她不是从审美意义上来考察文学,而仅仅是关注文学所用语言和普通语言体系分离的不同程度。只不过,她在此已经和俄罗斯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分道扬镳了。抒情诗作为特殊的现实表述,远不如虚构文体更能展示文学的语言特征。
最后,汉布格尔还讨论了虚构文体的异类,即她所称的“我”—叙事和抒情诗的异类,即叙事谣曲。她将两者都视为伪现实表述。她试图以此来补全自己所构造的一整个文学谱系:按照与现实表述的远近关系,虚构叙事文体也即史诗类、戏剧和电影类在最远处,而抒情诗在最近处,之间的地带则是看似抒情诗的叙事谣曲和看上去不似虚构的“我”—叙事。
原文作者/李双志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