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部他人纪事诗
——《续补藏书纪事诗笺证》前言
文 | 王学雷
王謇先生少年时从苏州名宿沈绥郑(修)习考据,继列黄摩西(人)、金松岑(天翮)、章太炎(炳麟)、吴瞿安(梅)诸大师门下受国故。一生治学兴趣广泛,又勤于著述,惜生前仅出版有《宋平江城坊考》《盐铁论札记》两种,其余著述多未刊行。先生的《续补藏书纪事诗》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经友人整理油印才得以问世的一部作品,在近五十年来的藏书界及近世藏书文化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影响。
《续补藏书纪事诗》油印本行世之后,数量上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产生了各种版本,但包括油印本在内的各版本都存在着许多问题,可以说《续补藏书纪事诗》迄无善本。因此,我在2013年秋下决心对其重加整理,主要着力于校勘和笺证两个方面,同时留意此书的写作经过。
一
自叶昌炽创《藏书纪事诗》后,继踵者不绝,以“藏书纪事诗”为名的著述,或存或亡,名目盖不下十种,体例上亦率多依仿。《续补藏书纪事诗》体例依仿叶书,内容则继有补充,其油印本扉页上有洪驾时先生所写的一则《引言》:
吴县王佩诤謇,博学多才。家有澥粟楼,藏书甚富,又好著述,尝辑《宋平江城坊考》传世。读叶鞠裳昌炽《藏书纪事诗》后,依其体续补一百二十余首,为其晚年未定稿。今集资付印,供研究藏书源流之参考云。
其中“依其体续补”五个字,即是对此书体例内容最为精练的概括,故常为论者所引用。如陈声聪先生谓:“王佩诤(謇)……《续补藏书纪事诗》一百二十余首,盖续叶鞠裳之作也。”(《兼于阁诗话》卷四“澥粟楼藏书纪事诗”)郑逸梅先生谓:“吴中王佩诤赓续叶鞠裳的《藏书纪事诗》成《续补藏书纪事诗》,凡一百二十余首。”(《文苑花絮·几种油印书册》)周退密、宋路霞先生谓:“读叶鞠裳(昌炽)《藏书纪事诗》而善之,依其体例作藏书纪事诗一百二十余首。”(《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
关于《续补藏书纪事诗》的写作起因,王謇先生在书中的“伦明”诗传中有一段夫子自道:
(伦明)因见叶鞠裳(昌炽)《藏书纪事诗》尚有可续补者,乃作《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载天津《正风》杂志。拙诗之作,盖由先生启之也。
后来周退密先生却据此认为,《续补藏书纪事诗》所“续补”的对象是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而非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他在跋文中写道:
余读集内伦哲如明一条,自谓续补之作,实受伦氏所作之《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之启发而作,是伦氏续叶著,而先生又续伦氏之作而为此也。一书之作渊源有自如此(《杲堂书跋·续补藏书纪事诗》)。
起先我也非常认同这个看似新颖的见解,感到周退老“读书得间”,但经过认真思考,却又觉得“于义未安”。从先生的这段话中,我们只看出《续补藏书纪事诗》的写作是受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启发,而丝毫看不出有“续补”之意。不知周退老如何从中看出了“续”的意思?可能是受了其中伦明见叶书“尚有可续补者”这句话的诱导,想当然地认为《续补藏书纪事诗》则是“又续伦氏之作”了吧。最近获读周生杰先生新著《藏书纪事诗研究》,他在书中就提出了“王书名为《续补藏书纪事诗》,所‘续补’者何”这个问题,通过研究,他所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续补叶书”,而“非为续补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而作”。
说到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这本书,起初并无单行本,而是分期连载于1935、1936两年间吴柳隅主编之《正风》半月刊中。但这个杂志出刊于天津,在当时较为冷僻,南方士人一般不易见到,即连见多识广的周退密先生在多年后仍叹“传布未广,更未一见”(《杲堂书跋·续补藏书纪事诗》)。王謇先生获读此书也不无波折,其友人巢章曾致函说:
《正风》较冷僻,抄手亦不易觅,已托书店及友人留意。倘能买或借得原本,当奉寄或由章写寄。惟恐不获速偿斯愿耳。北地藏书家,章所知有限,恐伦先生多已罗入,姑稍待再写呈(原件书于巢章赠王謇文安邢氏后思适斋红印本《明湖顾曲集》副叶)。
巢章先生是位热心人,他原本想在买到或借到《正风》半月刊后,再将原杂志或抄写稿寄给先生。后来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得知先生比他先见到了《正风》半月刊后,于是又致函说:
幸乞垂示《正风》,此间迄无所得。南中移写,想得其全?伦君之著,亟思一读,想不吝惠假耳?(南中抄写之润如何计算?此书共几许字?所费几何?并乞示及。)(原件朱笔题于巢章转赠王謇的李宏惠编述《说朝鲜与中国关系历史》油印本封面及内封。)
可见当时觅读伦书之不易。类似的情形也见于先生的其他友人间,郑逸梅先生就曾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伦明著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闻曾载某报,我没有看到,仅见叶恭绰的《矩园余墨》附录一部分,非其全豹。幸同乡王佩诤录有完整稿,苏继庼向之借抄,我看到了喜不自胜,再由苏家转录(《文苑花絮·几种油印书册》)。
对于这样一本来之不易的书,先生犹精加抄存,今存先生手订的《澥粟楼书目(中)》中即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册,不分卷,伦明。精抄本”的著录。这个精抄本想必就是郑逸梅“再由苏家转录”的那个底本吧。
但是,作为与叶昌炽同样有着“藏书癖”的同乡后学,王謇先生照理应该“怵他人之我先”,率先继踵《藏书纪事诗》,可他却说“拙诗之作,盖由先生启之也”,自居于伦书之后。这是出于何种原因?似有必要作些解答:“藏书纪事诗”这种体裁的作品以记人记事为主,这就需要作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学识,而且还要具有较丰富的人生阅历。叶昌炽当然无愧于这样的作者,其书收录五代至清末的藏书家有1100余人,虽然有人指出其中仍有遗漏,但各时代的重要人物基本被网罗在内,尤其是其中收录的晚清人物事迹大多为其亲历亲接,无论在学识还是阅历上都有丰厚的铺垫。这就对后来的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再大量地重复叶书中的人物内容,已然失去了意义,后来的作者唯有通过自身的学识和阅历,采用“补”和“续”这两种方式进行写作,方能体现各自的价值。伦书亦不过是“为益数十人”(《自序》)而已,对王謇先生的要求似乎也就不会更低。我们不妨从《藏书纪事诗》早期的版本刊刻时间来看王謇先生与它的关系:此书的初刻本完成于1898年,收录在叶氏门人江标所辑的《灵鹣阁丛书》中,是年王謇先生才十一岁;后来叶氏对初刻本不很满意,1910年又有了家刻本,是年先生也不过二十三岁;约在1931年,苏州文学山房又有翻印本,此时先生已四十四岁。假设先生此时已有“续补”此书之意,但在我看来,按照当时的条件未必能达到理想的境地。先生当时固然在学识上无甚问题,但在人生阅历上却尚待更深广的时空加以延展。先生五十岁以前都生活在苏州,少年时即有博学之誉,且富藏书,学识不可谓不丰,师友切磋,交游亦不可谓不广,然早年病羸,平生足迹不出宁沪一线,交游范围主要还局限于苏州地区,可以说阅历尚未达到深广的程度。若反观其时之伦明,年长先生十岁,写《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时已年近六旬,又常年身居北平,时空阅历自然要比先生来得丰富。因此,他能先于先生著鞭并不令人奇怪,先生的写作受到其启发,成书在后也是理所当然。
先生获读《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但很可能是在五十岁左右。对他而言,伦书与其说是“启发”,倒不如说是“激发”,因缘际会,此时先生的人生进入了成熟期,更迈向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1937年抗战爆发,年末先生避寇沪上,任各大学教授。虽僻处孤岛,仍专心治学,此时也可以说是他学术上迈入了“井喷期”。五十年的苏州生活是梦影前尘,却颇堪回顾。寓沪后,不光许多吴门旧雨纷至沓来,更结识到了许多沪上新知,人生阅历也就这么积攒了起来,加上伦书的“激发”,先生着手写作《续补藏书纪事诗》从此提上了日程。
二
有趣的是,其实先生早先确实也曾怀有“又续伦氏之作”的意思,但未曾特别加以明说。《续补藏书纪事诗》不仅频繁易稿,而且有三度易名的情况,则未必为学界所知。一是《续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此名见于先生遗藏《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续)》钞本所附的三叶稿纸,上有先生所写的“冒广生”父子诗传,标题作“续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下署“碧山旧庐著书之一”。二是《三续藏书纪事诗》——此名见于先生手订的《澥粟楼书目(中)》中:“《三续藏书纪事诗》三卷三册。佩诤自撰稿本。”另还见于苏州博物馆藏《江左石刻文编》钞本中先生写有“王则先”诗传的一份手书散叶,作标题“三续藏书纪事诗之一”。三是《再补续藏书纪事诗》——此名见于下文要提及的清稿本“伦明”诗传中“拙著《再补续藏书纪事诗》,盖由先生启之也”。
第一个名称《续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顾名思义就是“续”伦书;第二个名为《三续藏书纪事诗》,似可这么理解,如果叶书算作“一”,伦书自是“二”,那么此书称为“三续”,亦表明所接续的是伦书;由此再论第三个名称《再补续藏书纪事诗》,“再补”就是“又补”,对象是《续藏书纪事诗》,这个“续”自然是指接续叶书的伦书。总之,这三个名称指向的都是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应无问题。问题是,为何最终定名为《续补藏书纪事诗》?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从读者的认知角度考虑,《三续藏书纪事诗》和《再补续藏书纪事诗》这两个名称都不太清晰,尤其对一般的读者而言更不易理解,如果不知有前面两种书,则所“续”为何,就很难弄明白;其次我感到应与先生后来所处时势境遇有关,因为此书的写作一直持续到1949年以后,书中有不少是20世纪50年代才有的表述。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有其时代的进步性,但依然是旧国民政府的象征,书中的许多人物则又都进入了新政权所缔造的新时代。如果书名仍以“辛亥”,尤其是以“续辛亥”来冠名,自然就不再契合新时代的语境。所以,先生改用“续补”这个通用的词汇来命名,是其采用的一种与时代语境不相违背的手法。这样做不仅可摆脱原来所处时代的限定,契合当下的时代语境,更突显了“依其体续补”《藏书纪事诗》的这个主旨。
据现有资料来看,王謇先生撰写此书的过程并不短暂。如从1937年先生五十岁算起,到书中提及的郑振铎1958年“奉使国外,飞机失事焚殁”,以及徐恕1959年“殁后,其子遵遗志全部捐献”,再到1969年先生八十二岁逝世为止,至少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可以说是贯穿了先生从中年到晚年这三分之一强的生命历程。陈君隐先生曾有诗咏此书:“澥粟主人何太痴,长将结发市书皮。到头赢得名无传,半部他人纪事诗。”(见于《学海丛书》本卷首题解)《续补藏书纪事诗》尽管没有经先生本人最终定稿,但这“半部他人纪事诗”对近代藏书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三
《续补藏书纪事诗》得以问世,自然应该提到洪驾时先生。洪驾时(1906—1986),字介如,浙江慈溪人,久居苏州佛兰巷,因颜所居曰佛兰草堂。早年与王謇先生同事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一生以抄书为乐,尤其抄写保存苏州地方文献不遗余力。晚岁居沪,就职于上海自行车厂,仍利用业余时间为公私藏家抄写了大量书籍。他曾为王謇先生无偿抄写过许多古籍,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就有记述,交情并不一般。
《三续藏书纪事诗》和《续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稿本今不知流落何许,但现在仍能见到由洪驾时先生手抄的两种《续补藏书纪事诗》清稿本。这对了解该书的写作过程大有帮助:
第一种原存先祖母处,先祖母2002年去世后,不知何故与先生的《宋平江城坊考》《书目答问版本疏证》等手稿一同散失在外。后来我在苏州一家旧书店中见到,但索价甚昂,一时犹豫,旋被售去。痛悔不已。杨旭辉君有心,曾据以摘其精要,撰《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清稿本叙录》一文,发表于《语文知识》2009年第4期(以下简称“杨文”),乃能窥得此稿本梗概。此稿本在“2013年泰和嘉成书画·古籍常规拍卖会(二)”中出现,当时仅见书影两页。没有料到的是,在2020年10月17日,又现身于泰和嘉成拍卖公司的艺术品拍卖会上,并幸运地为我拍得。在获得此稿本后,即与杨文的描述和部分摘录的文字进行对勘,并未发现有特别的差异,基本可认定即是那本从先祖母处逸出者。我们称作“清稿本”。该本捻装一册,协进源500字绿格稿纸蓝墨水钢笔缮写,每半叶10行,行25字,65个折叶。内容分为四卷,卷前未单列目录,目录写在前四叶眉端,从“丁士涵”起至“缺名氏”止,但顺序与正文不侔。卷首书名下署“流碧精舍海上丛著之一”。正文卷一从“沈锡胙”起至“伦明”止;卷二从“王其毅”起至“袁思亮”止;卷三从“汪之昌”起至“姚方羊”止;卷四从“翁同龢”起至“黄裳”止。诗顶格写28字占两行,诗传另起低一格写自然分行,行24字,小字占半行。正文人名上多数标有阿拉伯数字序号,有的人名序号改动两到三次,应该是为以后制定目录及最终顺序而作的临时性标识。部分人名上写有生卒年及身份,有的还施有浮签加以补充。对稿中的讹误,王謇先生作有不少更定。
第二种清稿本为友人卜若愚君所藏。为避免混淆,此本我们称作“洪本”。该本线装一册,中华书局560字绿格稿纸蓝墨水钢笔缮写,每半叶13行,行25字,47个折叶。不分卷,卷前有《目次》,上下分四列,从“丁士涵”起至“缺名氏”止,录139人。顺序与清稿本眉端所列目录基本一致。人名下面圈有与正文相对应的页码。卷首书名下署“流碧精舍海上丛著之一”。正文诗顶格写28字占两行,诗传另起低一格写自然分行,行24字,小字占半行。其中“徐绍桢”“范祥雍”两诗传为后加浮签,分别粘于“马一浮”“程守中”诗传眉端。全稿施有断句,然破句甚多,殊不足据。
通过对两个本子的对勘发现,清稿本较洪本为早,洪本虽然较晚,但人数上却不及清稿本多。如秦更年、袁思亮(附叶启勋、叶启发)、曹元弼、罗振玉、吴庠、伦明、姚方羊、徐恕、黄裳11人未见于洪本,而清稿本后来作了增补;洪本文字上的讹脱,在清稿本中大多予以更正,而清稿本中的补充文字则未见于洪本。如沈维钧诗传,洪本作“曾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又主持皖中书库”,清稿本原同,但后来改作“历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干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教授”;又“楚考烈王寿春大库所谓‘李三孤堆’者发掘后,迭出古器,君避寇寓皖,泥细拔金钗以易古物而归诸公库”,清稿本原同,后来改作“楚考烈王寿春大库所谓‘李三孤堆’者发掘后,迭出古物,君曾至皖北,购得楚铜器数件而以捐献公库”;再如“近年,吴中沧浪亭书库迁拙政园,君任典藏编目”,清稿本原同,后改为“革新后,吴中沧浪亭书库迁拙政园,君主典藏编目。苏州文管会成立,又聘君为专职委员”。这样的改动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一一例举。
这两个清稿本都是洪驾时先生抄写的,可见他对《续补藏书纪事诗》的撰写与流传之功诚不可没。
在清稿本“伦明”诗传最后,王謇先生缀有这样一句话,“拙著则并未刊行也,一俟修正问世,当先以油印试之”,说明先生曾有油印流布《续补藏书纪事诗》的打算,可是这一愿望在其生前没能实现。幸运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洪驾时先生亲自整理缮写,并鸠集同人故交集资将《续补藏书纪事诗》油印了出来,这个油印本从此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各种通行版本的“祖本”,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兹将其情况略述如下:油印本不分卷一册。玉扣纸线装,浅红色封面,隶书题签(应为蒋吟秋所题)。扉页有《引言》一则。卷前为《藏书家姓名》(即目录),分上中下三栏排列。卷首书名下署“流碧精舍海上丛著之一 古吴王佩诤謇著”。全书40叶,每半叶11行,诗占28字,诗传另起低一格写自然分行,行29字,小字占半行。
如果与清稿本进行比较,油印本体例上与之有着明显的差异,显示出清稿本较多地保存了《续补藏书纪事诗》的原始面貌,油印本则是经过精心编次而成:如清稿本每卷人名上都标有阿拉伯数字序号,油印本去除了这些无甚必要的临时性标识;从两个本子的人名排列顺序上看,清稿本虽然分卷,但人名排列次序却是十分颠倒紊乱的,并不能看出他们之间在生平、身份上有何关联和相似。就以其中所载人物的时代和年龄论,周中孚(1768)年齿最高,置于全书的第78位,而瞿凤起(1908)年齿较弱,却置于全书的第二位。同样的情况亦普遍存在于其他各卷中。相比之下,油印本虽不分卷,但人名顺序则经过了精心斟酌整理,先是按王謇先生五位业师的年龄先后顺序进行了排列:第一位沈修(1862);第二位黄人(1866);第三位章炳麟(1869);第四位金天翮(1873);第五位吴梅(1884)。其后再按人物年龄时代顺序排列,从年齿最长的周中孚始,继则翁同龢(1830)、李慈铭(1830)、汪鸣銮(1839)等。虽然后面人物先后顺序偶有倒错的现象,但大体上还是遵循着以年齿为序的体例。油印本将五位业师排在最前,是出于王謇先生的授意,还是洪驾时先生在后来整理过程中产生的想法,一时无法判断,但不失为一种符合情理的排列。
油印本与清稿本载录的人数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油印本载录126人,附录19人,总计145人。清稿本载录133人,附录23人,总计156人,较油印本多出费采霞、周越然、罗尔纲、周树人、阿英、朱仰周、姚君素、赵元芳、吴颂平、王镂冰、黄裳11人。
油印本与清稿本中用语称谓上的差异也颇值得一说。时间称谓上,清稿本凡是以干支纪年或民国纪年的地方,油印本一律改作公元纪年。如“改制丙辰归道山”改“一九一六年归道山”、“癸丑之役”改“一九一三年之役”;凡是表示抗日战争的干支“丁丑”,油印本一律改称“抗战”。他如“改制”一律改称“辛亥”,而“革新”一律改称“解放”;地名机构称谓上,清稿本“海上”“春申江”,油印本一律改称“上海”。他如学校,大学清稿本称某庠,如“吴东庄大庠”改称“东吴大学”、“辅仁大庠”改称“辅仁大学”。中学清稿本多称学舍,如“瑞云学舍”改称“振华女学”、“龙华学舍”改称“南洋中学”。图书馆清稿本皆称为“书库”,油印本则悉改称“图书馆”,如“海上市书库”改称“上海图书馆”、“武林书库”改称“浙江省图书馆”;人称上,清稿本与油印本之间的差异就更多了。另如“辞世”称“涅槃”、“谢世”称“颓坏”等等,不一而足。
对同一人物生平事迹的记载和表述上,油印本与清稿本的差异亦所在多有。除了一些语意晦涩或是繁复拖沓的词句被油印本删除,清稿本中一些涉及当时还健在人物的评价和事迹,因碍于时代或人情,在油印本中遭到刊落或改写。此类例子甚多,在此不便列举。
前面已经指出,《续补藏书纪事诗》的最终定名,应与先生后来所处时势境遇有关。同理,从以上清稿本到油印本的变化,尤其是用语称谓和人物生平事迹的记载和表述上的明显变化,更显示出与时势境遇的紧密关联。
对于清稿本与油印本的关系,杨文认为“此清稿本乃其祖无疑”,也即是说清稿本是油印本的“所从出”,是油印本的“祖本”。出于谨慎,杨文还判断“油印所据之本是否还有更后的修订稿本,抑或就是此本,尚难定论”。对于它的价值,杨文归纳了以下几点:一“完整条目可补入者”。就中如简又文、罗尔纲、黄裳、朱仰周、姚君素、赵元芳、吴颂平、王镂冰诸人,油印本没有收录,而清稿本却有,可以辑补。二“签条未被补入油印本者”。油印本有收沈修、马一浮,清稿本上于此二人事迹有浮签加以充实,而油印本没有采用。现在看来,似采用为宜。三“叙述史实更详实者”。油印本中虽载有沈锡胙、瞿凤起、陈奇猷、叶承庆、邵章、范祥雍、谢国桢、郑振铎等人,相较清稿本为略,从保存文献的角度也不宜忽视。四“叙事相异可资备考者”。如吴慰祖、程守中、吴庠三人的诗传,清稿本与油印本文字上有较大的差异,值得对比参考。总之,“清稿本可补正通行本者,亦多有之”。
通过对清稿本与洪本的考察,使我们对《续补藏书纪事诗》的写作过程会产生许多新的认识,同时对油印本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油印本毕竟是经过后期加工整理成型的版本,清稿本与洪本虽然很有价值,但并不能取而代之。当然,对油印本的得失还需要进行一番评估,这也是下面我们讨论其后出现的各个版本的起点。
四
油印本的印量通常都不会太大,且非正式出版物,大致仅在当时的藏书界和学术界内部有限地流通,庶几“供不应求”。于是在问世至今不到50年的时间里,《续补藏书纪事诗》就陆续出现了另外几个版本:第一个是1985年北京大学《学海丛书》本。是本的编校者为徐秋禾(雁)先生,他将《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续补藏书纪事诗》《广东藏书纪事诗》《续藏书纪事诗》四种藏书纪事诗加以合刊,总名《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作为《学海丛书》中的第一辑第一种刊行,中文打字机打字油印。其中《续补藏书纪事诗》所用的底本就是油印本。第二个是198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希泌先生点注本。是本所据底本也是油印本,还对正文稍加注释。后面附有潘景郑撰写的《后记》、甘兰经撰写的《王佩诤先生事略》及冯淑文编写的《藏书家姓名笔画索引》;第三个是199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本,点校者为杨琥先生。《续补藏书纪事诗》作为其中的一种,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广东藏书纪事诗》合刊。其所用的底本则是李希泌点注本,并未用到油印本,其中各条目大都作有题解,并对正文间有注释。
这三个版本对《续补藏书纪事诗》的扩大传播确实起了较大的作用,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学海丛书》本扉页有一牌记,称“本册系内部交流版,海内书迷,幸勿翻印,致生误会”,可知亦同油印本一样系非正式出版物,印量也不会很多。还有由于当时物力条件的限制,采用的是中文打字机先在蜡纸上打字,然后再油印,故其中有许多字迹不够清晰,一些无法打出的字形成空格尚待手工填写。况且纸敝墨渝,阅读上并不理想;李希泌点注本和杨琥点校本才是正式出版物,前者印数3300册,后者达到了5000册。现在,油印本和《学海丛书》本已然成为书迷眼中的“珍本秘籍”,精明的书商亦奇货可居,开出的售价更令人咋舌,想要拥有和阅读已十分困难,而点注本和点校本自然就成了现今便于获得和阅读的通行本。然而按照常理来说,后来的整理本在质量上通常都应该“后出转精”,可是我们检核了这两个通行本后,结果却大出意料:李希泌点注本中文字脱误现象十分严重,语意难明之处所在多有。于是将其作为底本的油印本拿来覆校,发现油印本中的讹误不仅几乎为其所承袭,大都未改,却又新出了不少讹误;杨琥的点校本中的讹误则又完全承袭点注本,也同样新出了不少讹误。
为何这两个后出通行的整理本却如此“一反常态”呢?这与整理者的自身业务水平和工作态度不无关系,但客观原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油印本所存在的问题。
整理旧籍,底本是关键,副本、参校本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当时整理《续补藏书纪事诗》并不具备副本和参校本,清稿本自不可见,所据的唯有油印本。整理者依靠自己的学养固然可以纠正其中一部分明显的错误,但总不能做到彻底。据李希泌先生在《前言》中称,他做点注本时所用的底本是谢国桢先生所赠的油印本,后来又借用了潘景郑先生所藏的油印本作为参考。需要指出的是,谢、潘两本无疑是同一个本子,文本上不存在差异,也就表明彼此不具有对勘之价值,形成不了底本与副本的关系,对李希泌先生的整理工作提供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油印本所存在的问题,李希泌先生在《前言》中没有明确地指出,但潘景郑先生在《后记》中似乎就已婉转地指出:“《续补藏书纪事诗》一卷为故友王君佩诤晚岁遗著之一。殁后数年,友人醵资为之印行流传,顾非君精湛之作也。”他认为此书并不“精湛”,大概即暗含有对油印本整理上的不满之意。相比之下,范祥雍先生的批评则显得更加具体,他在致徐雁先生的函中即明确指出了油印本整理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此书系初印本,因当时条件关系,草草完事、急于流通,其中谬讹不少。即以我个人的一首诗而言,有好几个字抄错。初读简直看不懂,经过仔细思考,才知为抄写者所误。”遗憾的是,这些问题没有被李希泌先生意识到,油印本中所存在的错字误句被他的点注本基本“照单全收”了。
洪驾时先生整理刻写《续补藏书纪事诗》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我们对他“草草完事、急于流通”的做法与心情应当表示理解,书中存在的“谬讹不少”也同样应当予以谅解。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油印本中的问题后来不是没有察觉,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问题才得以显示,于是开始纠谬正讹,另行刻写了一份《勘误表》加以弥补。这份《勘误表》有两叶,用订书钉将两纸钉住后折叠,厕于油印本末,而不与原书同装(线装)。表中除补有油印本正文中脱漏的“沈维钧”诗传一则外,勘正误字45处、衍脱34处,若将这些勘误移录至油印本相应的位置,则渐渐可读了。可惜的是这项工作似乎并不为潘景郑、范祥雍、谢国桢等先生所知,原因应该还是出在洪驾时先生“急于流通”的心情上——尤其是潘景郑和范祥雍先生,他们都是王謇先生生前关系密切的好友,与洪驾时先生也应该熟识,这样他们自然是第一批油印本的获赠者。而《勘误表》则是在后来才完成的,或许洪驾时先生没能及时补寄,由于这个时间差,他们的油印本中就没能附上《勘误表》——谢国桢先生的藏本也同样如此。遗憾的是,李希泌先生对此浑然不知——点注本正文中就没有“沈维钧”诗传,仅在目录上标注为“有目无文”,而《勘误表》勘正的其余讹误,自然也不能据改了。
其实徐雁先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他说:“李希泌先生点注本因所据底本字迹漫灭不少,又缺刻写者原附《勘误表》一份,又对于原文未作校订工作,因此此本不善,存有错误130余处。”(徐雁、王燕均主编《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卷上“文献录”)他所指出的130余处错误,应该包括点注本后来新出的错误,由此再进一步论以点注本为底本的杨琥点校本,其问题更可想而知了。
五
以上就《续补藏书纪事诗》各种版本的得失作了较深入的讨论,这里就此书的学术价值与得失也作一些探讨。
王謇先生学问渊博,治学几乎遍及传统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续补藏书纪事诗》仅是其学术的一方面展示。前引潘景郑先生对此书的评价认为“顾非君精湛之作”,一则此书未尽其力,是一部未竟遗稿;另则也未尽其才,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实远非止此。这是基于对先生生平学术有足够的了解,才能说得出来的话。但近十多年来,古旧书籍的收藏蔚然成风,藏书者为提高自己的收藏质量,并且获得有效的指引,除了自身经验的积累,则有赖于对藏书史的了解,于是藏书史研究随之兴盛,尘封多年的各种《藏书纪事诗》也纷纷被挖掘了出来——《续补藏书纪事诗》也不可谓不欣逢其盛。除了上文谈到的版本得失问题,作为一部藏书史著作,《续补藏书纪事诗》在学术价值上当然也是得失互见的,论者也多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了评价。
单方面加以表彰的有郑逸梅先生:
此后,吴中王佩诤继叶昌炽后有《续补藏书纪事诗》,凡一百二十余首,那就涉及我熟稔的朋友,如王蘧常、范祥雍、潘景郑、顾廷龙、瞿凤起、谢国桢、冒鹤亭、顾颉刚、陈乃乾、吴眉孙、王蕖川、金息侯、卢冀野、蒋吟秋、巢章甫、王培荪、王欣夫,又胡石予先师,读了益形亲切(《珍闻与雅玩·书册》)。
还有范军先生:
《续补藏书纪事诗》记录、品评了近现代以江浙沪为中心的一百三十余位藏书家的藏书事迹。虽然此书篇幅不大,但由于所记多为近现代藏书中心地区的藏书家,且书中保留了大量为他书所未见的第一手资料,故颇为人看重〔《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发行史·藏书类》〕。
郑逸梅先生也是王謇先生的故交,他谙熟近世掌故,交游广泛,书中涉及的不少人物也都是他的师长故交,所以此书会使之感到“读了益形亲切”;范军先生则是从保存史料的专业角度,对此书作了正面的评价。
给予肯定和赞赏的同时,对此书略表缺憾的是周退密先生:
此书则网罗东南数省著名藏书家甚备,其博闻强记实足惊人,殆非旁搜远绍、周咨博访、勤于笔札、积以岁月,不能成此也。然吾四明藏书家如冯氏之伏跗室、孙氏之蜗寄庐、赵氏之潜防阁、朱氏之别宥斋,竟未一字及之,不亦失之眉睫乎?读其书如揖老辈而闻数家珍,大开见闻。诗亦清劲,笔底澜翻,逞臆而出,刊落浮华,盖纪事诗之上乘也(《杲堂书跋·续补藏书纪事诗》)。
《续补藏书纪事诗》本身就是一部未竟遗稿,周退密先生提到的几位藏书家未见收录,也许有些遗憾,但“盖纪事诗之上乘也”确是很高的评价。
至于缺点,亦毋庸为尊者讳,论者每有揭出,主要有两点较为突出:一是记载疏误和收录人物地域的不平衡。如陈声聪先生指出:
略检颇多疏脱错误处。如“冒疚斋”一条,鹤亭之外祖周季贶之书钞阁藏书,得自福州陈氏带经堂者,曾依中郎仲宣故事,悉以归鹤亭,文中并未一述。其长君孝鲁之夫人为蒲圻贺履之(良朴)女,乃误称陈夫人,实为失检。又陈伯严一条,在清光绪十九年,其父陈右铭官湖北提刑时,借湖北杨惺吾在日本所得宋本《黄山谷内集》及朝鲜活字本外集、别集刊于湖北,越七年始蒇事,散原实董其役。此皆是书林中胜事,亦漏而未说,致此两条空洞无物,不免遗憾(《兼于阁诗话》第四卷)。
徐雁先生指出:
传主详于江浙两省,疏于其它地区。介绍其藏书经历、学术事迹、重要文献聚散存逸状况等,颇富史料价值。作品系其晚年未定稿,著述中疏漏甚多。纪传过于简略,闻见时有讹误(徐雁、王燕均主编《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卷上“文献录”)。
老辈著书多凭记忆,所述往往失实失记,后人不必以今天的学术眼光加以苛责。这些评论只是荦荦大者,书中此类情况往往而有,特别是一些书名经常出现误记,我在整理过程中都已指出。
二是人物收录范围问题。论者主要针对书中将许多一般意义上的文人学者当作藏书家收录了进去,而对有些值得收录的藏书家却有遗漏提出了批评。如范祥雍先生认为:
此书体例较叶氏原书为宽。我们所知的有几位著名藏书家未收,而教授和学者并不爱书者则多滥入。总之……可商榷之处当不少也(致徐雁函)。
所谓“并不爱书者”,应是指并不爱好藏书者,即算不上是藏书家的那些教授学者。黄永年先生同样也说此书:“缺点是有时滥了一点,有的并不以藏书见称的学者也收了进去。”(《古籍版本学》)
与范祥雍先生的意见相似,提出更为具体批评的是周子美先生。他的意见值得单独来说一下。他说:
内中如朱锡梁、胡蕴、沈勤庐诸人或为南社诗人、或为学术名家,向来都不以“藏书家”自命。王佩诤(謇)先生因与之相熟,其收录有若干,不免过宽。……再者王謇先生之诗中收入生存若干,如顾廷龙、瞿凤起等虽然各有收藏,但此例亦不宜开也(致徐雁函)。
周子美先生也是王謇先生生前的好友,作为近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从身份与职业经历上说,他比之所提到的几位“向来都不以‘藏书家’自命”的朱锡梁、胡蕴、沈勤庐诸人,应更该收录到《续补藏书纪事诗》中。惟不知何故王謇先生却将其遗漏?于是他将疑虑转移到“诗中收入生存若干”这个问题上来,举出当时与他一样尚健在的顾廷龙与瞿凤起,认为“此例亦不宜开也”。然则,翻看一下诸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广东藏书纪事诗》和《续藏书纪事诗》几本同体裁著作,收录生存人的例子比比皆是,成例既在,故此例倒不是王謇先生率先开的。惟认为收录“不免过宽”,则与范祥雍先生的观点不约而同。这也说明《续补藏书纪事诗》不仅存在收录范围过宽,又存在遗漏的矛盾现象。
以上对《续补藏书纪事诗》人物收录上的批评确实都是中肯之言,问题可归结为不该遗漏和不该收录两端。然而我却从范军先生“虽然此书篇幅不大,但由于所记多为近现代藏书中心地区的藏书家,且书中保留了大量为他书所未见的第一手资料”这句话中得到一个启示——抛开其中的人物身份不谈,换个更宽阔的角度来看待此书的“不免过宽”“有时滥了一点”等缺点,此书所载的一些原本就缺乏记载的文化人物事迹,却因此得以保存,其不亦善乎?诸伟奇先生有一段综合评论虽然很长,对《续补藏书纪事诗》的价值得失作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不妨繁引参考:
王謇(1888—1969)本人即喜藏书,家有“澥粟楼”,收藏甚富。他的故乡苏州在明清两代藏家辈出,藏书极丰富;他与近代一些学者、藏书家交往甚频。凡此,都为他记述藏书家(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藏书家)积累了优越的条件。故书中所记或亲历或亲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既可视为书城掌故,又可当作近代文化学术稗史笔记来读。书中所记姚子梁、陆鸣冈、林石庐、余心禅、徐恕、黄钧、张炳翔、王其毅、孙毓修等条内容多为他书所未道,其中展列的部分珍本、稿本多为公私书目所未著录。近代中国饱经忧患,近代藏书家也充满着艰辛。当读者读到王胜之的“栩园”藏书“论秤而尽”;顾建勋(引按,原误作“魏建勋”)“燕营巢”的身后萧条;吴庠的“校抄辛苦成底事,换得袁氏头八千”;刘声木的晚境艰窘“欲以书易米,而冷集居多,亦尚少问津者”,以及沈福庭身后的藏书遭遇和藏家间纠葛等处时,虽作者濡墨不浓,但读者依然为之动容,很难当作一般掌故来读。
由于叶著、伦著在前,该书乃“续补”之作,故所收藏书家不多,连附目在内,共一百三十二人。所记详于江浙,而疏于其他地区,且将一些不是藏书家的学者也阑入了,这一部分作为学术史乘看自然有价值,但与“藏书”之名不大相符。由于该书系作者晚年稿本,其中所记难免有失,如“冒广生”条下就将其子冒效鲁夫人贺姓误为陈姓(冒夫人讳翘华,乃清末维新人士贺履之季女,父女皆善丹青);“吴保初”条下记清末四公子为“吴君遂(保初)、丁叔雅(惠康)、陈散原(三立)、罗掞东(惇曧)”,然习惯称法应有谭嗣同而无罗惇曧;“丁惠康”条下指丁(丁日昌、惠康父子)与“瞿、杨、陆并称”“清季藏书四大家”,并责“叶著《藏书纪事诗》于丁氏独抱阙如,可异也”。其实,“清季藏书四大家”,依据藏书数量、质量和影响,习惯上是指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陆氏皕宋楼和丁丙、丁申的八千卷楼。丁氏持静斋虽雄富,然与此四家尚差一头。《藏书纪事诗》于丁丙、丁日昌皆有记述(分别见卷七、卷二),佩翁恐忽略了。另,纪事过简,一些有价值的藏书故实略而未记,陈兼于先生对此已举例说明(《兼于阁诗话》卷四),不赘。(《古籍整理研究丛稿》)
六
不可否认,至今的四个版本确实对《续补藏书纪事诗》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油印本、《学海丛书》本不仅稀见,且未必适宜阅读;点注本、点校本虽然通行易读,却谬误甚多。加之此书写作中本身存在的疏误、遗漏等问题。最后说一下我对此书的整理工作。
潘景郑先生在《后记》中说:“是书传印不多,鲁鱼难免,亦希后贤重为校理。”对当今的读者而言,《续补藏书纪事诗》不仅需要一个近乎完善、可读可用的版本,还需要一个较为专业详细的注释本。因此我在近八年的时间里,主要着力于此书的校勘和笺证两项工作。这是对潘先生的一个交代,也是后人的本分。
李希泌点注本虽然有个“注”字,但注释得实在简略,基本没有反映出注本应有的特色;而杨琥点校本虽然有个“校”字,却是一条校记也没有,反而注上了不少十分浅显、对理解文本并无特别帮助的解释——这两项工作都有必要重做。
我非常认同爱尔兰校勘学家比勒尔的这样一句话:“文本所需清晰解释的程度,随其作者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基本解释工作隐含在校勘确立文本的过程中。”(路德维希·比勒尔《文法学家的技艺:校勘学引论》)因此,我势必将校勘工作放在首位,使《续补藏书纪事诗》尽可能有个可靠的版本。校勘所用的底本当然是带有《勘误表》的油印本。现在由于清稿本的失而复得,无疑成为校勘上最有价值的参考本,尤其是油印本上原本疑莫能明的一些模糊字迹,因此得到了确认;《勘误表》所遗漏及一些讹误,也由此得以更正;尤其是一些事迹,清稿本叙述虽显繁冗,有时却比油印本所述更为明晰。将两者对照参读,必有助益;至于点注本和点校本,它们的校勘价值自然有所降低,但“日思误书,亦是一适”,有时由于它们的某些讹误,反而会引导出正确的观点。它们也是不必尽弃的,无妨参考。我们所采用的具体的方法则不外“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这几种最普通管用的技术。成果则放在脚注中,这里不烦缕述。
至于注释,我非常认同比勒尔的另一句具有指导意义的话:“无所不注(Commentarius perpetuus)的做法已经过时了。一方面,为了教会初学者如何阅读,我们需要一种注;另一方面,为了专家学者讨论文本中不同寻常的难题,我们需要另一种注。”(同上)我对《续补藏书纪事诗》的注释是这样的——在解决了其中的校勘问题后,针对其“文本中不同寻常的难题”,我采用了中国传统解释学中的“笺证”方式。另外,我在情感的投入和资料的拥有上,应该较他人还具有一种“先天的优势”——20世纪80年代初,承蒙顾起潜(廷龙)先生的关照,王謇先生被抄没的大部分遗稿由上海图书馆发还,我对这些稿本善加宝藏,如护头目。在平时的细致阅读中,发现有许多可与本书相印证的资料,用以参稽发覆,每见切当。这些资料大多没有发表过,十分珍贵,自当善加利用;先生师友以及同时代人的著述,我亦尽力搜求研读,收获不少;今贤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增加了我很多识见,避免了闭门造车和误入歧途。程千帆先生曾谦虚地说:“笺记之作,盖欲省读者翻检之劳,事等胥钞,难言著述。”(《史通笺记·凡例》)我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笺证者,深知此道之甘苦。好在杜泽逊先生说过一段暖心的话:“一书的不同注本、评本、选本、类编或系年,均不宜视为重复。因为它们通过再加工,已注入了新的学术成果。”(《四库存目标注·序论上篇》)
2019年正值先生逝世50周年,原本打算趁此机会速付枣梨,怎奈资料层出不穷,漫漫无际,有不知者,有知而不能得者,多方索求,又迁延一载,实属无奈。故于笺证上力求“详细”,非敢言“详尽”也。唯本人学识有限,难免错误,敬祈读者方家不吝指正。
王学雷
2020年7月22日写毕
2025年1月改定于苏州城市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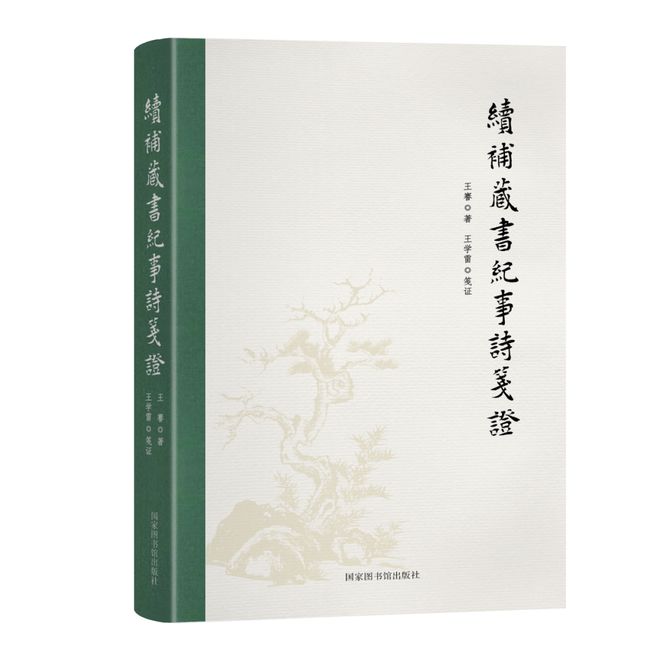
《续补藏书纪事诗笺证》
编著者:王謇著 王学雷笺证
定价:168.00元
装帧开本:精装16开
ISBN:978-7-5013-7176-1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综合编辑室
供稿 | 潘云侠 编辑 | 邓旭欣
监制 | 张颀
审核 | 弘文
点击"阅读原文",到国图出版社官方微店购买;或联系发行部:010-88003146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