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时期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探讨“大众文艺”,再到当今“新大众文艺”如火如荼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辨,文艺大众化是百余年来中国文艺发展的重要甚至主要思潮。历史地看,文艺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大众化过程,总是与媒介载体、科学技术的更新迭代相伴相生。因而,技术演进及其影响,理所应当地成为思考“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此基础上,以更加历史化的眼光、更为宏阔的视角观照,或能发现“新大众文艺”在技术伦理以外更为丰富的内涵。“新大众文艺”不是一个简单的普及或传播命题,而是包含深刻的价值判断、深远的历史向度、深厚的家国情怀。
与帝王将相、富商巨贾的秘辛或仙侠奇幻、神魔穿越的缥缈相比,“新大众文艺”更加“下沉”、更接地气,用一句流行的话讲即更有生活的“实感”。这一特点首先表现为创作队伍的多元化。曾经,文艺创作有一道高高的门槛,文艺作品多出自专业人士之手。而今,这道门槛正在逐渐模糊乃至消失,无数怀有热情、乐于表达的普通人深度参与文艺创作。与之相应,“新大众文艺”的题材内容相当丰富、活泼、亲切。不论“田园博主”视频影像中的山乡气韵,还是“外卖诗人”笔端文字中的市井温情,那些蒸腾着浓烈生活气息的鲜活表达扑面而来,抒发普通人的心声。而直接推动上述一切快速发生发展的,正是新媒体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日益蓬勃。新媒体技术为广大群众参与创作、发表作品提供了便捷可及的渠道,新媒体的社交属性、互动特征让文艺的创作生产、传播接受、欣赏批评趋于一体化,并强调沉浸式、参与感,催生了新的文艺形态、生态与格局。
笔者上述对“新大众文艺”特点的概括相当粗线条,主要是考虑不少论者已经对相关现象做出十分细致的描摹。下一步需要追问的是,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如何在价值维度上为“新大众文艺”寻找到精确的坐标?妥善回答这两个问题,对深入认识分析“新大众文艺”有着重要意义。
不同的理论立场可能对“大众”一词产生不同的理解,在传播学、文化研究等不同学科和领域中,相关的解读层出不穷。我们坚持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大众”并非简单指多数,更不是“平庸的多数”,而是历史的创造者、见证者,是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党的文艺方针、百余年来的文艺大众化思潮,始终致力于剥离附着在大众身上的层层遮蔽,揭示并还原其作为历史主人翁的重要地位,赋予其登场、发声以及被关注、被表现的文化权益,或者说文化权利,“新大众文艺”与此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这一过程借助了媒介技术的力量,但并不以媒介技术本身为旨归。
有人从鲁迅的《伤逝》中读出小油鸡、小狗阿随的价值并不比搞文学、搞翻译更低,那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珍重、对日常价值的重估。“新大众文艺”鼓励广大群众把生活写成诗、绘成画、谱成歌,这样的生活或许平常琐碎、不乏絮叨,但其中真真切切地包含着他们的情感、爱恨、梦想以及冲突、挣扎。当大众带着他们的真挚与质朴,自信地站上文艺舞台的中央,讲述自己的故事、切磋彼此的创作,“新大众文艺”便悄然实现某种历史焦点的切换、某种话语权力的再分配,这是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
一种新文艺现象的出现、一种新文艺范畴的提炼,通常会带来文艺概念边界和现有生态格局的调整。回望五四时期,新观念、新主张的提出,推动曾被认为是“小道”的小说一跃成为重要的、居于主流的文学形式,深度参与彼时的文化生活、社会实践,极大地刷新了中国文学史的关注视域、书写方式和评判尺度,繁荣了中国文学创作。同理,“新大众文艺”必然重新发掘及催生新的文艺样式,有论者称其为“多模态的文本内容和‘泛文艺化’的叙事方式”,颇有眼光。当网络游戏、情景短剧以及更多一时难以用现有概念精确命名的文艺形式不断涌现,越来越多带有审美意蕴、情感内涵和价值追求的新生事物及其创造者,拿到了“文艺”“作者”的入场券,文艺也必将以新的姿态、方式拥抱大众生活,成为某种“百姓日用而不知”。
由此一来,文艺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其影响力、辐射面将获得极大增强。可以说,“新大众文艺”以看似带有一定冲击性、颠覆性的方式,夯实并放大了文艺的重要作用。如果说,百余年前的小说等文学样式借助彼时作为“新媒体”而存在的报刊等形式,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中参与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完成了文艺事业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那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艺尤其是“新大众文艺”亦需挺膺担当,传递温暖、汇聚共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世界读懂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站在这一角度考量,“新大众文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或可进一步显露。
在字里行间表现人、尊重人、关心人,在奋斗路上陪伴人、温暖人、鼓舞人,这是文艺事业的出发点、落脚点。在“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运用更多是一种水到渠成、顺势而为。超越技术与“新大众文艺”之间假定的、机械的、单向度的因果关系,超越传统文艺形式与“新大众文艺”简单二分化的、对峙对抗的视角,超越面对新变化、新趋势时的过度焦虑、傲慢及其背后可能包含着的精英本位意识,以更宏阔平和的眼光穿透文艺现象,不仅注意到发展变化,更注意到发展变化中的那些坚定不移、一以贯之,更利于深化对“新大众文艺”的认识和理解,更利于切实推动“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
2025年7月3日《中国文化报》
第7版刊发特别报道
《“新大众文艺”:从技术描摹到价值确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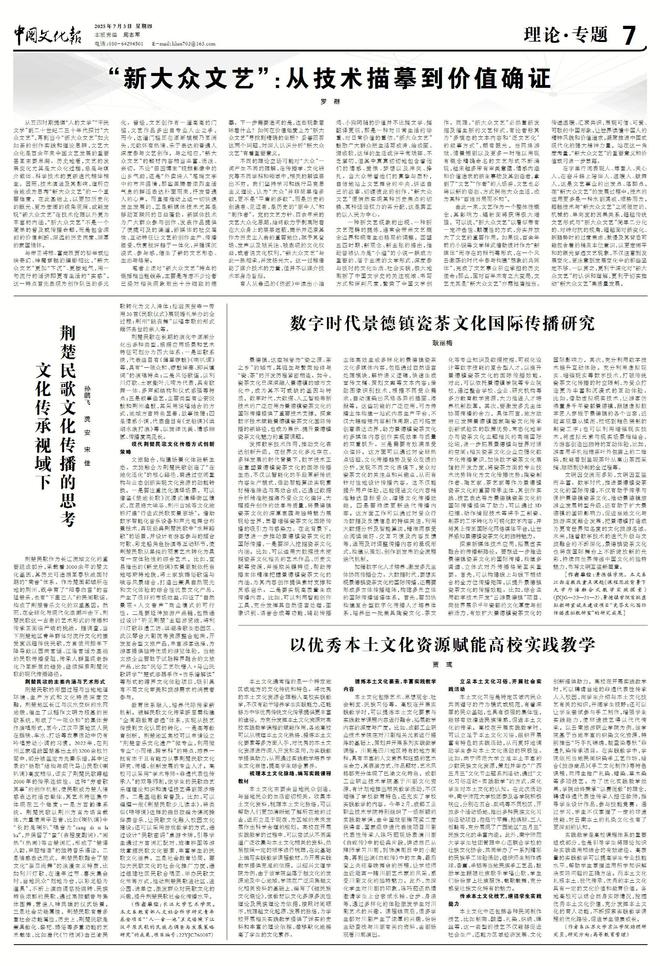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