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红学家周岭说《红楼梦》饭局里的虚虚实实
周岭先生是著名红学家、文化学者,87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自2020年起,年届七旬的他创建了自媒体账号“周岭说红楼梦”,用短视频的形式与网友分享半生研读《红楼梦》的心得,从曹雪芹到脂砚斋、畸笏叟,从高鹗续书到《红楼梦》诸多版本,兼及书中诗词曲赋、节令习俗、服饰器皿、宴饮娱乐各方面,可谓杂学旁收、新见迭出,煞是精彩。这些视频得到了红迷的热烈捧场,也引发了许多真诚的讨论。
迄今为止,“周岭说红楼梦”已更新了三个“百题”系列并多个“数十题”系列。其中,“说饮食”系列视频整理结集为《<红楼梦>中的饭局》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渊深,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贾府的饮食有着生动的刻画,无论惊世骇俗的“茄鲞”,刁钻古怪的“小荷叶儿小莲蓬的汤”,薛姨妈家的糟鹅掌鸭信,还是晴雯爱吃的豆腐皮儿包子,芦雪广现烤的鹿肉,应季的“油盐炒枸杞芽儿”,乃至于小丫头们吃的碧粳米饭、野鸡瓜齑、胭脂鹅脯……尽皆色味俱全,在精细中透着风雅。而为贾家管理田庄的乌进孝交租的单子里,更是飞禽走兽无奇不有,南北风物大开大阖,实打实地铺陈出贵族生活奢靡的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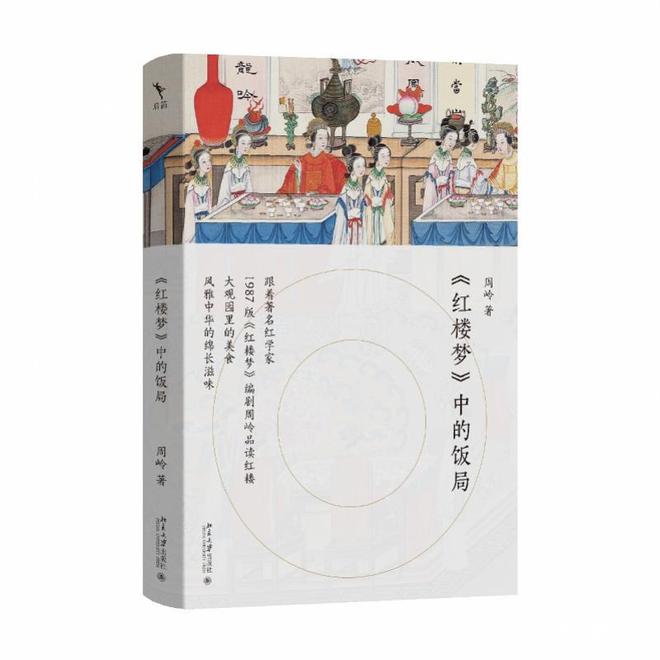
在《<红楼梦>中的饭局》一书中,周岭将红楼美食一一拆解,以庞杂的古代文献为基础,考证虚实,钩沉源流,匡正谬误。他坚持认为,曹雪芹在“家长里短、一饮一馔之中,寓了一些大意思”,即便写菜品、写食材、写宴饮,也贯彻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的哲学精神。例如他提出,让世代红迷心心念念的“茄鲞”,其实是做不出来的一道菜,纯属曹公杜撰。读红楼需别具只眼,才不会为作者的“烟云笔法”所迷惑。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世代流传,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当下一方面红迷甚众,一方面又罕有通读原著者。周岭希望通过《<红楼梦>中的饭局》,以“吃喝玩乐”为切入点,引导读者回到经典,回到原著。
“读这本书是为了助读《红楼梦》,读《红楼梦》是为了读懂中国。”周岭向南都记者表示。
南都专访著名红学家、87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周岭

著名红学家、87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周岭
饮食文化是《红楼梦》里的杂学
南都:《红楼梦》里写衣食住行都特别精彩,尤其是饮食,正如您所说,“家长里短、一饮一馔之中,寓了一些大意思,并且写得极为生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系统研究《红楼梦》里的饮食的?
周岭:红学要给它分类的话,我的意见是把它分成“红外学”和“红内学”。“红外学”就是《红楼梦》文本以外的学问,比如说研究作者曹雪芹,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包括他的生平,《红楼梦》成书的时代背景,《红楼梦》的版本流传情况,这都属于“红外学”,和文本本身的关系不大。“红内学”就是研究文本。现在我们的研究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由于没有什么新的资料发现,“红外学”已是炒冷饭,没什么好说的了。只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乱说、妄说,不叫做学问了。而“红内学”的研究远远不足。就文本而言,对《红楼梦》的人物,《红楼梦》的写作方法,《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的总纲,这些方面的研究文章非常多,但是对《红楼梦》当中的杂学部分研究特别少。只在诗词曲赋领域有一些专著,衣食住行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白。
中国人的服饰,所有的小说没有比《红楼梦》写得更好的,因为曹雪芹家是织造世家,对纺织品、衣服、饰品,从面料到色彩到款式到工艺,熟得不得了,所以《红楼梦》当中的服饰写得是光彩斐然。但这方面有人做专门的研究吗?没有。在《红楼梦大辞典》编写过程当中,我是负责服饰这部分词条撰写的,也就是说,红楼梦的服饰,大概红学家当中只有我一个人在研究。我接下来也要专门把《红楼梦》的服饰写成一本书。
饮食也是相同的情况。《红楼梦》里边写到吃食,写得非常精彩。有虚有实,有成品,有食材,有南有北,有餐有饮,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活动,各种餐茶酒具,太丰富了!而且这方面的描写完全顾及曹雪芹写这本书的宗旨,叫“无朝代年纪可考,无地域邦国可考”,不坐实在某一个朝代,也不坐实在某一个地方。汉唐元明清,东西南北中,都有。服饰是这样,器物是这样,饮食是这样,医药是这样,哲理宗教是这样,建筑也是这样……这是杂学,也是整个小说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不能孤立地看衣食住行,也不能孤立地看一首诗一首词,也不能孤立地看一个建筑。
中国人“民以食为天”,中国是饮食文化方面最有历史也是成就最高的一个国度。孙中山先生把“美食”和“美术”并提。我们历朝历代的文人、大学问家都跟吃有关系,例如苏东坡、白居易。袁枚写《随园食单》,曹雪芹的祖父写《居常饮馔录》。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而且这些文化不仅仅只着眼于吃,从吃可以勾画出芸芸众生的生活。
《红楼梦》也不是为了写吃而写吃,所有的吃都是为了他结构故事、塑造人物服务的。我为什么要写《<红楼梦>中的饭局》这本书?现在虽然喜欢《红楼梦》的人很多,但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认真从头到尾读过原著,关于《红楼梦》知识都从各种各样改编作品来的。
一方面是红迷甚众,另一方面是从头到尾真正读过原著的人很少。这就非常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广大的喜欢《红楼梦》的人去读原著。但是由于时代的隔膜,文化的断裂,好多人觉得大部头啃不动,还不如去听听故事算了。也就是说,改编作品起到的作用肯定是很巨大的,但同时我们要做一些工具方面的,向导方面的工作,使得大家能够读进去。
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从哪一个门都能修成正果。《红楼梦》也一样,你从哪个门进来也都能读《红楼梦》。但问题是我们从其他的门进可能都不太容易,吃喝玩乐的途径就很容易。
大家都喜欢吃,《红楼梦》又很吸引人,结合起来,从这一个门进入《红楼梦》,然后再看看《红楼梦》写的是什么,这就有意思了。从吃这一头进去,也有很多看不懂的东西,怎么办?这就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想法。
南都:书名为什么不叫《<红楼梦>中的美食》而取名为《<红楼梦>中的饭局》?
周岭:你提得很好,为什么不叫《<红楼梦>中的美食》?因为美食有点受局限,你只是写吃了,实际上除了吃还有玩。因为它里边有多少在酒局上的娱乐活动,拇战、射覆、占花名儿,行飞花令、牙牌令、击鼓传花。这些东西你用美食就不能涵盖它了,如果用饭局那就全进来了。
而且饭局还有一个意思,它既然叫做“局”,你就别光着眼于吃喝玩乐,还要想想这局里边还有哪些要深究的内容,通过这个局,你要悟出一些什么道理来,通过这个局,你找出一些什么故事来,还有,谁出席的这个局,为什么?甚至要通过这个局破一个什么案。
虚构的茄鲞和消失的豆腐皮儿包子
南都:关于“红楼第一菜”茄鲞,您非常敏锐地指出,这道菜里的深秋的茄子和春初的新笋是不打照面儿的,因此茄鲞不是一道做得出的菜,根本就是王熙凤逞才使能哄着刘姥姥玩的。这个看法非常有意思,也令人信服。曹公在饮食上使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有什么更大的寓意?
周岭:说到这个茄鲞,就说到红楼菜。《红楼梦》里边写的菜,饮食场景很多,食材也很多。读《红楼梦》的人对《红楼梦》的菜都很感兴趣。
我记得从40多年前开始,就有一个个的餐馆做“红楼宴”。比如说北京中山公园里边有一个餐馆叫“来今雨轩”,那儿就做红楼宴。北京北海公园里头也有一个红楼宴。1988年我们红楼梦文化代表团出访新加坡,还把红楼宴给带到新加坡去了,做了一个多月,反响极为热烈。等回到国内之后,在1989年底、1990年年初,又在广州做了一次红楼文化艺术展,有一个内容也是红楼宴,也做了一个多月。我刚才说的红楼宴,我都参与指导了,所以我对红楼菜很熟。
但是因为这些红楼宴都是某一个菜系加持的,所以就带有这一个菜系的非常重的痕迹。另外有些食材也不容易找,所以真正的“红楼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
说到红楼菜,必须说茄鲞。为什么我把它叫做“红楼第一菜”?一,它的地位;二,它的知名度;第三,它在整个宴会当中出现的时候所引起的轰动效应,以及对人物刻画的作用。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最能体现曹雪芹“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宗旨。这个菜就是虚实结合的,茄子是实的,鲞也是真有的,茄鲞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就没道理。鲞是干鱼,到今天绍兴还有一道名菜叫“白鲞扣鸡”,就是用咸鱼跟鸡一块烧,非常好吃。但茄鲞这道菜里没有干鱼,这就是生造出来的一个菜。曹雪芹生造出来这个菜名,肯定有他的目的。我认为第一个目的就是醒人眼目。茄鲞两个字一出来,大家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在这个菜上了,由于注意了菜,所以注意了菜的做法,就注意到这个菜的影响,以及所有吃这道菜的人,写人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种文不对题的起名法很有意思。我也是读《红楼梦》,一读茄鲞看不懂,我就觉得有意思了,我去琢磨它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写?第二就通过这道菜写刘姥姥、写王熙凤,你看这两个人写得还得了吗?刘姥姥的瞠目结舌,王熙凤的煞有介事,读者到这个地方全都目瞪口呆,所以这个菜能不叫“红楼第一菜”吗?它合理吗?一点也不合理,深秋的茄子和初春的新笋是碰不到面儿的。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都烹制完了以后,放瓷坛子里,吃的时候把它盛出来,用炒熟的鸡瓜子一拌就得。炒熟的鸡瓜子是热菜,取出来的是冷菜,冷菜拌热菜,谁家有这样的吃法?它就从不合理当中又起到了最后一个作用,间离效果。
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核心就是间离效果。曹雪芹深谙此道,你看他就不断把你带入戏,你已经很痴迷的时候,他又推你一把,又或者拉你一把,让你出戏,这可是不得了的一个大手笔。
你看这个东西之后,你觉得这个不可能啊,我太认真了,哑然失笑,然后就出戏了,这就是曹雪芹写茄鲞的目的。
南都:我去年到苏北过年,发现晴雯爱吃的豆腐皮包子很像一道苏北地区的家常菜(当地叫腐皮包子),怪油腻的。这两样是一个东西吗?晴雯这样一个伶俐的丫头怎么会喜欢吃这道菜?
周岭:豆腐皮儿包子各地都有,尤其是苏浙一带。浙江的湖州有一道名吃就叫湖州千张包子。
好多年以前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学校伙食一般,我每个星期天带本书到西湖边上去看书,中午找西湖边上有一家饭店吃饭,他家的湖州千张包子做得好吃极了。8分钱的鸡汤粉丝汤底,汤是熬得非常好的老母鸡汤,上边放一个单件或者双件,单件一个是1毛2,双件两个是2毛4,加上8分钱,一共三毛。我很少吃双件,因为没钱,吃个单件就不错了。这单件就是千张包子,当时叫千仁包子。千仁包子外边儿是一个豆腐皮儿,这豆腐皮儿并不是后来我们说的千张,那个时候是腐衣,熬豆浆的时候上面结了一层皮,挑起来薄薄的,腐衣很薄很好吃,比千张好吃多了。用这个做皮儿,里边儿的馅儿是猪肉馅儿加上开洋、火腿、鲜笋,里边至少有一个鲜虾仁,开洋是干虾仁,它是鲜虾仁。这一个包子,从馅儿上说就非常好吃,皮儿又是豆腐皮儿的,比面、比千张都好吃。然后又放在鸡汤的粉丝汤底里边,可口无比。
很多年以后,我们拍电视剧《红楼梦》的时候,带着王扶林,带着李耀宗,我说我一定要请你们吃一个湖州千张包子,找不到了,那个时候就没了。你看这才几年的功夫就找不到了。
大概有七八年前,我应湖州政府的邀请去做一个项目的顾问,下了飞机就说请吃饭。我说别太麻烦,你们帮我找一碗你们这个地方的特产,豆腐皮儿包子。他们找来了,我一吃不对,粉丝太粗,汤也不是鸡汤,皮儿是千张,也不是腐衣了,那里边包的就是肉馅,也有虾仁,但是完全不对了。
所以你觉得你在淮安吃的豆腐皮包子有点油腻,但各个地方有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们要是复原《红楼梦》的这套东西,一定是非常精致,选材要非常讲究,绝对不能做得很油腻。我也不主张用千张做皮儿,这个豆腐皮儿应该就是用腐衣做皮儿,因为它薄。馅儿就得仿我当年吃到的西湖边儿上那家饭馆那东西。
我曾经在北京卫视做一档节目,跟英达、邓婕一起,叫《春妮的周末生活》。他们希望我能够带着他们做一个红楼菜,我提出了做《红楼梦》的豆腐皮儿包子。可惜了当时只有千张,但那一天做出来的也很好吃。
所以我说晴雯吃的豆腐皮儿包子一定是很精致的,要不然也不值得宝玉专门给她找人送过来,李妈妈吃了宝玉也不会这么生气。
螃蟹宴上缺席的蟹八件
南都:螃蟹宴是网络上红迷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在您看来,曹公写螃蟹宴的目的是什么?
周岭:曹雪芹写螃蟹宴还是为了写人物,主要是写史湘云。作者写人物的手法和其他小说不一样,不是一出场就把这个人给写完了。他是用画家三染法,叫一勾二勒三皴染,不断地把一个人物给写完整。这个活动写她这个面,那个场景写她那个面,再一个故事写她的另一个面,把一个人物的多侧面、立体的形象给塑造出来。
曹雪芹的这些饮宴活动都跟塑造人物有关系。史湘云为什么要办螃蟹宴?是因为她听说大观园里姐姐妹妹开始作诗了,她没赶上,她觉得我来做东道,我们再写诗,过这个瘾。从这个人这些言语作态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没心少肺的女孩,正面说就是“幸英豪阔大宽宏量”。她也没想太多,怎么想就怎么说了。
她住在蘅芜苑,跟宝钗关系很好,宝钗就跟她说,你要请吃饭是要花钱的,你每月就那几串钱,家里边父母双亡,跟着叔叔婶子过日子,又不是想要什么有什么,请客的钱哪来?钱不够了,你是回家要去还是在这朝谁要?这又旁写了一笔宝钗,宝钗最能够替别人想。你看这是她的性格的一个侧面。你不能说宝钗有心机,她关心史湘云钱不够了怎么办? 所以宝钗说,我哥哥铺子里的伙计,他们田庄上出的好螃蟹,让他送过来,这家里边从上到下从老太太开始都是喜欢吃螃蟹的。
这顿螃蟹宴于是就在宝钗的赞助之下开成了。够吃不够吃呢?后来刘姥姥来了,问平儿,平儿说哪里够?也有摸得着的,也有摸不着的,能摸得着的就吃几个,摸不着的只能看着。但你再看史湘云什么表现?螃蟹宴上招呼着大家“尽管放开量吃”。其他地方只要写到史湘云,都是大笑大闹的形象,只有这一个地方,说“史湘云招呼一会儿众人,又出一回神”。“出一回神”四个字,背后的内容太丰富了,你粗粗地一看过去太可惜了。
史湘云为什么出一回神呢?这一回神的内容,就是她的不得已,用别人的钱给自己做脸,本来不够吃的东西,又让大家放开量吃,心里边不是滋味。这一笔真神来之笔,把史湘云的不得已的一面也给写出来了。写人物就得这样写,这就是螃蟹宴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红楼梦》的写作笔法就是一笔多用,它不是一支笔只写这一件事,他写了一件事,一定又勾连了很多人很多事。例如在螃蟹宴上很多人的表现,凤姐的表现,老太太的反应,写得都非常精彩。
南都:另外还有个问题,螃蟹宴上为什么没有蟹八件,薛姨妈还说要“自己用手掰着吃”?
周岭:《红楼梦》还有一个写法叫“不写而写”。《红楼梦》的时代已已经有蟹八件了,但原文当中没写过,电视剧里出现蟹八件这事儿是我干的。怎么说呢?我们在拍电视剧《红楼梦》的时候,序集有个很重要的场景是中秋之夜,甄士隐请贾雨村来吃饭,两人吃什么?书上没写,但是剧本里要体现。最好是反映时令的东西,中秋节可以吃螃蟹,而且从形象说比较好看。
你要吃螃蟹就得有工具。在明中叶以前是没有蟹八件的。最早有一本书叫《酌中志》,写宫中吃螃蟹,都是用什么吃的?宫女和太监留着长指甲,用指甲来剔蟹肉,能把螃蟹壳剔得干干净净,摆出造型,吃得很艺术化。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工具。明末才开始有工具,清初才开始广泛使用,到了清中叶、晚清的时候,江南人家嫁女的嫁妆里边总必不可少地有一套蟹八件。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一个是看书,再一个听家里边的老人说起。因为我是在北京出生,我们家上两代人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很久了,我小时候就听老人家说,北京有个馆子叫正阳楼,是专门吃螃蟹的,在那儿吃螃蟹就用蟹八件,每件什么样,哪一件用来干什么,说得很清楚。我就很向往能够找到一个蟹八件,看看什么样。
除了我的父母、祖父母他们那一辈在北京见过蟹八件以外,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没见过,因为解放以后连吃螃蟹的机会都很少了。我们在拍这场戏的时候,我就跟道具部门说,我听说有一种东西叫蟹八件,把这东西找来,看有没有。能找到的话,这一顿中秋夜宴就很添光彩。道具部门到处找找不着,最后终于在北京工艺美术品公司找到一套,他们也只有这一套,是准备去拿外贸订单的样品。在序集里边摆上了,大家看了以后开心得不得了,还有好多特写镜头。
但为什么螃蟹宴上没写蟹八件?首先螃蟹宴上应该有蟹八件,这是不写而写。因为像贾母、王夫人、林黛玉这样的人,她吃螃蟹真的用手掰用牙啃?这不可能。一定用工具,只是没写而已。它的着眼点没在工具上。另外薛姨妈说“用手掰着吃”,不排除也是要用工具的。那只是一个说法,就是我自己来,你别伺候我。
忽南忽北、虚虚实实的红楼饮食
南都:您在书里详细讨论了“乌进孝交租”的单子,内里有典型的江南食物,如御田胭脂米、碧糯、白糯、粉粳,也有属于关外满人才有的吃食,如大鹿、獐子、狍子,曹雪芹为什么这样写?
周岭:研究《红楼梦》必须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生活,第二个宗旨。我们先说生活。曹雪芹他们家祖上是在关外的,从龙入关。明朝在关外有辽东都指挥使司,这么一个衙门管辖整个关外的事务。它下边有各种卫和所,都是军事编制。比如沈阳有沈阳中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有卫有所。曹家的祖上明朝初年开始就做沈阳中卫的指挥使,是在那个地方镇守的官员。这个职务是世袭的,父亲死了传给儿子,儿子死了再传给孙子,这样一辈辈传下来。一直传到明末的时候,沈阳中尉指挥使的名字叫曹锡远,他的儿子叫曹振彦,曹振彦就是曹雪芹的高祖。曹锡远和曹振彦父子跟努尔哈赤打仗的时候兵败被俘,投降了满族。以后跟着满族人打天下,在关外打了不知道多少仗,立了很多功。这在文献都有记载,还有好多碑文可以证明他们在关外的情况。
后来曹振彦跟着多尔衮一直打到关内,他的儿子叫曹玺,也就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也打了很多仗,立了很多功,他后来官做得很大,做了内廷侍卫,又做了内务府几个司的郎中,又派到江宁去做江宁织造,还兼了工部尚书衔,他是他们家第一代做江宁织造的。
后来传给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又传给曹雪芹的父辈曹颙和曹頫,到曹頫那一代被抄家,这家就完了。也就是说曹雪芹的祖上是关外来的,而曹雪芹的出生是在南京。他家有三代四个人在南京做了六十年江宁织造。所以,从生活来源这方面说,他们家有一些家里边的说法,祖上是什么情况,曹雪芹小时候耳濡目染可能都清楚。他的生活环境就是江南,所以他对江南的生活很熟悉,对于老人口中的关外生活他也很熟悉。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的东西,为什么有关外的也有南方的,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曹雪芹著书之时,他的艺术宗旨是什么?我刚才说了,“无朝代年纪可考,无地域邦国可考”,他就不愿意坐实在某一个地方和某一个朝代。再一个他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哲理又贯穿全书的始终。所以他就借着他的生活,在他的整个著书的宗旨的指导下,在他的哲理的统摄之下,让乌进孝交租,甚至所有的饮食起居,所有的方方面面的生活都带有浓重的忽南忽北,虚虚实实的色彩。
这样写出来的小说,让大家不要老是想着这是什么朝代,在什么地方,你就着眼于故事,着眼于人物,这个做法是非常成功的。

2008年夏红剧亲友在周岭家聚会
南都:研读《红楼梦》这许多年,最让您眼馋、渴望尝试的红楼饮食是什么?
周岭:应该说红楼梦里所有的吃的我都很眼馋,都渴望尝试。当然也还有一些很难得吃到的东西。
从食材来说,我很多年前就一直向往吃一次鲟鳇鱼。乌进孝交租的单子里有“鲟鳇鱼两个”,在程高本《红楼梦》里,改成了“鲟鳇鱼两百个”。为什么?大概觉得送那么多东西,鲟鳇鱼才两个太少了。显然程伟元、高鹗他俩没吃过鲟鳇鱼,也不知道鲟鳇鱼,但曹雪芹是经过见过的。
鲟鳇鱼两个就不少了,你知道一条鲟鳇鱼多大,一个头就拉一车,一条鱼得三四辆车来拉它。最长最大的鲟鳇鱼有一吨多重。它要长一百多年才能长这么大。捕捞鲟鳇鱼也很难。乾隆皇帝专门有写捕鲟鳇鱼的诗,写得很传神。
鲟鳇鱼全身都是宝,好吃得很,鱼肉是非常鲜美的,但是皇家每年也就是几条进贡到宫里,像京里的达官显贵,八旗那些王爷每年冬天也派人到关外去收这个鱼。一直到解放前民国时代,每年冬天都有鲟鳇鱼送到京城来,老百姓也能吃到。谁家也没那么大锅,没法整条鱼烹制。怎么吃?买鲟鳇鱼也都是切一块,称了一斤半斤之类的,回到家里切成丁,用油一炸,然后再炒或者再炖,味道非常鲜美,不是一般的鱼能比的。
第二个,鲟鳇鱼全身的骨头都是软的,没有一根硬刺。这么大的鱼没有硬刺,很奇怪。这骨头干嘛?骨头拿来煲汤,鱼汤炖得白白的,像奶一样非常好。第三个,最重要的部分,最难得到的是鼻子。鼻子被砸碎了全是脆骨,煮熟以后凉拌,好吃至极。
我很多年就一直想看看有什么机会能吃一次。有一年我到哈尔滨讲课,当地也是要招待我吃东西,问我想吃点啥,我说鲟鳇鱼。他们居然说野生的没有了,但有养殖的,就在松花江的北岸。带着我过江,到松花江的北岸还要走不少路,找到一家专门吃鲟鳇鱼的馆子。案子上一条大鱼,大概有十几米长。那天我吃了炒鱼丁,吃了鱼骨汤,可惜鼻子早就被人吃掉了,还没吃着。现在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尝尝鲟鳇鱼的鼻子。
做视频的一个任务是匡正误说
南都:这几年,您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系列视频“周岭说红楼梦”,受到广大红迷朋友的喜爱。我们这个访谈系列名叫“重释经典”,通过网络平台聊红楼梦,传承红楼文化,发起相关讨论,也是“重释经典”的一种有效方式。你在做“周岭说红楼梦”系列的过程里有何感触?您如何对待网络上的不同意见?
周岭:疫情之前,我一直在北大清华人大几个大学讲课,讲了很多年了,每年都有一个讲课季。到了疫情开始都困在家里了,讲课季就停了。我觉得时间别浪费,所以才开了一个视频,叫“周玲说红楼梦”,在几个平台上发布,主要是在今日头条的西瓜视频,也转发到抖音上,在哔哩哔也做了一点发布。
这个视频我是想一个一个系列做下去,大概已经做了几百讲了。做的过程当中也收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

著名红学家、87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周岭
比如说正面的意见。我讲曹雪芹的时候,曾讲到曹寅在任江宁制造以前做过内廷侍卫,在内廷侍卫之后又做了内务府的几任司官。我当时就说了他在内务府的什么司什么司。就有网友跟我说,周老师你漏了一个会计司。说得很对,因为当时重点不是要说曹寅在内务府的任职情况,所以就没有说得很全。实际上我在前边和后边都有提到。但就说明,红迷当中真是藏龙卧虎,他们读书读得很细,对曹家的家世生平的研究不可小觑。你稍微有一点没提到,他就给你提醒了。我觉得提得很好,我在结集成书的时候,这些地方都要补写上去。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因为他不是研究《红楼梦》的,也不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更不是做学问的。比如说有人就提出来,您对癸酉本石头记怎么看?我也简单地回复了一下,我认为这个本子是谁也没见过,只是某人自称他根据他看过的印象,根据记忆写出来的,这个不是原本,无从评论起。我个人看是哗众取宠,是编出来没什么意义的一本子。像这一类的问题也很多,还有的人就说,周老师你掉到“曹家沟”里去了,《红楼梦》根本就不是曹雪芹写的,社会上很多人这样说,也有一些所谓的学者言之凿凿,但实际上不对的。因为《红楼梦》的著作权就是曹雪芹的,我在视频当中说得很详细,证据找得很多,而且有很多证据应该说是铁证,足以证明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这个著作权不能给别人。
有些提的都很好笑,说《红楼梦》是吴梅村写的。吴梅村绝对写不出《红楼梦》来,《红楼梦》里边借省亲事写南巡,康熙6次南巡时吴梅村早死了,他怎么知道南巡的事呢?
我随便举个例子,《<红楼梦>中的饭局》里面提到的普洱茶。普洱茶得名叫普洱茶,是因为雍正七年改土归流成立了一个衙门,这个衙门叫普洱府。这个地方以前产茶并不叫普洱茶,叫普茶。普洱府成立以后,这个茶才叫正式定名为普洱茶。《红楼梦》里写到普洱茶,那一定是雍正七年以后的事儿,吴梅村早死了,怎么可能是他写的?这些一定要有证据,没有证据的话不能说。我们有证据可以断定《红楼梦》是成书于什么时间段。所以我觉得做这些视频有一个任务就是匡正误说。
南都:《<红楼梦>中的饭局》是“周岭说红楼梦”系列中结集成书的第一本,未来还将有哪些主题结集出版?这几年在网络上讲《红楼梦》,您对这部经典之作又有了哪些新的想法?
周岭:我讲过的系列,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已经出了一本《<红楼梦>中的饭局》,还有两本签了合同。其中一本是说《红楼梦》的改编,从历史上《红楼梦》一问世,就有人把它改成舞台戏,一直到后来我们87版电视剧,以及其他电影电视剧的经验得失,这主要是给后来的人提供一些借鉴,这个系列应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结合今天的一些新的认识,我提出来的,这个书的名字叫《IP变现:粉墨红楼之路》。很可惜《红楼梦》原作者写完这个小说,是在贫困交加当中去世的,稿费他一分也没挣着。后来根据高鹗的说法,有人把这个书抄出来以后,在庙市上“昂其值得数十金”,就是在庙会上卖抄本,那时候能卖几十两银子,按照刘姥姥的说法20两银子够我们庄稼人活一年了,一部书都能养一户人家活一年了。也就是说这个书开始变现了。
至高鹗把这个书印出来,他没说变现的事儿,但是想来这个书也赚了很多钱。赚钱更多的还不是出版的书,是改编的各种各样的舞台作品。无论是戏曲还是电影电视剧都赚了钱,我们87版电视剧《红楼梦》也赚了很多钱,当然我们没有分着,中央电视台光广告费收了多少?也就是IP变现要感谢改编作品。而这些作品变现之后,我们希望应该拿出来一些来推动《红楼梦》的普及事业,要圆曹雪芹的梦。而且后边还有很多更新的机会,你比如说现在AI技术、区块链技术,怎么能加持在IP变现这件事情上?
比如说我写了一部《<红楼梦>中的饭局》,大家看了到此为止,或者是有人去开个餐馆或者怎么样,都是一般性的效果。如果我把它做成一个红楼饭局项目,无论是在北京、在苏州或者在美国,开若干个红楼私房菜的样板店。
我们过去的红楼宴不能叫很正宗的红楼宴,有很多问题我们不细说。我这本书出来之后,尤其是我来参与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我有一些新的感悟,所以做这样的红楼饭局的样板店,以及做好了以后,又能够开很多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的连锁店,不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吗?也是为天下苍生造福的事情,也能够变现,也能对红学世界做更多的贡献。然后把AI技术植入进去,做成各种沉浸式的场景,可以让王熙凤指挥机器人布菜,可以跟来就餐的人互动对话……再加上区块链,因为将来的资产80%以上都是虚拟资产,我们可以用区块链技术再把红楼饭局这个项目做成一个结合元宇宙的项目。就是说它有实的、落地的,也有虚的,数字的。所以《红楼梦》给了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机会,它是一个宝库。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