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两点,你躺在床上刷短视频,手指机械地上滑,屏幕蓝光刺得眼睛发酸。突然,一个念头闪现:“我为什么要看这些?我现在快乐吗?”那么恭喜你,这一刻你已经在无意识中触碰了哲学命题:人的生命感受究竟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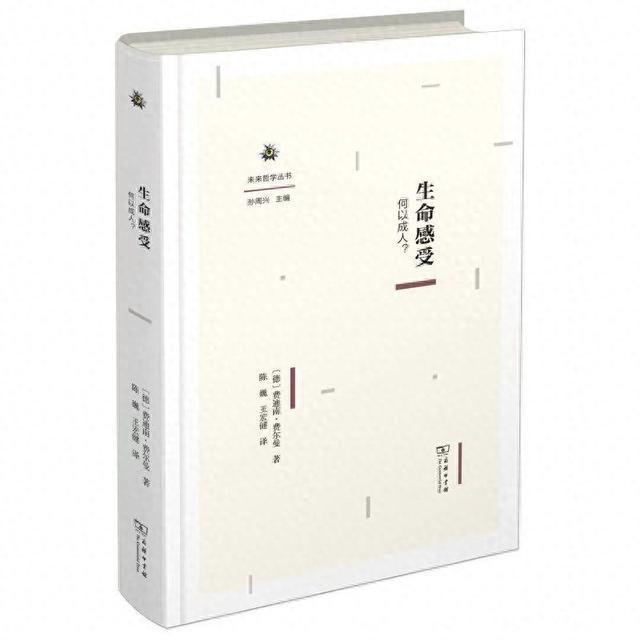
最近,当代德国生命哲学家费迪南·费尔曼生前正式出版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生命感受——何以成人?》出版,该作如一剂“哲学解毒剂”,对当代人的生活有着极现实的指导作用:刷手机停不下来却更空虚、朋友圈点赞无数却更孤独、日程表精确到分钟却更焦虑,与其在元宇宙里当数字难民,不如先找回自己鲜活的“生命雷达”。
费尔曼的学术生涯始终围绕“生命”展开,从早年对胡塞尔、狄尔泰的研究,到晚年聚焦“生命哲学”,他始终致力于弥合理性与感性、存在与体验之间的裂隙。本书作为其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系统提出“生命感受”这一核心概念,以探讨人与其世界之间的本源性联结。
它既非纯粹主观的情绪波动,亦非客观的物理事实,而是主体与世界的动态交互中生成的生存确定性。而这一概念的提出,直接挑战了传统哲学中理性至上的范式。费尔曼指出,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理性动物”和“政治动物”,却忽视了“感受”作为第三维度的存在。他援引布鲁门贝格的“如何存在”之问,将哲学从对“本质”的静态追问转向对“生存”的动态探索。
费尔曼对当代社会的诊断尤为犀利。他通过“虚拟空间”与“数字化时间意识”两章,揭示了技术如何重构人类的存在方式:
现代交通与互联网消弭了地理距离,却制造了“无空间性”的生存体验。雅斯贝尔斯笔下的“均质化恐惧”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预言,在今日演变为“无感受的感受”——人们在虚拟社交中模拟故乡,却在现实中失去归属。
数字化时间将生命压缩为“滑梯上的滑行”,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界限被批量化的信息流击碎。费尔曼借用赫尔曼·吕贝的“未来确定性萎缩”理论,指出现代人陷入“既渴望自由又依赖规训”的矛盾:我们痛恨被算法支配,却又依赖其维持社会运转。
面对这些困境,费尔曼并未沉溺于悲观。他提出穆齐尔所命名的“可能感”概念,认为数字化带来的拟真体验虽瓦解传统记忆结构,却也催生了新的生命创造力——年轻一代通过“编织虚拟回忆”重构身份认同,这或许是人类适应技术异化的生存智慧。
“只有回到生命本身,哲学才能重新赢获自身在当代世界的价值。”这本书想传达的一个理念,是做自己人生的“野生哲学家”。当合上这本书时,你可能会突然发现:通勤路上堵车时的夕阳,比朋友圈九宫格更治愈;外卖小哥的一句“祝您用餐愉快”,藏着比元宇宙更真实的温暖;深夜失眠时的胡思乱想,可能是你离哲学最近的时刻。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试读
生命感受——何以成人?(节选)
着眼于爱欲的生命感受,洞穴比喻也获得了某种新的阐释。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是充满教益的,但却是抽象的。它没有说,人为何以及如何抵达洞穴。在心理学上它也是前现代的,因为它不合乎当今时代对我们的感受之内在世界的研究。在自我观察时,我们不也只看到阴影,而却将其认作我们自身的唯一现实?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爱欲给予这个问题以回答,且克服了柏拉图对感官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严格区分。我们人所看到的阴影乃是我们的身体性自身的反射,但它不只是假象,而更是生命意志的表达,它的火焰照亮了我们的亲密性的洞穴。
通往那里的道路经由布鲁门贝格的《洞穴出口》,后者展示了古代的洞穴比喻从培根经过笛卡尔与康德直到维特根斯坦的现代转变。在结尾,布鲁门贝格接着阿诺德·盖伦表述了他自己的立场,即对追求自我保持的表达。借此,布鲁门贝格停留在理论好奇心的框架内。爱欲的生命感受之视角被忽略了。他没有深究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的兴趣朝向的是逻各斯的诸种形式。与此相应,他的洞穴和柏拉图的一样,是没有身体定位或者没有感受色彩的构成物。
与此不同的是布托·斯陶思,在他的著作《洞穴形象》中,他详尽阐述了洞穴比喻的不同向度。斯陶思的洞穴世界一时是遁世之所,一时是未成熟者的场所。培根在他的偶像学说中将洞穴形象赋予作为个体的人,斯陶思紧接着培根提出了视域减缩的向度。因此,每个人都藏在他自己的无知洞穴之中,它“破坏和腐蚀了自然之光”。在这种含义的摇摆中,洞穴成了人的一般生命感受的辩证法之比喻。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在斯陶思的洞穴形象中,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有着核心地位。在对话中的她和他,或者是变幻莫测的塞西尔和酷似作者的“自我”,用身体语言相互交谈。自此,斯陶思成了不可思议的爱情动力学和一切相关深渊的精妙阐释者。他对伴侣联系的精确观察使得他成了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布鲁门贝格也是一个分析家,但在《洞穴出口》中,他仍处于诞生的心灵创伤之中,后者掩盖了被弗洛伊德所宣称的性方面的求知欲。此外还有清醒的主客分离,后者导致了认知主体的孤立。为了在生命感受的意义上扩展主体,必须让爱欲作为逻各斯的补充而发挥作用。
(文化责编:拓荒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