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环球网报道 记者 文雯】在学术的广阔天地里,总有人怀揣着对知识的无尽渴望,皓首穷经,默默耕耘。陈年福便是这样一位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深耕者,他从中学语文教学起步,却在甲骨文研究中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归宿,开启了别样的学术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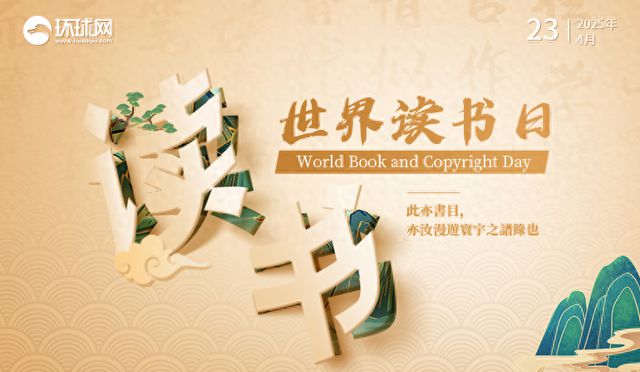
环球网: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从中学语文教学转向甲骨文研究这条道路?
陈年福:我喜欢书法,在做了10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师以后,决定去考书法研究生。没想到最后学起了甲骨文。若说是什么契机,大概书法与甲骨文都与文字相关。有意思的是,当我进入甲骨文这个世界之后,书法就再也没有了长进,我发现自己基本上没有时间来玩书法了。希望在完成了甲骨文研究的一些计划后我能再次把书法捡起来。
环球网:在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坚定了深耕甲骨文研究的决心?
陈年福:学习与研究甲骨文,或者说学习与研究古文字可能并无什么瞬间便让一个人下定决心继续而不去改变。学习与研究古文字开初或许有一种新奇之力能吸引你,但接触多了,更多的时候是枯燥,要耐得住寂寞。关键在于坚持,这个坚持有些久,大概有个10年左右。因为只有学习与积累了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才能打好基础。只有坚持住了才会有考释出第一个新字后的无比喜悦,接着一个个新字考释出来,会让你有一个个喜悦的瞬间。这与做学生时独立做出了一道道几何证明题给人带来的喜悦是一样的。人是天生的发现者,考出新字,便也是一种发现与发明,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愉悦。这或许就是学习古文字的魅力吧。
环球网:面对海量的甲骨文资料,您是如何进行分类和筛选的?
陈年福:我1993年考上研究生学习甲骨文时,正赶上几种大型的甲骨文研究材料问世。大型著录材料《甲骨文合集》与《小屯南地甲骨》等早已公开出版,文本摹释工具书《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与文本摹释引得工具书《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正好出版,同时查阅甲骨文考释情况的工具书如《甲骨文字典》也出版了,而甲骨文字集释的工具书《甲骨文字诂林》在我硕士毕业时也出版了。有了这些材料与资料图书,学习和研究甲骨文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难了。因为一般大一些的大学都会购置这些图书,获取资料比以往要容易多了。我写硕士论文时,可以用计算机写作论文了,我的学位论文便是自己在计算机上写作的。硕士论文便是我利用计算机研究甲骨文的最初成果。以后的研究可以说一刻也离不开计算机了。
当时看到有这么多的甲骨文研究材料与成果,起初心里老是觉得甲骨文研究做得差不多了,可能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但这其实是一个初学者的错觉。后来写论文时实际利用了这些文本材料工具书,才慢慢发现有不少问题。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释读者看不到最原始的甲骨著录拓片,只能根据经翻印的不清晰拓片来释读文辞,难免会有各种错误。
因上述原因,我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主要已经完成的就一件事:甲骨文文本材料释读整理及其数字化。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说是一个大工程一点也不为过。
第一,时间长。1998—2010年,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殷墟甲骨文摹释全编》(10册,线装书局,2010年);2011—2021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殷墟甲骨文辞类编》(10册,四川辞书出版社,2021年);2021年,“殷墟甲骨文数据库”(中华书局古联公司籍合网,2021年试上线,2022年正式上线)。我1996年硕士毕业,1998年调浙江师大工作,2021年退休,整个工作期间除必要的教学工作外,全部研究工作主要就是就是做了这件事。
第二,材料全。共收录37种甲骨著录材料与5种缀合材料计拓片93850片,经剔除重片后的拓片为59593片。凡公布的材料凡全部收录。
第三,整理难。甲骨文文本材料的整理有拓片著录、拓片缀合、释读文辞的汇纂等各个方面。其中,仅重片一项的整理就非常困难。甲骨著录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拓印时间的早晚,有收藏整理者的不同,有拓印质量的优劣等等。虽然甲骨实物是唯一的,但甲骨拓片则可能广泛流布,而早期甲骨著录书有些是仅据拓片而著录的。这都会造成甲骨片在不同著录书之间的重复收录,即他重。因为甲骨的保存会出现腐缺磨损的现象,在不同的时期或由不同的人拓印或拍照,所以著录的拓片或照片图像的清晰度、完整度等可能存在差异,这类他重片的存在对甲骨文的释读具有互相参照的价值,因此甲骨片的重复著录有其合理之处。《合集》《补编》等大型甲骨著录书,由于收录甲骨片来源复杂,则不可避免会产生所录部分自重的现象,但同一书中自重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作为大型的甲骨文文本引得类工具书,重片必须剔出,否则会造成材料利用上的错误。但要剔除数万片甲骨中的全部重片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第四,释读难。甲骨文文本材料整理就是将释读正确的文本依片号或依单字等汇纂在一起。释读正确是最重要的。但将一条条的文辞从拓片上释读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一般分两步:一是原文释读(原文摹写),二是将摹写的原文转换成现代汉字(释文)。虽然大部分文辞已有释读,但即使全部校释过,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第五,造字难。甲骨文文本数字化,要造两种专门字体才能将文本录入电脑。一是原文字体,二是释文字体。我造的原文字体(ZJNUJGW.TTF)大约有14000个字、释文字体(JGWSW.TTF)大约有5000个字,基本够用了。造字也花费了大量时间。
得益于长期从事甲骨文文本整理与数字化工作的经历及其产出的数据库成果,我在编纂与出版甲骨文文本材料工具书时更加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这一基础性工作迫使我一一校读全部的甲骨拓片,通过不同的著录材料仔细校对每一条甲骨文辞的释文,汲取诸家之说并反复酙酌每一文字的不同考释与分合,因大量造字而注重辨析文字构形的细微笔画形态、构件数量位置方向等的变化等等。这一全方位考察全部一手材料、经眼每一片甲骨、辨析每一字一形、细究每一辞一句的研究积累,加上方便快捷的数字化手段,让我在研究工作过程中经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仅在释字上便有了难以想象的巨大收获。
这样就有了我在甲骨文研究中的第二件事:编写《甲骨文词典》。
环球网: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编写《甲骨文词典》的初衷和筹备过程吗?
陈年福:2021年(我的退休之年),《殷墟甲骨文辞类编》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在甲骨文文本材料整理及其数字化研究任务的完成。但其实就我个人的甲骨文研究而言,此前的所有数字化工作就像是做资料卡片式的研究前提与基础,自己真正的研究工作好像应该从退休时算起。这一年,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数据库的《殷墟甲骨文词典》编纂”,同年中华书局古联公司也决定在籍合网上线我的“殷墟甲骨文数据库”。为配合上线的需要,我利用自建的数据库以及在写硕博士学位论文中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甲骨文字词表”,很快完成了《甲骨文随机词典》的编写,这年年底数据库试上线,翌年4月正式上线,至此,甲骨文数字化的工作便正式告一段落,同时我的研究工作重心便完全移到了词典的编写上来。在随机词典的基础上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承担的国家项目于2023年4月结题,同年《甲骨文词典》列入202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这样便有了词典的出版问世。
环球网:这本《甲骨文词典》相较于市面上其他相关词典,有哪些创新点和独特之处?
陈年福:这是一本全面系统的语文类词典。以解释殷墟甲骨文全部语词(单音词与多音词)、短语(包括习语)、句式的具体用义为宗旨。词典用以字统词,即以字本位的方式编排所收录的语词,3840个字头统领3918个单音节词目(包括35个分列词目与43个未分列词目)与3750个多音节词目,词目共计7668个。词典的编纂目标是为读者在学习与研究甲骨文中碰到一些难以读懂的文辞与语词时,可以通过查阅本词典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为能够查阅到全部字词,词典所收录的语词既包括已识字语词也包括未识字语词。所收单音节词目,即使文辞已残,无法据文例与句法推定其用义的未识字(包括未隶定字、个别习刻字)语词也全部收录。所收多音节词目,有一部分并非严格意义的成词语词或专名,而是需要解释的形式较为松散的语词组合。
词典专列“析形”一项,对记录语词的文字构形,尤其是甲骨文字的特殊构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揭示。如揭示甲骨文字通过缺笔、增笔、连笔、断笔、倒书、变形等方式改变形符的正常笔画形态以记录使用时的特殊用义,揭示甲骨文字构形中的声符表形现象。
词典在文字考释、解释疑难语词方面有大量的新发现。如解释“甘”用作“疳”,发现了甲骨文所记载的小儿疳证、疳疾等。考释出新字“䀯”,并从而发现了甲骨文文辞所记录的商人观象授时的实例。词典中类似的字词例很多,有数百例。
环球网:您认为未来甲骨文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可能会在哪些领域?
陈年福:甲骨文研究将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重点依然是文字考释。有不少文辞我们还是读不懂,关键是不认识字。尽管释字很困难,但甲骨文研究的突破还是在于释字,包括对已释字用义的解释。大家将会发现《甲骨文词典》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环球网:在甲骨文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将这一古老文化遗产传承给大众?对于利用新媒体技术传播甲骨文文化,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陈年福:社会大众关注甲骨文这一最古老的文化遗产就是一件好事。这当然少不了一些有志于推广甲骨文文化的人利用新媒体技术来传播与传承。我的学生李右溪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现在做甲骨文文化传播的人逐渐多起来了,质量上参差不齐。我觉得传播者应该有意识地学习正确的甲骨文字知识,而不是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随意乱讲;或根据一些对甲骨文字的错误解释来讲。我的建议是开讲者一定要有甲骨文基础,比如最起码要有硕士水平以上才能保证不会讲得太离谱。
(文化责编:王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