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音:重现近代日本女作家群体的天才火花

小说家、译者默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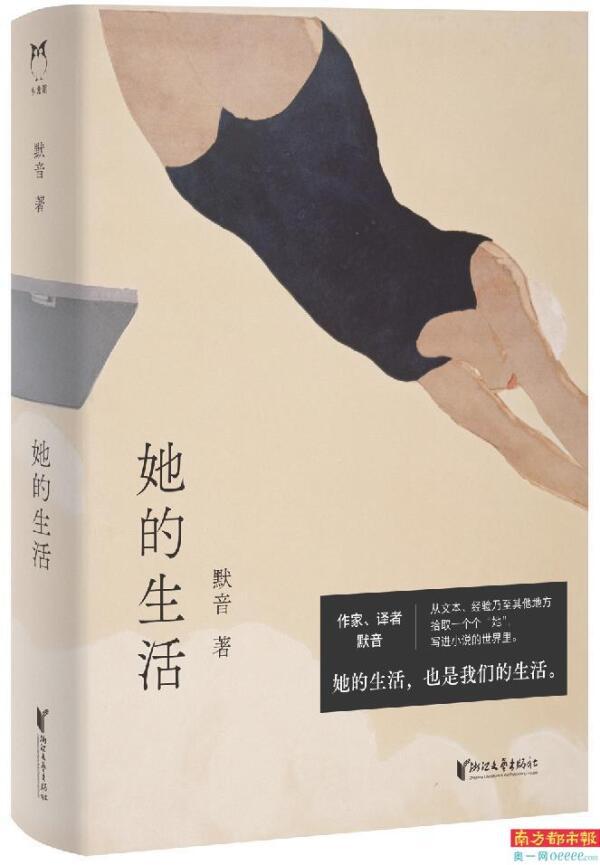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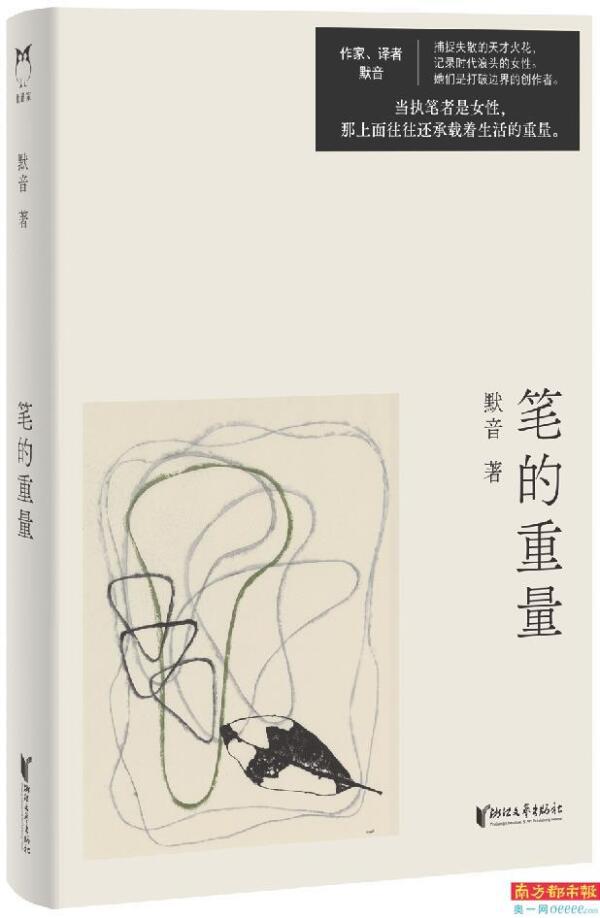
最新出版的《笔的重量》和《她的生活》两本书,是小说家、译者默音继2024年推出中短篇小说集《尾随者》后的新作。
2019年,默音辞去出版社的工作后,接下了日本女作家樋口一叶选集的翻译。樋口一叶是被印在5000日元纸钞上的女性,被日本文学研究者认为是“进入明治以来最初的女作家”。在深入梳理一叶的小说、日记等资料后,默音一头扎进了明治时代的文坛过往,最终在翻译之余,写出一篇关于樋口一叶的长文《一叶,在明治的尘世中》,收入她今年出版的随笔集《笔的重量》。
这本书里还有几位日本近代女作家的故事,比如从丈夫的“笔录员”到畅销书作家的武田百合子、近代第一个靠稿费实现经济独立的女作家田村俊子等,从明治、大正到昭和,她们都是立于时代浪头,创下过许多“第一”的女性创作者。默音将这些失散于时代叙事中的天才火花一一捕捉并重新串联。
“我忍不住为那些曾经出色却终于湮没在时间中的女性感到惆怅,她们本该留下更多的痕迹。”透过梳理资料,默音重新端详她们走过的路,“我在其中看到种种阻碍和限制,来自社会、家庭、性别和其他因素。她们能越过外部和自身的障碍,留下文字,给我们这些后人阅读,何其珍贵。我很高兴自己能写出她们的故事。”
在非虚构之外,默音还创作了中短篇小说集《她的生活》。作为《笔的重量》姊妹篇,正如书名揭示的,小说集《她的生活》的文本聚焦的对象是“她”。每一篇的女性形象有她自身的脉络与性格,其中收录的《彼岸之夏》设想了樋口一叶及其妹妹生活在现代日本的情景;《梦城》的起点是武田百合子的《富士日记》在未来世界的阅读演变;《竹本无心》的人物原型是衔接樋口一叶与武田百合子的众多女作者。
从非虚构到小说,《笔的重量》《她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互为映照,构建出一部从文本到现实,从经验到想象的文字交响。
默音说,如果你读过她们的真实生活,想要走进由想象力重构的世界,不妨通过《她的生活》一试。反过来,如果你先读到那些与她们有关的小说,可以通过《笔的重量》这本书铺就的小路,走入历史的罅隙,眺望她们的人生瞬间。
访谈
读职校时写科幻短篇获奖
南都:能从源头开始谈谈你的创作经历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基于一种怎样的想法开始写作?
默音:如果要追溯我成为一名写作者的起源,离现在将近三十年了。职校二年级的夏天,我在上海的第一八佰伴实习,分在中国字画文房四宝柜台,顾客通常是由导游带来买手信的日本旅游团。因为有大段发呆的空白,我开始想故事,写了第一个科幻短篇《花魂》投给《科幻世界》。幸运的是,当年12月的杂志刊发了,还获得年度“少年凡尔纳奖”,让我拿到一千多元奖金,比当时店员的月薪还多点。实习生工资只有一百多,因此感觉是一笔巨款。
我的小说刊在“校园科幻”栏目,有作者的学校和真名,我很快收到雪片一样的来信,大多数是在校学生。我给其中一些回了信,和同在上海的两个成了朋友,不过后来渐渐走远。
到了论坛时代,我在论坛连载爱情小说,拥有一些热心读者。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但更多是习惯和爱好。后来我念了大专自考,辗转过若干份工作,从日企IT到深圳一家日文杂志社的编辑。我在豆瓣写过自己学日语的经历,学日语和写作这两件事在我身上就像是一股绳索的两条线,密不可分。2006年,我想考研,从深圳回到上海。2007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念日本文学。那时我的理想是成为出版社编辑。大概是在研二开始写《甲马》,写了两稿,没能出版。之后我到九久读书人实习,去那里是因为有我喜欢的编辑彭伦,他现在是群岛图书的主理人。我们共同的朋友段晓楣是位图书策划人,也是看过《甲马》初稿的几个人之一。彭伦知道我在写小说,有一天,他对我说,张悦然她们要做一本Mook《鲤》,你要不要写稿试试看?于是我用一天的时间写了《人字旁》投给《鲤》,刊在创刊号。写的时候,我明确知道它是三篇小说之一,三个故事分别对应性别、种族和时间的困境。可以说,从《人字旁》开始,我的小说写作就好像河流涌入新的河道。
南都:此前你推出了“记忆三部曲”《一字六十春》《甲马》《星在深渊中》三部长篇,谈谈它们在你写作生涯中代表的意义?
默音:我只能说,在写的时候,每篇小说对我来说都是重要的,我有一些迫切需要表达、并且只能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的东西。一旦写完,好像就可以放下,也不想过多地谈论。
稍微讲几句《甲马》。实际上,在重写这部作品之前,我有一年多没写东西。我在出版社上班,业余做烘焙、打毛线,过得忙碌和自洽。我至今仍然不知道写小说带给人的更多是苦还是乐,重写《甲马》是一种既自虐又蓬勃向上的经历,长时间积攒的能量一下子爆发出来。如果让它一直停留在失败的第二稿(出书的版本是第四稿),我想我会终生保有遗憾吧。所以,最终能完成,还是好的。
“她的生活”是一种三重映照
南都:这次你同时推出了《她的生活》《笔的重量》两部作品,谈谈二者的关联性,它们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默音: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我的翻译工作的延伸。2019年,因为在工作之余写长篇有些力不从心,我辞去出版社的工作。出于对生计的忧虑,接下了樋口一叶选集的翻译。樋口一叶是距今一百多年的写作者,其文体是半文半白的“雅俗折中体”,翻译比预计的远为繁难,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阅读樋口一叶日记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日记并非纪实,其中也包含创作,或者说谎言。如果综合一叶的小说、日记,以及其他人留下的关于她的文字,就像拥有一面面不同角度的镜子,镜中的那个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真实。出于小说作者的好奇心,我梳理一叶的生平,写下第一篇类似人物小传的随笔《一叶,在明治的尘世中》。那时我没想到,之后的几年间,类似的张望和写作将一次次发生,我透过文本,与武田百合子、田村俊子等创作者同行一段时间,写下她们的故事,一次是非虚构,一次是小说。由此诞生的就是《笔的重量》《她的生活》。当然,小说集《她的生活》,不全是这一类延伸文本,也有三篇独立的小说。
南都:《她的生活》与田村俊子1915年发表于《中央公论》的小说同名,在随笔集《笔的重量》中,有一篇你写田村俊子与同时代女作家故事的文章标题也是《她的生活》,如此起名有何深意?
默音:田村俊子的《她的生活》,讲述一名女作者对婚姻有着清醒和悲观的认识,“女人完全闭上了灵魂,像人偶一样被从后推、往前拉着,一天天过着盲目的日子”。尽管如此,她还是结了婚,在婚后面对家务与写作的冲突,并在这个过程中怀孕,置身于更大的困境。在小说结尾,她最终还是坚持写作。这个故事描写的女性创作者的处境,放在现在也毫不过时,为了向田村俊子致敬,我用《她的生活》作为关于她的文章的标题,以及我的小说集书名,形成三重映照。
南都:《笔的重量》为我们呈现了日本文坛女作家群像,你在资料爬疏整理过程中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发现?
默音:实在太多了。比如,写田村俊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当然是九卷本《田村俊子全集》。有一位很重要的先行研究者黑泽亚里子,曾在冲绳国际大学任教,是全集的两位编者之一,她的研究领域也涵盖我的书中提到的另外几位女作者。我后来和她通信,得到许多鼓励。回到上海后,我走访与田村俊子有关的历史建筑,拍了照,发给黑泽老师。她发来1980年代走访同一批建筑的记录,照片里还有年轻的正在读研的她本人。目睹那些照片,我感到是田村俊子让我的现在与黑泽老师的过去相连,一种不可思议的体验。
南都:《笔的重量》中的日本女作家们几乎都逃不开情爱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牵绊。通过梳理从樋口一叶、田村俊子、尾竹红吉、长沼智惠子到武田百合子这些女性的写作历程,你希望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默音:在写作这项主要依靠脑力的职业上,男性与女性原本是平等的。不过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女性的确更容易受到情感和家庭的制约。我一直以为,小说并不是要讲什么大道理,同样地,在写女作者群像的时候,我也并没有想过要给读者什么启示,仅仅是邂逅这些女作者,并想要讲出她们的故事。我相信每个读者能从中照见自己有共鸣的部分。不过可能有读者会注意到,除了情感、家庭,我也花了很多笔墨写女性创作者的经济,毕竟“以文/画谋生”是每位创作者面临的重大难题。
“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武田百合子”
南都:在写作之外你还翻译了多部日本文学作品,《她的生活》一书中《彼岸之夏》《梦城》《竹本无心》这些篇目更是你翻译的延伸产物。谈谈你的翻译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二者如何互相影响?在你翻译过的作家中,谁对你的影响最深?
默音:前面也说过,这几篇的写作顺序是翻译的过程中大量阅读资料,写人物小传,心有不足,于是写小说。我从事翻译工作也有17年了,对我来说翻译和写作一直是平行线,自我感觉使用的是大脑的不同区块。如果不是对文本背后的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翻译工作的触角不会蔓延到写作上。对我影响最深的应该还是武田百合子,她的人生态度,她的观察力和生命力,是我极为喜爱但无法成为的样子。
南都: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默音:暂时没有长篇的计划,想好好写几个中短篇,多读点书,多出去走走。两年前开始迷上观鸟,现在对我来说观鸟比工作要快乐得多,算是一种迟来的贪玩。
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文化责编:王涛
 )
)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