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优府网首页 |
|
设为首页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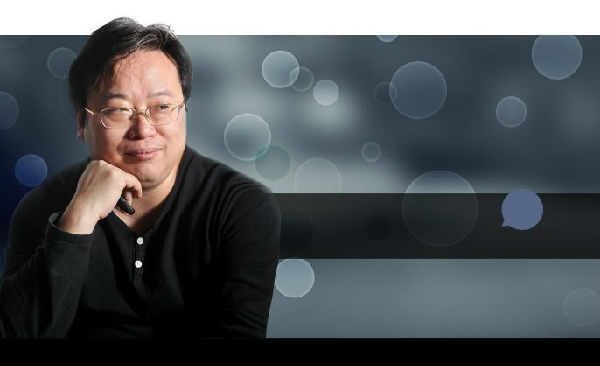
这是一个粗鄙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当我们回溯中国历史时,我们看到的信息传播的经典,就是通过烽火台来传播信息。在小说《基督山伯爵》里,也有描写了一个关于信息传播的非常重要的细节——邓蒂斯如何利用信息的不对等,挣到了钱,让仇人破产,实现了自己的报复计划,这说明此信息只有少数人掌握,也说明了当时的信息传播方式是非常单向的。
一直以来,技术革命推动着媒体业态的重塑,比如,告别铅与火,让黑白报变成了彩色报纸,改变了报纸的开机量以及报纸的厚度。但这种技术进步更多地是推动内部业态的变化,并未对媒体行业重塑起到根本性的变化。业态的成熟来自于技术进步。
这些年我每年都会在年底写一篇有关中国媒体评点的文章,大概在两年前,我就在一篇盘点文章里认为:信息垄断是专制主义的基石。过去,媒体往往代表启蒙者来说话,但今天已完全不能,互联网的技术让普通人拥有了像上帝一般的力量,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上帝,当然这一定也有先知先觉者。但如此一来,整个媒体业的新的分化开始了。新的互联网技术和传播技术带来的革命是颠覆性的,这跟我们过去讲推动内部业态变化的技术完全不一样。过去,在盛行激光照排技术时,飞利浦还在做电子纸张,但好像失败了,不能量产,但乔布斯的移动终端最终带来了颠覆性革命,小小的手机和IPAD彻底改变了这一生态。
在颠覆性的变革中,传统媒体黄金时代已经过去。2005年,时任京华时报社长的吴海民写过“传媒的冬天已经到来。”那时,还没人理解这个冬天到来的意思,没人理解它的真正含义。我们还看不到技术带来的杀伤力。
其实早在2004年,IDG创始人麦戈文就讲过大致的意思,说IT媒体将首先完蛋。在中国,IT媒体曾经是无比辉煌的。不久前,我与秦朔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说,“2012年,这是传统纸质媒体的高点,从此以后走下坡路,2013年则是电视媒体的转折点。”我也认同这样的判断,虽然它的经营额度不是最高点,但是事实上传统媒体的辉煌从此以后将成为回忆,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我们难道就完全放弃了?不会,即使人将死,我们还要努力奋斗,媒体也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有自己运行的逻辑规则。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替代者在野蛮生长,我们在座各位不仅是传统媒体的编辑、管理者,也更可能是一个自媒体人。比如说我朱学东,是最迂腐的传统媒体人,但是我也是一个新媒体的实践者,我今年唯一遗憾的就是,当时申音找我开公众微信帐号时,我说我忙不过来,拒绝了。到今年,我在新浪微博发了将近3万条微博,粉丝量还可以,在腾讯微博发了几千条微博,而我也是很晚才学会怎么在朋友圈发消息。我还是早年博客的写作者,直到今天还坚持着,在许多人放弃的时候,我博客的点击量却越来越高了。
所以说,我是传统媒体人,我估计在座各位没有人比我更传统,但是我觉得我也是新媒体的弄潮儿,不是因商业目的才来“弄潮”,但是在弄潮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弄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与过去传统媒体不太一样的是,今天,在传播技术的影响下,与过去传统媒体传播的封闭、自恋、单向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平台是一个开放、共享的平台。但我目前做的《中国周刊》,虽然也有所谓新媒体,但它依然还是一个非常封闭、保守的、单向的传输平台。
现在传统媒体人越来越多地奔向新的技术主导型媒体机构,我们都在向新的媒体平台、向新的技术移民。当然,在移民的过程中,很多人唱着挽歌走的,这也显示出他们的高明,虽然我明知道要死,但是我有时候多少会有点不忿。
今天,我根据个人实践中的经验和判断,想谈一谈技术变革会带来哪些变化?
一,我们都是媒体
首先,传统媒体内容生产的专业性和垄断性正在被打破。过去,我们媒体人工作很牛,很有职业尊严,我们把自己当作启蒙者。这些年,中国很多新闻学院的教育里起码有一点是成功的,但这个成功是不专业的,即让年轻人永远怀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梦想,这是他们投入这个行业的动力。但是并不专业。当然,在当下的环境里,如果完全专业的话,那可能中国社会会更糟糕。说法不一定对,但实际上这是毫无选择的过程,所有人进入媒体机构以后,就成为内容的把关者,是守门人,我们要为公众接受什么样的信息进行选择,我们才是选择者。
但是,新的传播技术打破了“选择困境”,内容生产的专业性和垄断性被打破了,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写文章。我每个月大概写5万字左右,大概有将近2万字的流水账日记,我是在记录自己的想法,另外大概有3万字是写得比较认真的文章。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还是微信,我们都是内容的生产者,我们不仅给自己、给同行提供内容,还给新媒体提供内容。
我们这些人,传统媒体里边经过相对好的职业训练出来的人,在新的技术媒体时代,我们会有自己的春天,只要我们能够做出好的内容来,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媒体。
刚才杨鹏兄所提到的,到4G时代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因为还没到来,但是我相信,3G时代已经给我们带来天翻地覆般的变化了,4G时代的变革会更加强烈。我个人可以经营我的博客或者经营我的媒体平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潜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传统媒体的专业性和垄断性被打破,传统传播渠道的垄断也被打破。我再举一个小小例子,比如,我现在写文章,每个月写3万字都有发表的可能性,我写完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想分享,其中一些我是等发表后我再放上博客分享,大多数文章我是写完以后就想分享。所以,我们现在都成了媒体,我们都在打破过去的传播垄断。过去我想给某报的副刊写一篇文章,便投稿给它,现在我根本不想,我只想发在我博客里,跟大家来分享,获得即时分享的快乐。
在这种冲击和对比之下,我们会发现,我们传统媒体的效率低下渐现。效率低到什么程度,过去我们从没意识到,因为过去我们有很好的利润水平,在一个政治垄断的背景下,在严格的媒体准入制度下,在有限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我们曾有过的很好的生活,都把我们养成了懒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传统媒体人实际上都是懒汉,我朱学东也是。举个例子,我们在传统媒体机构拿8000块钱跟互联网媒体行业拿8000块钱,人家才是真正的民工,传统媒体人哪算什么新闻民工?你是士大夫,你是知识分子,你很清高,可是,现在是一个市场竞争极其残酷的时代,你的低效,人家的高效,最后人家一定会把你干趴了。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劣币驱动良币的过程,你认为你写的东西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所以传统媒体的成本会越来越大,其实刚才杨鹏兄也讲到了,死的一定是集团。
我个人判断,三线城市的媒体和报纸也许还有一些生存空间和机会,但是这个空间和机会非常小,如果再扩版的话那就是找死。成本问题会是今后传统媒体都要面临的挑战。但是相当一部分一定会瓦解,一定会死掉,它本来应该死掉,为什么不死,我下面也会跟大家分享到。
二,技术会杀死传统媒体吗?
刚才我讲到的技术对于我们传统媒体的影响,它会杀死我们传统媒体吗?
首先,我们现在中国式的媒体格局不是依托市场形成的,它是计划经济的模式,是政治的模式,非市场、分散、低效、高耗。比如,一个报社里有很多总编、副总编,但像《中国周刊》有总编、副总编,但是我们其实就是编辑,一个名头而已。高耗是因为我们整体性在消耗,我们有太多的同质媒体,一个城市的都市报全部是同质的,没有特别的特点,你稍微有点优势很快就会有人来模仿,很快就有人抄袭。我记得在2003年,那时候喻华峰还在《南方都市报》时,有一次我作为传媒杂志的记者采访范以锦社长,采访完了我们吃饭聊天,当时喻华峰就说了一句话,说如果黎元江没有进去,他一定使劲砸钱,把《信息时报》砸出来,让《南方都市报》不会有今天的日子。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到今天为止,传统媒体市场里边,我们不能靠市场来打垮竞争者,相反我们的竞争者利用这种政治格局的保护,在充分地消耗着市场有限的资源。我们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遇到竞争的时候,通过资本,通过市场,通过其它方式可以把对手打垮,在中国则没有人被打垮,在政治保护之下。就像我们看到的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合并,两个巨头的合并,一人补5000万,听说他们的实际费用需要每年8000万,甚至我听说某经济新闻报纸也需要某地市委宣传部一年补500万,我对此特别惊讶和震撼。在这样的市场里,怎么能确立起真正的市场优势?其实就是把所有人都搞死,而不是让强者获胜。这是跟我们政治格局紧密相关的,因为媒体背后过去都是机构与单位,都是党的媒体,党的人,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实在活不下去了,你就是去敲竹杆,也能分散有限的广告资源。
这是一个完全的劣币驱动良币的过程,因为我们没有法律,即使有法律,也是选择性执法。所以我们讲在市场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之下,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死亡之路,但是杀死我们的不是技术,甚至不是市场。但是这个变化已经开始了,它活不下去了,很多市场资源向新的媒体领域投放,传统媒体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但是基于政治保护的原则,它还可以继续活下去,我们看到太多媒体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政治忠诚优先原则一定会被市场效率优先原则取代,这一过程我们付出的代价会非常昂贵,最后可能所有人都被搞死了,这个涅槃还没有形成。
三,大众媒体未来会不会走到一城一报?
其实我在今天PPT里边所提到的判断都应该打一个问号,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思考。
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我们大众媒体未来会不会走到一城一报?
我相信会,但是也许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我们却都死掉了,因为我们的体制决定了我们自己没有选择。
当遇到技术变化、市场变化时,美国媒体可以选择融资,可以选择卖掉,可以选择死掉,可以死了多少回都没有关系,就像生活杂志。该卖就卖,像商业周刊这样的杂志也可以卖。
当然我们也可以卖,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卖,但是我们过去扩一个版还要有关部门批准,我们现在想写一个选题都还要人家选择,我们的决定权在什么地方?如果正常的市场我们也会走到一城一报,当然我们这一过程会出现很多选择,这个选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产生。
第二,专业细分市场杂志的转身。像专业性杂志更容易建立起垂直的体系来,更容易获得盈利,更容易向新媒体转型,这在实践上有很多经验。但像我们这样的综合性杂志转身很难。
第三,向奢侈品方向转型,像我们的杂志仅仅形式上像奢侈品是没有用的,首先要有内容,也要有形式。
四,2013年是一个大关
2013年,这是一个大关,我在2012年就看到这个变化,我曾经写过文章讲这个事情,过大关,今年年底大家都要过大关。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这是一个最乱的时候,我们很多传统媒体人,首先是心理防线被摧毁,市场变化确实在发生,但是这个市场变化不仅是我们媒体行业变化,是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发生变化。到今天为止,我们不知道中国经济的底在哪。但我们看到了太多问题,这些问题一定会在传统媒体里面显现。其它行业也会有死掉的机构,但是为什么我们一有死的,就意味着整个行业一定要死了呢?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行业一定要灭亡了呢?
这两年,将是传媒业最动荡的时候,动荡以后我们会有选择,一部分媒体会活下去,尤其是真正强势的媒体品牌会活下去,毕竟这个时代依然需要传统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暂时还没有被技术彻底瓦解。比如《中国周刊》发表的好文章会在互联网上获得非常高的点击率,有人认为技术平台需要短文章,但我们发表的都是长文章。
传统媒体已经走上调整之路。但调整首先体现在心理上,打了败仗,阵脚一乱,大家都惊慌失措逃跑,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心理,哪怕他是最聪明的将军、最有勇气的将军,他也会慌乱。但是稳住阵脚以后我们会看到可能未必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坏,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大转型的时代我选择做一只鸵鸟”,鸵鸟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外面的喧嚣,你要死也好,要活也好,一听他的话一定死,不听他的话反而活下去。
其次,重新认识,内容为王,这个时代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容为王”?
我们要提供独特体验的文章,回到人本,回到人性的描述上。
有人问《中国周刊》还有人看吗?我说,我所做的都是反映个体命运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容易产生共鸣,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一个学校,一个企业,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如何转折,转折过程中如何抗争,而不再去挖掘真相逻辑,因为我们基本上知道了。但我们媒体的专业性还没有完全被取代就像《中国周刊》任何一个封面报道,没有组织的支持是无法完成的。其他部分内容要回到工业化、标准化、产品化的生产上,就是要压低成本。
我的理解就是技术,最终是普惠的,要利用技术而非投靠,投靠意味着比短,我们不可能跟技术员比技术,我们擅长的就是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关怀,我们要用关怀来产生读者共鸣,这也是互联网的用户体验,用在我们这个上面就是这样一个理解。《中国周刊》做4年月刊,尤其这两年在互联网上影响力很大,就是通过它的传播,通过技术让我们插上腾飞的翅膀。杂志在传统渠道和品牌传播上哪怕投入几百万、几千万,都可能是打水漂,没有互联网就是打水漂。传统杂志的真正的互联网市场,反而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但是它一定很小众,一定需要寻找共同价值观的人,这也是未来同仁办报、同仁办刊的很重要的方面。
五,学会野生而非圈养
我们从组织到个人都要学会野生而非圈养,要学会在残酷的环境里面生存,残酷环境里面生存并不一定生存不好。此时,无论我们在传统媒体里面,还是在新媒体的技术平台上,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一定得到相同价值观的人相互吸引、相互团结。这种同仁报办不是四十年代的同仁报办,它是在新的技术平台上,寻找到我们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而且不再是大规模的组织,大规模的成本。因为技术对组织架构的冲击瓦解非常大,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新闻民工背后,我们传统媒体一个死亡的很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文人办刊的骄傲、清高。换一种说法,就是低效。
到今天为止,技术还不是杀死我们传统媒体的真正力量,它给我们带上的不只是翅膀,不只是共同体组织,它还可以把大组织瓦解成一个小的组织,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更是这样。未来个性化传播渠道,一定是个人魅力型,一定是专业型,其实口碑型和个人魅力型是相互重叠的,我个人在博客里面的传播,更多的还是个人魅力型,别人说朱学东这个人比较坚持,比较顽固,写流水账写几年就如一日的写下去,我说不仅写流水账,我连抄诗都要几年如一的一直抄下去。
所以专业与大众的结合,利用的专业的表达方式和视角,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大众平台,才有可能是我们的未来。
我每一个PPT配图都是我们的封面报道,选的其实都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所有的思考都来自于我自己的体会和理解,比较迂腐,比较传统。因为我是科盲,我不知道技术变化最终会带来什么,但是我自己认为,无论技术如何变化,挖掘人性内部的东西,反映人本力量的东西一定会有未来,这个内容才是真正的“内容为王”,无论技术如何变化,无论媒体形态如何变化,是纸质的还是纸质与电子媒介集合的,好的内容就是回到人本,这也是我们像做公益一样,回到人本上。
 )
)